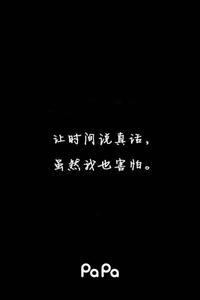你现在看到的是《时尚先生Esquire》12月特刊“年度先生”专题(点击这里查看年度先生全名单)。接下来我们会陆续推送“年度先生”的封面报道。今天是第3天,主角是年度歌手李健。
2015年,《我是歌手》让李健成为大众男神。在名声如潮水涌来的时候,这个有着41岁心智的人的第一反应是推掉通告和代言,按原计划出国准备新专辑。
李健清楚名利“有个警戒线,过了,会有问题”。他“不需要更多的钱”,名下没有房子。他坚持边缘且自我的生活,最看重的是“去全世界看一看,留一些时间看书和练琴,然后要喝茶喝咖啡”。
李健:正好适合孤独的尺寸
撰文/雷晓宇 摄影/陈漫 短片导演/杜寻梦
2015年11月3日,北京。
李健刚从杭州开完演唱会回来,有点累,所以睡到中午才起床。太阳还不错,他从建国门开车到金宝街的香港马会,和一帮搞金融的朋友吃饭,听人聊了一顿IP和电影工业。下午的时候,他没练琴,而是坐在工作室楼下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气泡矿泉水,又喝了一杯咖啡,接待杂志采访。有个朋友在旁边桌子等他,一边趁热吃着牛肉面。他们要讨论下一场演唱会的安排。
对一个刚推出新专辑的当红歌手而言,这样的生活节奏堪称闲散。但是李健坚持要这么做。
半年前,李健因为《我是歌手》的电视节目真正在大众范围内走红。他的反应是,推掉通告和代言,按原计划出国,处理新专辑的事儿。
两天前,他才刚刚放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周年庆典演出。原因很简单,他要去健身。在小区的健身房里,他经常和他的邻居姜文一起健身。但是过去这段时间,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姜文了。
“他把自己搞得太忙了,已经很难再过闲散的生活。”他说,“但我就要过闲散的生活,不要太忙。”
“人到一定阶段要做减法,所谓名利,有个警戒线,过了,会有问题。”
“我最看重的事情还是那几样,一切要为那几样事情让路。我要去全世界看一看,留一些时间看书和练琴,然后要喝茶喝咖啡。这真的就是我最关心的,其他都不是。”
“我不需要更多的钱。那一定会影响到你。一天还是24小时,但是你的有效时间会越来越少。”
“我名下没有房子。也有人找我,要给我提供独栋的院子做工作室。我都拒绝了,不需要。”
看起来,李健能够做到,因为他有41岁的心智,而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尝到名声的滋味。
“坚持就是无路可退”
第一次走红是在2001年。水木年华推出第一张新专辑,“不到半年就火了”。李健27岁,年轻气盛,他搬到姐姐亲戚的一个四合院里,宣布单飞。
第二次走红则经过了9年的等待。2010年,因为王菲在春晚复出唱了他的《传奇》,一夜之间,大家都知道有李健这么个人。这之前的一些年里头,他一直住在亲戚的那个旧四合院里,出了四张新专辑,很多DJ和圈里人喜欢,但没有一张挣钱。
21世纪的头十年,正是唱片行业受互联网影响最大的十年,行业不景气,很多人被从既有的社会结构里甩出来了。李健是清华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他的音乐选择成本更大,要面对更多的自我拷问。
“我可能是性格原因,从小心就比较大,还挺沉得住气。至少没有被唱片公司遗弃,不需要自己花钱出唱片……偶尔也焦虑,会想,人家孙楠在这个岁数已经怎么样了。但我这个人,觉得有吃有喝就行,吃一顿饭,看一个DVD,就忘了,很快就消解了。”
李健说,那时候他老提醒自己,现在之所以没有那么红,是因为还没有那么好。“我唱得很好,但我现场发挥不好,老紧张。我不像很多歌手,在酒吧夜总会锻炼过。我一上场就打折,面部表情也是僵的,一紧张,音也不稳。包括那时候老发胖,脸肿......我可能还不够,需要锻炼自己,我总这么安慰自己。”
他没想过放弃,并且非常警惕这个念头。“我经常提醒自己,你除了音乐什么也不会。人基本上一旦做了音乐,就废了,不能再上班了,不能再干别的行业,很难再社会化了。那时候,我写过一句歌词:坚持就是无路可退。”
还好有那9年的内心磨炼打底子,李健的2015会更容易点儿。当然,他确实又一次感受到了出名的压力。拿到《我是歌手》亚军之后,找他的人越来越多,粉丝也越来越多,这些管他叫“秋裤男神”的90后新粉丝们,和他多年追随的铁杆歌迷之间还会发生分歧。也有一些是非,几天前的杭州演唱会上,他开口感谢赞助商,立刻就有媒体发文章,质疑他在做广告。
“人越来越有名之后,需要的心智水平越来越高。你似乎成了一个中心人物,被解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但没必要因此小心翼翼,还是一如既往,过一种相对自我、相对边缘的生活。”
“很多人心里是没有声音的”
李健身在娱乐圈,但他有知识分子气。随着时代审美的变化,有时候,他这种特质显得他格格不入,落落寡合,有时候,这种特质又让他被看见,受欢迎,甚至成了某种有约束力的标签。
已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写了专栏文章,分析“李健现象”,为何他能够在一个急躁慌乱的时代环境里表现出平静、坚定、更接近生命本质感受的状态。专家用心理学的术语说,这是因为李健有“自我”,他把自己那一块地方保护得很好,有这个地方留在那里,不管外部世界怎么变化,你能够依然故我,为自己而活。
李健自己也承认,他的“自我”部分,来自大学时代的精神启蒙。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开始接触圆明园当代艺术家,在五道口也开始有大量的地下摇滚演出。他读《梵高传》,听窦唯和“涅槃”,和圆明园画派的艺术家来往,那种时代氛围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锤炼了专业技巧,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人要听自己的。
“老有人说,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心里是没有声音的,都是被活着,被变化。我们这一代70后算是幸运的,躲过了文革和反右,中学时代被洗脑得不太严重,所以大学时代也很容易就能够解毒。90年代出现那么多新东西,如果既有的自己不够坚固,那么很容易就被摧毁掉了。很多50后就很难,成了时代的牺牲品。真正的无依无靠,就是到了老年毫无兴趣。”
另外,常年保持的阅读习惯也对李健有巨大影响。知识结构会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结构。通俗点说吧,当一个人的男神是肖邦、舒伯特、马尔克斯的时候,对于陌生人管自己叫“秋裤男神”就会更容易一笑而过。
“你找一些参照系,就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就像我经常感受到时尚的有限性一样。”
最近,李健在一点一点重读当年读过的书。他爱从书里拎一些句子出来。他读北岛的《青灯》,感叹“房子小,但正好适合孤独的尺寸”真是好句子。他看陈丹青,觉得木心说得真对——“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
和自己的有限性做斗争
要真说李健有什么困惑的话,还是在音乐创作上。有时候,他会感到焦虑,带着一把吉他去外地演出,但是三天都没有练习。他担心,自己不碰琴,琴也不会给自己灵感。他又一想,哎,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完整创作出一首歌的巨大愉悦了。
回想当年蛰伏的9年漫长时光,他就是靠这种巨大愉悦支撑下来。“每一次写出一首满意的歌,本来已经快没自信了,就又能信心满满。又写出一首,信心就又多一些。”
他安慰自己,“再也写不出来”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科恩到80岁还在出新专辑啊,STING60多岁还在唱高音啊……最多会变少,没那么好了,但不会完全没有——除非你的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了。所以,话又说回来了,人不需要那么忙,要把自己的土壤保护好。”
以前,在李健的自我评价里,向来觉得现场表演比词曲创作更让自己不放心。但现在倒过来了。唱现场成了一种可控的重复操作,但词曲创作,尤其是词的创作,阈值越来越高,越来越稀缺,越来越难。
“有时候是一点想法也没有,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有时候是有个想法,但不知道要从什么角度来描述。我在想,接下来可能会写一些叙事性的作品,用一首歌来描述一个场景,像《加州旅店》那样,也能够满足我对于意味深长的需求。”
几年前,因为《传奇》火起来的时候,李健给自己买过几十万一块的手表。但这一次,他比谁都明白,真正的快乐是创作。这种快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他又不愿意跟很多同行一样去做生意,可怎么办好呢?
从2013年4月起,李健开始健身跑步。他不再那么容易感冒了,精神压力似乎也得到了缓解。他要过闲散的日子,又不能够忍受自己碌碌而为。他41岁了,难免要开始和自己的有限性作斗争。
提问个人IP的年代

E:都说2015年是IP元年,你如何理解个人IP?
李健:我今天中午才搞明白IP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在马会和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吃饭,他们在讲IP。我这才知道,原来I是INTELLIGENCE,P是PROPERTY。个人IP,就是好比《贝尔加湖畔》这样的歌,就应该能够卖到很多钱。然后拍成电影,搞出相关一系列产业。
中国现在热钱越来越多,创作力跟不上,不匹配,包括电影和音乐。好比高速公路修好了,上面跑的全是破车。之前很多人找过我,拍个IP电影什么的,但后来我退缩了。因为我不想见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它会干扰你的生活。而且我对电影没有把握,没有天赋,不可控。
E:你所在的行业,在五年前,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互联网和资本正在改变贵行业的游戏规则吗?
李健:五年前,那就是2010年。要说个人品质,以前可能讲敬业吧,工作态度——现在更讲才华。
以前晚会比较多,没有太多才能的人,很平庸,但是靠为人,靠做人,也能混得不错。但现在不行了,现在真的就靠才华。情况变了。地方政府取消了《同一首歌》那样的晚会演出,完全靠市场和自我认证。
至于资本,它还没有真正地加入音乐行业。它刚刚加入电影,音乐还是一个处女地。但是会很快,就这一两年——我已经感受到了。因为他们发现,电影一年几百亿,音乐一年几千亿。热钱一定会进来,已经开始了。
这两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是单纯讲才华了,而是更讲究综合能力,综合审美。去年,或者前年,我如果参加《我是歌手》,就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力——一个人不飙高音,唱情怀,也能出来。
这当然是进步了。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开始了,没人有能力操纵娱乐大众的审美口味。这都是好事。必须有一阵乱象,乱象之后,才得以规范,才可以洗白。
E:行业变化中,最触动你的一个人、一件事是什么?
李健:我赶上了,应运而生。为什么《传奇》2002年就写出来了,2010年才火?人们发生变化了。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发生,加快了人们审美口味改变的速度。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今天不会这样。
E:你认为音乐行业的行业危机是什么?
李健:有危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靠音乐维生,这是很残酷的。1997、1998年的时候,EMI和索尼,听到这些名字都激动,觉得哪天能够进这样的唱片公司,真是遥不可及。我突然想起来1990年代的场景,我在录音室里看到一个百代的工作人员,那真的就像看到我的未来一样,仰望,觉得神奇得不得了。
打个比方,这就像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在那里住那么一个小房子,人人都肯定喜欢,但是在现代都市里面,已经没有人会想要住那么一个小房子。在现在的工业里,传统唱片公司那种东西已经很简陋了,不适合,必须重新翻修。唱片公司需要大量的改变调整,如何成为一个互联网下的唱片公司。
E:畅想十年后音乐行业的变化?
李健:希望版税版权正常化,大家的收入能够不仅仅靠演出,让一些老年音乐家们能够完美地度过晚年。我在美国,看见一个老太太,爵士钢琴家,每两三个月就去唱片公司领支票,也可以养活自己。我就想,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撰文/雷晓宇 编辑/杨潇 摄影/陈漫
统筹/谢如颖 化妆/高晶 发型/陈锋 场地/麻乐Ge烫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