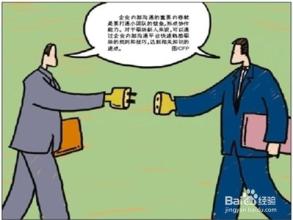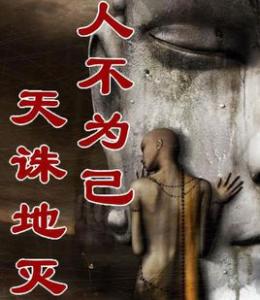*老北京杂谈
“俗语”不俗
——再介绍几句老北京俗语
俗语,作为老北京语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并不“俗”。面对不少“俗语”已经消逝,面对北京市市民结构的巨大变化,我更担心老北京俗语趋于彻底消逝的结局。既然喜欢介绍老北京俗语文章的朋友是绝大多数,所以我还是再“班门弄斧”地介绍几句老北京俗语。
一、“熬鹰”。
几年前,我们单位有一个年轻人好睡,每天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必须要迷瞪一觉。但是有一个领导喜欢午休时打扑克,而且每次必须叫这位喜欢睡觉的老弟一起玩儿。有时候,这个年轻人一边打扑克,一边打瞌睡,于是我“仗义执言”,对那个领导说:“你这儿‘熬鹰’呀!让他睡觉去吧。”没想到这句话说完,包括那位领导在内,都问我什么叫“熬鹰”,于是我做了解释。所以现在看来,大概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一老北京俗语及其含义,现介绍如下:
“熬鹰”,也有些老北京人说成“熬大尾(读yi)巴鹰”或“熬大鹰”,意思就是像人们“除夕熬夜”一样,人为地让“鹰”彻夜不眠。这句老北京俗语,来自满族人的驯鹰方法。鹰,作为一种猛禽,人们征服它不易,更不会听任人来指挥,所以就得“熬”。也就是说,连续几天几夜不许那“鹰”入睡。直到把它的野性消磨殆尽,老老实实地任人摆布为止。具体方法这里就不谈了。
久而久之,“熬鹰”就成了老北京人一句“俗语”,多用来指责干扰人们睡觉。如,面对夜晚的扰民行为,过去一些老北京人就会说:“你们干什么呀,‘熬鹰’呀?”意思就是你们让不让人睡觉呀。面对这种指责,那些扰民者也就收敛啦。这就说明昔日老北京人还是知礼儿。如今,那“熬鹰”的人们可太多了!我夜间经常听见疾驰的摩托车发出巨响;五环外一些地区夜间经常响一阵鞭炮声;凌晨遛早的狗狂吠等。所以“熬鹰”这个俗语渐趋消失,反之,“熬鹰者”可是日益增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吃爷的”。
这既是一句老北京人中流传的“俗语”,也是老北京的一句“歇后语”。具体说法就是:“庙后的住家儿——吃爷的!”渐渐地,人们就简略成一句俗语“吃爷的”。
据说过去老北京城内外寺庙特别多,不少大小寺庙的庙后或附近,都有不少住户。有些生活贫困者,就“偷”寺庙的供桌上一些人们上供的食品吃。因寺庙供奉的是土地爷、财神爷、城隍爷等诸神。所以人们就取这个“爷”字,指那些依靠寺庙供品生活的人们为“吃爷的”。后来,人们把那些贪便宜总撺掇他人请客及经常去朋友或亲戚家白吃白喝的人等,也称作“吃爷的”。所以这基本是一个贬义词!
我从小时候起,还真听见不少人用这句俗语形容某些人。如,我们胡同里住着一对儿中年夫妇。这二位不管走到哪个邻居门口,只要闻见香味儿,就走进去说:“哟,做什么好吃的呀?”说着,就下手抓着吃,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有时候赶上有邻居改善伙食,他们就故意凑过去,如果人家礼貌地谦让一句“一起吃吧”,这二位真坐下就吃!所以胡同里的人们都很烦他们。胡同里的老北京人都说他们夫妇是“吃爷的”。也有非老北京人称其“吃人儿的”!这种没皮没脸的人还真不少,而且大多是“小人”,得罪不得!
三、“打狼”。
这一“俗语”也是源于满族生活方式,即传统的围猎方式。具体到打狼这种动物,必须要许多人结伴而行,否则有危险。后来,老北京人就把许多人聚集而行的行为称作“打狼”,也把那许多人一窝蜂地凑热闹行动称作“打狼”。我小时候,看到许多邻居住户喜欢凑热闹。如听到胡同里传来吵架声音、或叫卖稀罕食品、胡同里卖艺的人们到来的锣声时,不少院子里的大人和孩子一窝蜂地往外跑。有些老人看不惯,就说:“干吗呀,‘打狼’去呀?真疯!”

“打狼”,应该不算是贬义词,有人在善意地规劝时也用这个俗语。如让某个人去干一件事儿,有不少人要一起同去,这时候那个派活儿的人也会说:“去那么多人干吗呀,跟‘打狼’似的!”
四、“军师”。
这既是个名词,也是个老北京俗语。该词主要来自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军师”是指蜀国的诸葛亮。由于他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料事如神,所以蜀汉皇帝刘备在当初请诸葛亮“出山”时,就任命他为“军师”。历史上被称作“军师”的人,几乎都是杰出人才。但是老北京人的这句俗语“军师”,可不是对一个人的褒奖,而是个贬义词。“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被称作“狗头军师”,而多少年来,老北京人都把那些背后出坏主意或挑拨离间挑起争端的人,称作“军师”,暗含讥讽、轻蔑之意。这“军师”的适用范围甚广,我小时候,所住的院子里就有一个被大家称作“军师”的老太太。这个人闲得无事儿,专门走东家、串西家、传闲话、跳动邻居不和。特别是当许多人对某个人有看法儿或心存嫉妒时,这个老太太就给这些人出主意,教唆他们如何对付某人。最后,大家都看穿了她,一位老先生冷冷地当众斥责她说:“你真是个‘军师’!”所以老百姓中被称作“军师”的,按老北京人话讲,都不是“省油儿的灯”。
“军师”只是在老北京人的俗语中是贬义词,并不同于对那些充满智慧的人的尊称。
归根结底,说老北京的俗语不“俗”,就是这些俗语本身就含有文化内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