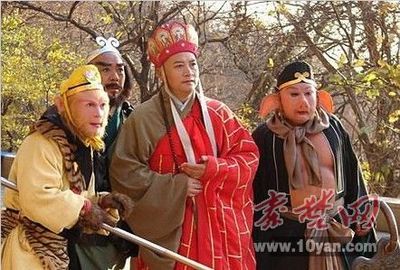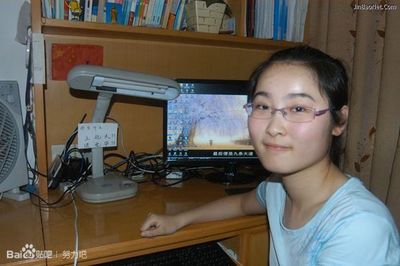首先,说钱钟书在“文革”中奉行的是“乌龟哲学”与“鸵鸟政策”,我不同意,可也不想多作争辩。我不明白的是:葛博士凭什么认定钱钟书在“文革”中是“假装专心于学术”?一个“假装专心于学术”的人,能在那样一个“乃武升天,斯文扫地”天地玄黄的时代写出那么独到厚重的学术著作《管锥编》来?葛博士也是“学术”中人,现在又是一个不用“假装”的年代,我更相信你不乏“专心”美德,那你何妨试试?——你的大作我看过,离独到差得远,离厚重当然差得更远。也许,你的时间都用去“对周遭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又见,反而又抗了,可实绩呢?不妨自报一下。
说“在强权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也显得陈义过高,更成问题的还在于:何谓反抗?难道一定要对暴力大叫大嚷、签名上书、游行示威,甚至开枪开炮才叫“反抗”么?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像李洪岩先生说的那样“关心政治而不做政客,担当道义而不忘学问,敢于负责而不哗众取宠。更多的是通过著述,来表达对人类、对现实、对自然的沉思(见《为钱钟书声辩》7、8页)。”就此而论,钱钟书是够格的:一部《管锥编》中,我们随处可读到钱钟书对专制暴政的辛辣讽刺与批判,这难道不是他对强权的反抗?知识分子对强权的反抗不是通过大叫大嚷,而是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潜移默化地进行——这一点,作为博士的葛红兵就一点也不知道?
李慎之先生在《送别钱钟书先生》(《大公报》1999年1月19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按:有不少人把他看做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煎熬着他的心。1989年的那个夏天,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一首七律(按:此诗后来收入《槐聚诗存》,也是诗存中他晚年诗的唯一一首)。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
块然孤谓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年。
我们相对黯然。我相信,海内外无论怎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命运作怎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朱学勤先生原来也认为“这二十年发生了那么多事,他(指钱钟书)就是沉默呢?是不是太世故了?”可看了李先生这篇文章后,他又才“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能保持这样的明白就行了,你还能要求他们怎样?你能要求他们上街去喊吗?这对他来说,太苛刻了,他内心的信念没有变,在可能助纣为虐的关键时刻,没有投下那块石头,这就可以。我对他是肯定的,至于他的文学成就,我没有发言权”(见《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朱先生因为专业的缘故对钱钟书文学成就不够了解,不知道他在文学研究中也贯穿着他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态度却仍能作出这么客观的评价,而身为文学博士的葛红兵却对行内人说出这么外行的话,这真叫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何清莲有这样一段话:“任何学者都没有办法超越他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要容忍文化的多样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的多元性。我们仍缺乏这种精神。”或许,这对也以治学为己任的葛博士有启发。
其次,想说一下葛博士将钱钟书与萨特作比较的问题。作比较当然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法,它能使金铜清楚、黑白分明。但我们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也得小心,因为任何比较都是有前提的,失去了这个前提而进行比较,那就只能是钱钟书讽刺的那种“狗比猫大,兔比猪小”的乱比,除了可笑之外,别无意义。最近看到一篇题为《甘地的限度》的文章(见《随笔》2001年5期),其中就谈到:“我们在谈论甘地运用‘非暴力’技术,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时,可能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制度演变,这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国家,无论它在统治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时犯下了多少错误,但有一点你得承认,那就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尽管它当时的民主制度、宪政体系还不完善,但它毕竟是民主制度,它的建国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权、人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帝国不管在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它的‘自由、平等’理念,但它毕竟是有规矩可循的。”我们不妨假设:如果甘地不是在印度,而是在中国也搞这“非暴力不抵抗”的运动——比如绝食——那会怎样?
其实,也不用假设,事实就有:上世纪30年代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不满于司法机关对他们的虐待,于是在牢中“绝食抗议”——可,除了饿得自己死去活来而外,什么效果也没有。鲁迅曾就此事发表议论说:牛兰夫妇显然是看错了地方,以为这儿也是英国人统治的印度,还讲什么人权,所以以为甘地在印度采取的方式在这儿同样适用。再后来,张志新他们开始为讲真话而坐牢,在牢中也曾为自己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而绝食抗议,结果却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好几次都给送进医院,插上饲管,而后把液体食物硬往你胃里灌——看你吃不吃!当然,这前提是你还有存在的需要——比如觉得你还有什么“重要问题”没有交代之类——如果没有这些个需要了,那你要绝就叫你绝:牢方顶多将那些霉烂的食物扔在你面前——反正我是尽了责啦,你硬要死,硬要“自绝于人民”,硬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那也随你的便!所以说在西方或其他地方行得通的办法,到了我们这里就不一定行得通——当然,也就无法比较。具体到萨特的例子。我们当然应该佩服他走上街头与苏联斗、与法国政府斗的勇气,可我们不要忘了:他是生活在一个诞生了“人权宣言”的国度,是一个他参加了游行示威而不会坐牢更不会给割断喉咙再枪毙的现代化国家,所以他这样做一点不困难——中国知识分子到了法国也不妨这样去做做“二十世纪良心”。可钱钟书生活在中国,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葛博士应该明白。50年代胡风事件时,开大会批判胡风。当时胡风的好友吕荧走上台去表示:胡风问题应该是个学术问题,不应该把它搞成政治问题,更不应该把他打成反革命。结果,马上被轰下台,直至后来给活活弄死。在这样的国度,你也能要求钱钟书走上街头大声疾呼?这与谋杀何异?如果是一个外国人,他因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作此苛求,我们虽然不接受,倒还能够理解;可葛博士“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地地道道的原产货呵,怎么也这样脱离实际地“高瞻远瞩”?我们应该明白的是钱钟书的文化使命:他不是战士,只是一个学者,我们不能将对战士的要求强加到一个学者身上,况且,在那样一个时代,钱先生便是站出来又真于事有补吗?
有论者指出:“即使钱激烈抗争而招致更残酷的迫害——这是可以肯定的,有每个过来人的经验为证,由学者化为烈士——这未必可以肯定,至少未必能以同等程度肯定,有储安平的命运为证,那也未必更有益于社会,因为这将使《管锥编》不会问世,就如倘若太史公不含垢忍辱而求死雪耻,《史记》将不会问世—样。这都不是中国人所期望的结果,尤其是那些谋求将爱国主义建立在传统文化及某些同胞所创获的杰出学术成就基础上的人们所期望的结果。”我想,这才是爱人以德的持平之论。
鲁迅曾感叹在中国没有西方那样勇敢的囚徒,那原因是因为中国监牢里的刑具实在是要比西方的厉害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该埋怨中国人不够勇敢呢,还是该攻击中国的监牢过于残暴?当年,有官方背景的王平陵曾指责鲁迅:“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作势,吞吞吐吐,打那么多弯儿?”鲁迅认为这不过是官话而已:“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地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我们此时又该去骂石头呢,还是该去骂植物?舍此而就彼,是不是有点“半夜吃桃子——拣了软的捏”?是不是也是“乌龟哲学”与“鸵鸟政策”呢?又是不是有点“强权的同谋”?也是当年,胡风的好友舒芜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到中央,结果给最高当局断章取义后作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铁证给抛了出来,于是胡风和他的朋友全成了反革命分子。后来大家都骂舒芜不是东西而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要不是因为他把私人信件交出去,会有这样的冤狱?可聂绀弩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舒芜交出胡风的信,其初是泄愤,随即是箭在弦上,其中大展鸿图的是X某,我以为是此公。因此我说‘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至于恶来是否干过X某的事不得而知,大概未干过好事。”
曾经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苏共“二十大”上,新任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做报告(史称“秘密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是揭露斯大林在执政期间如何乱用权力滥杀无辜,慷慨激昂头头是道……正讲得高兴,下面传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时你不也在场嘛,当时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赫鲁晓夫看罢也不忌讳,冲着大家就把这纸条读了,读罢脸一板,厉声道:“这纸条是谁写的?站出来!”会场一下鸦雀无声——谁敢站出来呀。一分钟后,赫鲁晓夫笑了:“我当时不站出来的理由和你现在不站出来的一个样。” “轰”会场上爆发出由衷的笑声。这个故事的寓意似乎是: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最好把自己也放进去——多一点同情与理解。愿与葛博士共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