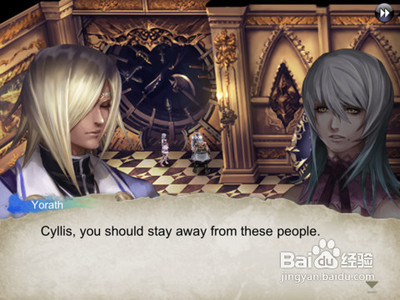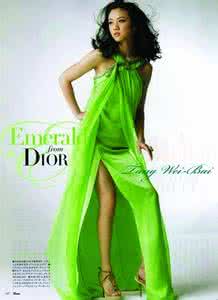
色界之戒
说来可笑,读《色·戒》当是在《十八春》之前,但当时我全然没有理会作者的名字,或可说,我全然不知张爱玲的旷世才华,至于读她的《小艾》,也是因题目的原因,这其中自是与我有些渊源,直至后来买了张爱玲的文集,才把那些从前读过的,沉下心再细细去品味。 写《色·戒》读书札记,是很早之前的想法,说不清原因就搁置了,至《色·戒》被拍成同名电影,写札记的想法就消失了,因我实在是那种不善于追捧热点的人,这就注定了我必要成为文字的边缘人。前几日有人说,“《色戒》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改编的?我才知道啊”,旧日想法,就蠢蠢欲动了。 张爱玲曾以万字写《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重笔书写了旗袍,可见她对旗袍的钟爱以及对审美的独到品位,《色·戒》开篇,即以形象描写为始。 旧上海的代名词,想“麻将”是必不可少的,牌桌上的王佳芝“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钮扣’耳环成套。”这样的描写,并不见奇特,若是接下来读“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便知道这一笔张爱玲写得如何奇妙。看电影比读小说来得容易,我想这该得益于视觉上的直观,而《色·戒》中的开篇,即有如影视剧这般的感觉,并不见作者多费笔墨,写王佳芝的清秀和官太太们自以为雍容的俗,而读者却分明知晓了。 我又把这开篇理解成是一种铺陈,为篇中写易先生与王佳芝的幽会,所打的精致的前战。易先生在汪伪政府供职,是汪伪政府部长之后,当是阅人无数,总该是习惯了雍容与恭维,就连他生就的一副“鼠相”,相士也说是主贵的,王佳芝的不落俗套自是让他生发了耳目一新的欲望,更何况王佳芝本身就担当着美人计的主角色,“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易先生更是要上勾的。 说起王佳芝接受的这个任务,多多少少是带着某种冲动,她原是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岭大迁到香港后,借港大教室上课。(岭南大学始创于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曾多次迁校,1900年迁到澳门,1904年迁回广州,1937年迁到香港,1942年迁至广州以北的韶关,二战后,终又迁回广州。广州沦陷之前,迁到香港,成了香港岭南大学的前身)流亡的心情使一些思想激进的学生以拯家救国为己任,王佳芝参加了爱国历史剧的公演,篇中有一段话“下了台,她兴奋得松驰不下来,大家吃了消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艺机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步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王佳芝的醉,多因演出的成功,实是陶醉于自己的演技,她爱国的热情里,尚还存有不少的盲目性,这也是我以为张爱玲为后来所写美人计失败所埋下的伏笔。 为完成刺杀易先生的任务,王佳芝“出演”了生意人家的少奶奶——麦太太,已婚人需要有性经验,日后勾引易先生,也定是需要这样的经验,王佳芝就因此失掉了童贞。“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篇中用了“便宜”二字,便可知王佳芝实则是如何不甘心把自己的初夜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她同学中唯一嫖过,唯一有性经验的梁闰生。这是张爱玲为写美人计失败所埋下的又一伏笔。 一切准备停当,利用关系去接近易太太,却不想还没找到下手的机会,易先生夫妇就辞行回去上海,美人计搁浅。“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王佳芝也感觉自己上当,以为最初就是被人别具用心利用,跟他们一伙人慢慢疏远了。这该是张爱玲为写美人计失败所埋下的再一伏笔。 珍珠港事变后,海路通航,学生都转学到内陆上海读书,此时出现了篇中唯一一个职业的特工——地下工作者老吴。张爱玲对老吴的用笔甚少,篇中只稍稍提过几笔,我仅理解成老吴只是一个绝对的配角,只是一个再度引发美人计实施的导火线。再者,我也一直惴然思忖是否与张爱玲避谈政治的情结有些关联? 张爱玲是避谈政治的人,《色·戒》是她唯一一篇涉及政治背景的小说,张爱玲回应发表在《人间》上以域外人署名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时,写过一句“00七的小说与影片我看不进去,较写实的如詹·勒卡瑞的名著《“冷战中”进来取暖的间谍》——搬上银幕也是名片——我太外行,也不过看个气氛。里面的心理描写很深刻,主角的上级首脑虽是正面人物,也口蜜腹剑,牺牲个把老下属不算什么。”这句话,有张爱玲悲情的一面,她心里自是容不得残酷的牺牲来换取的成功,她不能理解职业特工所具备的职业素质,或可说,她也是不屑理解,因而在《色·戒》文中,她对地下工作者老吴略带几笔,那几笔中细读总还是含有不屑的味道,她将之称为“神龙见首不见尾,远非这批业余的特工所能比。”(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 剩下的,就该是计划的如期实施,王佳芝也是颇费心思,篇中所有的笔墨俱是为这最后一次行动而做出的铺垫——王佳芝已经感到危险的临近,“今天不成功,以后也是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篇中并未写过王佳芝如何美貌,但我总以为她是极美的人,只因有“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这样的语句,就足以让我知道她是美人,因而王佳芝一直对自己能胜任这主角心存自信。但易先生是见过世面,老奸巨滑之辈,王佳芝却是特工中业余之业余,隐约中能感觉她的力不从心,此时篇中有句话“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从想写这篇札记开始,这句话就一直在头脑里盘醒,侍机由我的指尖冲出,我不得不几次按捺,安抚自己说,还不到时候,这实在是太精致的语言,又实在是张爱玲的风格。因我甚爱平底长靴配裙装这样的装束,一爱十几年,丝袜几乎必不可少,却尽在丝袜脱丝之时,平添了一份尴尬,越是怕,就越分明感觉丝袜的开裂,张爱玲的一字“爬”用得实在贴切,后来,我却习惯了不穿丝袜,虽不合礼仪,总是少了份担心,此处自是题外话,只因我不能不倾服于张爱玲的语言,未免就絮烦了。 这最后的行动定在一家珠店,刚好也是借了易先生要送王佳芝一枚钻戒,他们第一次在外面幽会时,易先生说这值得纪念。实则王佳芝与易先生只幽会两次,但“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这话中隐隐,王佳芝已经爱上了易先生,篇中未深提,是作者留作后笔。 但最终行动失败了,这是必然的结果。在珠宝店里,选钻戒的过程及王佳芝的心理,张爱玲俱是用笔丰足。那丝丝点点内心中的微妙情绪,都仿佛是王佳芝轻声而又不经意的叹息:“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道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儿工夫,使人感到惆怅。”此时有仿若画外音的一句话,“权势是一种春药”。 张爱玲是洞悉世事的人,尤其对男女之情。记得我写张爱玲的聪明时,有人极力反对,说她总不及杨绛,这之间其实是全无可比性,张爱玲仅是聪明,她并不具有壑智,她入得世,却总出不得世,因而她的一生是郁悒感伤的一生,她只是“鞋袜不沾地”来此世走过一遭,或可说,她本是不属于凡间。张爱玲的出身,及她小资的情结,也铸就了她的思维。但我依然喜欢她的作品,喜欢她的语言,喜欢细微之处,一些人不能理解的世间沧凉,我一直想,我骨子里生就带有悲剧色彩。从前有人批评我读书的专制,说我几乎从不涉猎外国文学,这必然要抑制我的视角,我不能否认,除了《简·爱》我由衷地喜欢,也读过一些类似于《羊脂球》等优秀短篇之外,我总是沉不下心读其他,这或是因我的任性,我生就便是一个十分任性的人,改了许多年,却总不见成效。 我曾说过,我是那种写字很慢的人,就因为我总是不能凝神,譬如这些题外的话,总是不经意间就流于纸间。 前面曾说王佳芝隐隐的爱,直到珠宝店里,作者才大肆渲染,类似于“权势是一种春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这样的话,是王佳芝内心极其复杂矛盾的时候,她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爱上了易先生,但通常这样的问,却是局外人清,局内人迷时。此时再看张爱玲留下的三处伏笔,王佳芝的爱国冲动,以至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就披挂上阵,特工的情感,是一件严重的事,但她却没有准备。再者王佳芝的失身,她心有不甘,但凡女人,哪有不珍视自己的初夜?尤其在那样的时代,这其实是王佳芝的一个心结。又者,失身之后,王佳芝本就十分委屈,得到的却是同伙隔岸观火的疏远,这不能说不刺激了她的热情。加之易先生的馈赠与性爱上老到的大手笔,王佳芝再所难免落入了情网,世上,自是没有无因之果。 在刺杀行动的最后一刻,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她低声说“快走”,易先生惊惶失措,篇中曾写易先生是绅士派,但在他惊慌逃路时,“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呼嘁嚓声。”不过三两句,十几二十几字,就让一个绅士儒雅扫地,我以为这也是张爱玲对文字成熟的驾驭能力。 王佳芝与他的同伙,不过晚上十点,就统统被枪毙了。王佳芝走的是易太太的线,成为了公馆上宾,是交友不慎,说出来也有失颜面,为了保全自己,这是必行之事。虽然易先生不无心动,“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但王佳芝比起自己的仕途,轻若鸿毛,“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不知这是易先生给自己的安慰?或是他太精于懂女人的心? 解读张爱玲,她的一生,爱得任性,如她的话——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是女人的悲哀。无论男人或是女人,大多为一个“懂”字去生去死,像为食的鸟,死都不觉遗憾,这就更觉得悲哀。我后来想,爱与婚姻是两件事,为懂去爱,为不孤单去结婚,爱——懂自己的人,嫁——爱自己的人,若刚好两者是同一个人,却又是一生中如何的幸事。 “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段话,令人毛骨悚然,域外人在他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这样评论,张爱玲亦在回应中肯定了这样的效果,也原是她想要的。其实这毛骨悚然的,不过是人最自私的一面,即也是张爱玲所说的“最终极的占有”。易先生这样的心思,王佳芝自是再没有机会明白,若是她尚可以明白,不知她是因此而欣喜,或是哀伤? 旧上海,依然是牌桌上的热闹,边打牌,边说易先生请客的事,“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整个故事,从牌桌开始,到牌桌结束,不过是一天之中,一场爱,悄然结束。 我似乎没刻意看过李安执导《色·戒》之后,众口对它的评说,但总还是有一两篇偶然入目,尤其有一篇写英烈的亲属抗议影片诋毁了她的名声,这英烈据说是《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另又看过一些人对小说的品评,类似于“张爱玲为了粉饰自己提不上台面的爱情,就牵强的扯上了英烈”这样的话,想张爱玲活着,她定是没有语言的,张爱玲这一生为自己辩白的话,似乎很少,禁不住又想她的那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不慈悲,也皆因不懂得。 在《聊斋》中,常有借尸还魂的事,魂是思想,尸是载体,载物是船,方能渡到彼岸,张爱玲通篇都不想涉及政治,她原就是避谈政治的人,我却反以为是那些指责她“牵强扯上英烈”的人,玷污了英魂。《色·戒》通篇,不过是在说一个“爱”字,犹如硕大的篷草,枝叶蔓摇,土层下,不过是不盈拳大的根,看上去是一篷,其实都是那一声从口中嘘出的叹息,叹王佳芝,亦是在叹自己。 我从未想过,我对《色·戒》的话原是这样多,一路写下来,竟然自己也有些惊诧,却想,这或许是一种聚集后的爆发,只是返身通读,又似乎感觉并非我想要表达的,倒感觉仅题目四个字——色界之戒,就该是通篇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