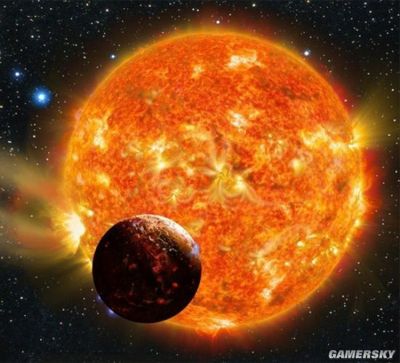这是苏州东山的一个小村落,叫陆巷。背靠莫厘峰,面对浩瀚太湖,掩映在大片桔子林中。没有专门的旅游宣传,更没有大批游客光顾,冷清古旧。可又如何能料到,就是从这小小的村落中,走出了数十位从进士到状元的古代才子,又走出了十几位现代的教授呢?
村巷只有二米来宽。两边的墙面早已斑剥,露出上了年代的青砖白缝。铺街的石板棱角都已磨圆,象一条条“鲫鱼背”向前延伸。不多的几家店堂,铺面都是老式的闼板门木格窗,就如我现在所坐着的对门,就是一家同样格式的乡村面店。
与我对桌而坐的,是一个长得很水灵的本地小姑娘,正在桌边专心出虾仁。那倒在桌面上的虾,都是欢蹦乱跳,其中有大半是很有名的“太湖白虾”。我问小姑娘:怎么活虾中把白虾和河虾混在一起了?小姑娘回答说,是她父亲刚从湖边捕捞上来的,每天都这样,一出水就送到这店里做“面饺头”。我一听,食欲大开,叫一声:“那我也来一碗。”店堂里随即一位妇女答道:
“虾仁面一碗——,请稍等。”
就在我坐着的地方不远,“解元坊”,“会元坊”,“探花坊”三座石牌坊,一座接一座,横跨在狭狭的村巷上。它们在这里耸立了几百年,记载着在明朝万历年间,从这里走出了一位叫王鏊的读书人,二年之间连中乡试第一名,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三名,最后当上明朝宰相的真实故事。
古韵古貌,民风淳厚,是这里给每个来访者最直接的影象。走过三座石牌坊向右拐,就是王鏊的故居“惠和堂”。那故居前一级级青石石阶上,被当年王鏊的骡车碾出的两道深深凹槽。还历历在目。而那占地二十多亩的宰相故居,虽格局宏大,然所有古色古香的梁柱门窗,都早已漆色褪尽。少了几多亮色,却多了一份古朴。糟朽的地板,磨损的楼梯,苔痕上阶绿的天井,各房中榫缝隙松的明清家俱,都在无声诉说着岁月的苍茫。
古居中各进厢房的老式书桌上,都整齐排放着文房四宝,没有人看管,也没有人拿动。我在那静无一人的书房中伫立良久,很想翻翻书桌上那部半尺厚的线装书,但终久没敢伸手,生恐惊动了当年老宅的原主人。也许,隔壁幽暗的卧室里,那有着双层围屏的雕花踏步床上,老先生正午睡方醒呢。
——连空气也是几百年前的。回味着刚才的游览,坐等吃面时,面店的女主人却还要给面锅加水。她提着担桶,走向不远处的一口水井。看着那造型古拙的青石井栏圈,我脱口而出:“‘清嘉庆年制’,噢,这口井也该有二百年了吧。”“那有什么稀奇,”出虾仁的姑娘接口道:“你看看脚下的石板,每块都还隐约看得出上面刻着的一只圆瓶,瓶中插有三枝箭,这是当年为我们村里的王鏊平步青云,连升三级而特意刻制的,有四百年哟……”
说话间一碗面条已端上桌子。淡淡的蒜花香中汤清面细,粉嫩的虾仁撒满碗口,上面还顶着两颗碧绿的青菜心。呵,田园风轻拂,色香味俱全!
坐在巷子边,脚踏着四百年前的石板,喝着二百年前古井里打上来的水烧煮的面汤。品尝着眨眼前还鲜活的太湖虾仁,真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不明白:这个陆巷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出了众多的现代学者,为什么不事张扬,民风民居仍如此古朴呢?想起了宰相故居里,后院门楼上看见的一砖雕篇额,上书:“蔑誉乃吉”,也许,从中可以找到些答案吧。

陆巷的古村落,陆巷的虾仁面,一个古老,一个鲜活,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原汁原味。但愿下次再来,仍是如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