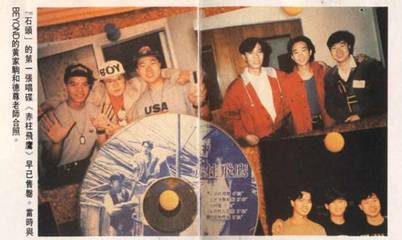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房地产广告
文 | 唐博
转自《地图杂志》(微信ID:DiTuZaZhi),本文经“地图杂志”公众号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蹒跚起步
一切还要从100年前说起。20世纪初,香港岛北部。
维多利亚港湾,皇后大道两侧,船坞、码头、货仓、别墅,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尤其是置地公司在德辅道中与毕打街交界处开发的告罗士打大厦,高达9层,既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又以其钟楼闻名于中环。然而,这些热点区域和宏大建筑,都是外资公司的杰作,罕有华商的身影。
20世纪初香港岛北岸“维多利亚城”的行政区划范围。“维多利亚城”与华人俗称的“四环九约”的范围基本一致 地图/姚维娜
而诸如港岛上环、九龙深水等如今的繁华地段,在当时尚显得偏僻荒凉。抱着发财梦涌入香港的大量华人,被无情的现实惊呆了:并非遍地黄金,没有固定居所,他们只能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在这些地方搭建木屋度日。1864年,香港平均每间房屋居住华人16.9名;到1891年增加到18名;再到后来,香港城区甚至出现三四十人同挤一屋的情况,人均居住面积远低于港英当局法定的华人墓穴面积(1平方米)。
19世纪末的上环,有大片华人居住的旧屋
19世纪末港岛中区干诺道新建建筑物,包括香港会所、太子行、皇后行、邮政总局大楼等
一些家底殷实的华商从住房紧张的背后嗅出了商机,认为香港被压抑的住房需求一旦爆发将势不可挡。于是,他们开始介入地皮生意。最早把房地产作为金融工具的华商,是洋行买办和商行老板,如太古洋行买办莫仕扬、怡和洋行买办何东、和兴号金山庄老板李升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华商崛起,开始逐步收购洋商手握的地产物业,自建中国式的“唐楼”。在“马嘉理事件”造成中英短暂交恶期间,清政府实施“海关封锁”,香港经济一蹶不振,全靠地产业的繁荣才得以重振旗鼓。到19世纪80年代初,华商在房地产业的影响力逐渐超越,甚至压倒英商。港督轩尼诗不得不承认,华商业已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大部分都掌握在华商手中,港英当局的税收也有90%来自华人。
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华商大举收购地皮物业,并购破产商行,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炒高了地价,引发地产投机热潮。房地产投资犹如一场赌局,暴利驱使着越来越多的华商和洋商倾囊而入。据估计,就在这四五年间,香港地价、楼价飙升了6倍。
然而,正当这轮投机风潮如火如荼之际,消息灵通的洋商突然获悉英国政府即将派员前来取缔香港华人旧式楼宇。于是他们踩准高点率先大量抛售了手中持有的房产。消息闭塞的华商们一看危机临头,也被迫争相抛售,导致楼价暴跌,赔得一塌糊涂。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香港楼市雪上加霜,破产的华商比比皆是。香港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伍廷芳,就因房地产投资失败,悄悄离开香港,毅然从政,当上了李鸿章的幕僚,成为清末民初的政坛明星。
虽然伤了元气,但华商在这轮投资风潮中也并非一无所获。许多华商开始染指港岛中区,打破了外资房地产商的垄断;劫后余生的华商,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华人移居中区,开设店铺,享受这里繁华的商业都市生活。
清末礼部尚书许应骙之子许秉璋,由姨太太出面,在干诺道购入几栋洋房,当时每栋也就两三万元,几年后却升值到二三十万元。到1930年,许家的财产已经增至200万元,比许应骙为官一生的遗产还多。
1889年成为置地公司董事局仅有的两位华人董事之一的李东,在1901年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多达600万银元,加上一大批房产,比港英当局财政收入还多180万两。李氏家族俨然香港首富。
就在香港华人房地产商队伍稳步壮大,生意日渐兴隆之际,太平洋战争的阴云突然降临。接下来,便是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其时香港经济陷入停顿,房地产业千疮百孔,对于华商而言,无异于一场梦魇。
地产革命
1953年圣诞前夜,香港九龙深水附近的大埔道山脚。成片的铁皮房和木屋依山而建,杂乱无章。没有街灯闪烁,没有电力供应,有的只是通过偷电换来的些许光明。夜里9点半,北风呼啸的山上的一间木屋内有人点灯时不慎烧着棉胎。火借风势,烈焰迅速吞噬了民房。人们纷纷夺门而逃,哭喊声响成一片。大火足足烧了6个小时,1万多间木屋付之一炬,5.8万人无家可归,为香港有史以来所罕见。
这场后来被称为“石硖尾大火”的事件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个严峻事实。一方面,由于经济复苏,外来人口涌入,香港人口迅速膨胀;另一方面,战争导致原有房屋损毁严重,供应不足,“房荒”成了世人瞩目的社会病。房租跳涨,四年内翻了五番,很多人租不起房,只好挤在一起。湾仔一栋古老的3层木结构唐楼,竟然挤下90人之多,不少居民只能睡6层的“碌架床”,条件十分恶劣。1956年,有35%的私房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5平方英尺(约为1.39平方米),还有25万人居无定所,不得不在郊区搭建木屋、铁皮屋,甚至露宿街头。
20世纪60年代香港普通民众恶劣的居住条件——多层唐楼(左)、笼屋(右)
20世纪50年代立信置业公司出售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的“分层售卖价格表”
然而,就在房租快速上涨的同时,香港的房屋售价却增长乏力。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当时的惯例,新建楼宇不能超过5层,而且要整栋买卖。除了上海来的大款和俗称“金山阿公”的海外归侨,罕有买得起的主顾。他们买房子并非为了住,而是为了收租。售价低,租金高,一般八九年即可回本。这样下去,房子盖得再多,解决“房荒”也遥遥无期,何谈发展房地产业。就在这时,有两个头脑灵活的华人房地产商率先推陈出新。
1948年,位于九龙尖沙咀北的山林道46号至48号,正在出售两栋5层高的楼宇。跟其他滞销的楼盘不同,这里竟创造了三天售罄的奇观。作为开发商,鸿星营造有限公司老板吴多泰得意洋洋。这两栋楼宇,每层都有三房两厅、两间浴室,工人房和厨房也一应俱全。吴多泰深知,买得起整栋的主顾稀少,资金周转缓慢。在律师行的帮助下,他弄到了港英当局田土厅的批文,决定分层出售,并在房契上注明每层业主享有的土地权益。这种售楼方式很快就在香港推广开来。
1954年,位于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的一个超大型社区开始售楼。100多栋楼宇,大约600多个居住单位,还未竣工便被一扫而空。它们的开发商是立信置业有限公司,老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霍英东。当时,尽管“分层出售”让买主的数量多了一些,但仍以富裕人家为主。当时的楼宇每层约1000平方英尺(约为92.9平方米),总价约2万元,而普通打工仔月薪不过200元,一下子很难凑齐这么多钱。霍英东认为,只有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买得起房,并且愿意出手买房,房地产生意才能做大。于是,他在“分层售楼”的基础上,首创“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
更让人称奇的是,他为新楼盘创制了香港第一份售楼说明书——《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分层出售说明书》,用20页的篇幅详细说明了楼宇的地理位置、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配有地盘图以及楼宇的透视图、平面图和剖析图等;明确了首期订金50%,以后每期交10%,直至第六期项目竣工交房时付清尾款。漂亮的楼书,灵活的销售策略,吸引了大批主顾前来洽购。买家付清首期订金时,楼宇刚开工,好比植物处在开花阶段,尚未结果,于是这些楼宇就称为“楼花”,分期付款也就俗称为“卖楼花”或“卖期房”。
后来,首期订金的比例逐渐降到总楼价的10%~30%,并且出现了银行中长期按揭贷款的制度,使得普通市民买房的资金门槛大大降低,香港楼市的成交量迅速拉升,楼价开始飞涨。吴多泰、霍英东大受其利,迅速做大,成为香港华人房地产商的奇葩。他们创立的分层、分期售楼制度,逐渐成为房地产业界通行的销售策略,在地产界无异于掀起了一场革命。
寡头崛起

就在吴多泰、霍英东叱咤香港房地产市场之时,一个名叫“鸿昌合记”的杂货店在上环开张了。由于老板起早贪黑,待人和善,街坊们交口称赞,生意也日渐兴隆。几年过去了,杂货店变身成为主营日本拉链批发的“鸿昌进出口有限公司”,这个老板也被誉为“洋杂大王”,他的真名叫郭得胜。
搭乘香港轻工业繁荣的快车,郭得胜的生意非常红火。随后,他又开始染指房地产业。1963年,他和冯景禧、李兆基合伙创立“新鸿基企业公司”,自任董事局主席。“新鸿基”的命名,分别取自冯景禧“新禧公司”的“新”,郭得胜“鸿昌合记”的“鸿”及李兆基的“基”。这个日后著名的地产巨擘,成立之初只有十几名员工。
创办新鸿基的“三剑客”——冯景禧、郭得胜、李兆基(从左到右)
就在新鸿基在香港地产界初出茅庐之际,一场从罢工游行演变为暴力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五月风暴”在1967年爆发。这场社会危机使香港经济遭受了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大街上随处可见弹片,市面上到处散布流言,大多数香港人生活在恐慌与焦虑中,一些商人为了保住生意,被迫远走南洋。
然而,郭得胜没有走。他从各种途径了解到,许多中小企业对多层工业楼宇很感兴趣。于是,他开始到处收购别人贱价抛售的工业楼宇,并将“分层销售”、“分期付款”的售楼方式移植过来。他坚信,危机总会结束,复苏迟早到来,现在抄底正当其时。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内地鲜活的农产品供应依旧源源不断,中英街的边贸依旧熙熙攘攘。渐渐地,香港社会的政治环境逐渐稳定下来,经济衰退也趋于终结,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
曾经害怕动乱而离开香港的商人们纷纷归来,西方跨国公司在香港增设机构,增派高级职员,各种热钱也争相涌入香港,中高档住房的需求量急剧放大;轻工业的迅速复苏,增加了大量就业机会,市民手里有了钱,日子稳定了,消费欲望和投资激情被重新点燃。然而由于前几年的萧条,香港楼市的供应量下滑,造成短期内供不应求的局面。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刺激了香港房地产市场大幅度反弹。1969年初,港岛山区、浅水湾和九龙塘的高级住宅每平方英尺售价60~80港元,到翌年底已经涨到160~200港元。
郭得胜的工业楼宇,卖得出奇的好。从1965年至1972年,新鸿基的销售额约5.6亿港元,平均每年高达7000万港元。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三人被誉为香港地产界“三剑客”。
就在新鸿基风头正劲,积极准备上市之际,“三剑客”却分道扬镳。冯景禧创办“新鸿基证券”,进军资本市场;李兆基创办“恒基兆业”,开始自立门户;郭得胜则推动新鸿基公司更名为“新鸿基地产”并完成上市。其后的20年间,新鸿基地产就像是一家楼宇制造工厂,源源不断地将地皮“原料”加工成楼宇,推向市场。更可贵的是,郭得胜只在香港和内地稳扎稳打,精耕细作,决不贸然向海外发展。1990年,郭得胜在香港病逝,留下的是一家市值高达254亿港元的大型地产集团,以及无数商界传奇。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那个动荡年代,除了郭得胜,还有两个人也留了下来,抄到了底。他们就是号称“塑胶花大王”的李嘉诚,以及周大福金银珠宝店的学徒兼女婿郑裕彤。
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实业,将地铁上盖物业与地铁通车日程配合,在中环站和金钟站的竞标中大获全胜,分别建成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创造了开盘首日售罄的佳绩,书写了“华资地产界的辉煌”。他投资创办的长江商学院,成为培养高端商务人才的著名摇篮。郑裕彤的新世界地产,以在尖沙咀的新世界中心最为著名,囊括大型商场、高端住宅、电影院、五星级丽晶酒店等多种业态,开辟了商业综合体开发的新路。他投资开发的香港会展中心,作为港岛濒海的标志性建筑,见证了香港回归时的政权平稳交接以及历任特首宣誓就职等重大政治活动,历史意义非同凡响。
李兆基自立门户后, 看到香港人多地少的现状,认定小型住宅大有可为,于是在市区大量收购旧楼加以重建,开发300~500平方英尺(约为27.87~46.45平方米)的小户型住宅。这些住宅由于交通便利,受到顾客青睐。他还意识到市区土地日益稀缺,因而率先进军新界楼市,大量囤地,开发出“沙田第一城”等郊区市镇。1981年,李兆基借壳一家名叫“永泰建业”的小型上市公司完成了上市。
至此,长江实业、新鸿基、恒基兆业、新世界,作为香港华人房地产商的“四大天王”各就各位,开启了香港地产界的寡头时代。即便在1982年和1997年的两次地产危机中,即便在炒楼者因巨亏而跳楼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的舆论氛围中,“四大天王”依旧处变不惊,渡过难关,引领着香港华人房地产商开拓新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