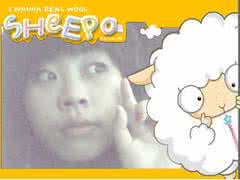
文:晚睡姐姐
? 这是某部美国律政剧中的一个故事。
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现在第三个孩子还在妈妈的肚子里,也快到了预产期,全家人都很高兴。
妈妈去做产检,医生告诉她,这个孩子的胎位有问题,一定要剖腹产,如果自然分娩婴儿会有生命危险。
妈妈不同意,她有信仰,笃信上帝。相信上帝会眷顾她的孩子,既然前两个孩子都成功自然分娩,那么第三个也一定没问题。
医生再次做出检查,非常严肃地告诫爸爸,这个孩子绝对不能正常分娩,他以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来保证,必须剖腹产。他希望爸爸可以做通妈妈的思想工作,爸爸提出了要求,妈妈还是断然拒绝。她不是不关心胎儿的安全,她也同样深爱这个未出世的孩子,但她更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这爱本身就是她信仰的一部分,强大,不可撼动。
一面是太太的宗教信仰,一面是专业的现代科学,爸爸显然更愿意相信后者。在万般无奈之中,他只有聘请律师起诉自己的太太,以太太危害到婴儿的生命安全为理由,要求法庭裁决强制太太进行剖腹产。
夫妻对簿公堂,遥遥相望,泪眼朦胧。谁都不想走到这一步,怎奈两方的权利在中途发生了碰撞。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到底是保障妈妈肚子里孩子的权益,还是尊重妈妈自主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法官也承认自己陷入了僵局。
两方律师各自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进行了举证和辩论,但最终的裁决权还是在法官手里。法官思虑再三,还是决定维护妈妈的权利,妈妈有权利选择自然分娩,即使法庭也不能强迫一个人放弃自己固有的权利。法官说,婴儿的安全固然重要,但保护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则正是法律的职责和神圣之处。
说实在话,当时看到这个故事我也非常不理解。何必这么执拗呢,难道信仰比孩子的安危还要重要吗?我相信,这位太太要是在中国,肯定被先生拉到医院就给她剖了,谁管你什么信仰不信仰,而且保证舆论都站在他那一边:你是妈妈,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你个人的权利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故事让我想了很久。最后,我理解了妈妈也理解了法官的决定。这个故事肯定是极端戏剧化的,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一定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它带来的提示是,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一个人人都尊重,并努力维护自己权利的氛围。这是个很好的启发。我们不较真,我们习惯交出自己的权利给别人,我们的权利时常被别人侵犯也时常去侵犯别人的权利,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我们变成了活在笼子里又不自知的那些人。
前几天两会上有人建议“孩子不满十岁的夫妻不能协议离婚”的提案引发热议,提案称从2002—2013年,国内离婚对数占结婚对数的比重从15.0%增加到26.1%。原因是《现行婚姻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婚姻登记程序过于简单,离婚门槛低,所以致使近年来离婚率逐年攀升。他们因此倒推出要只有提高离婚的标准和门槛,才能制止草率离婚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企图以侵犯一方的权益来确保另外一方的利益得以维护的思维。作为自然人的夫妻,有权利选择任何法律允许的方式离婚,而不能以保全子女的利益为借口,人为提高行政围栏,增加离婚的难度。
要保护离异家庭的子女权益,就要从法律的源头上明确离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却不是本末倒置——“既然离婚对孩子未来的成长不利,那干脆不许你们协议离婚。”这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近些年来,国内的离婚率确实一路红灯,全线上扬,但究其根源,并不在于结婚、离婚的程序简单,而是和当代人更注重感情的质量有关。以前的人能忍的日子,现在的人不肯忍了,以前离婚是丢人的事情,现在破除传统观念人们活得更自我。这离婚率自然就高起来了。
能让孩子有个完整家庭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我也相信,无论谁走到婚姻尽头时肯定有自己下定决心的苦衷。如今来看离婚的源头,已不完全单一。可能是被父母催出来不自由的婚姻、可能是当初草率的结婚,也有可能是双方性格在各自社会环境中与之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等等。的确,对旁人来讲总是劝和不劝分,但我们该做的是如何想办法维持或增进婚后夫妻的感情,而不是在手续上刁难双方的权利。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能消除对于剩女或离异者们的偏见。就像那个坚持要自然分娩的妈妈一样,即便知道后果与风险,她也要求这个世界尊重她的权利。先不论对错,仅这种执着而言,也是种对自己身体争取自由的体现。
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我不知,但是我希望我们在结婚后的世界与思维中不仅仅被孩子占据了100%的生活。别忘了,还有一个需要你关心与尊重的人:TA就是你的爱人。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