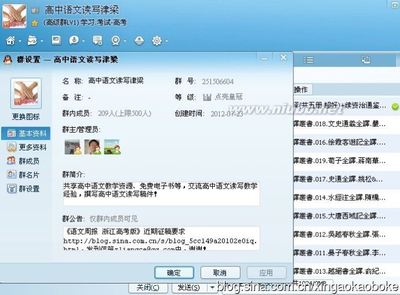文革期间发行的报刊书籍,同这个时期的许多物品(如邮票、像章、红宝书、红袖章等)一样,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现代文物了。这类报刊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意义而具有较高的研究、纪念和收藏价值。因文革时公开发行的杂志本来就不多,时至今日,则更是稀少难觅了。特殊时期造就了特殊杂志,也造就了时下的特殊收藏热点。
《毛主席语录》又叫“红宝书”,在文革期间,它发行到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它最初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解放军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加以补充、选编而成的。最早的“红宝书”是1964年5月出版的,自从1966年12月林彪为其写了“再版前言”后,便逐渐红遍全中国了。
文革中发行的“红宝书”数量极大,仅1967年全国就正式发行了3.5亿册,同时还出版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本。“红宝书”式样多为红色塑料皮本,以10.7×7厘米为流行本。汉字版共有7种版本,最早的一种是1964年5月出版,最晚的一种是1969年2月出版。少数民族文字有5种,分别是蒙文、朝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每种文字印有3种版本。“红宝书”外文版共用了37种文字出版。
由于时过境迁,这类“红宝书”大多数被遗弃、处理,因而收藏难度随之增大,但这正应验了一句收藏者的格言物以稀为贵。目前,这一中国独有的历史遗物已在收藏领域中独树一帜。一本品相上等的第一版《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150元,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300元,而一些稀有版本系列(如少数民族版、盲文版等)更是价格不菲,“红宝书”已真正成为许多收藏者喜爱的宝书。
目前,一本品相上等的文革初期的大64开《红小兵》期刊,定价才2分钱,现价约为60元。连文革后期发行的《朝霞》、《学习与批判》等杂志的价格也在5~10元左右。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本64开的《战地新歌》第一辑,定价不过几角钱,现售价高达80多元。
文革时期的另一类报刊也很走俏,例如,在头版中印有“最高指示”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版和盲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等。
在作者收藏的文革炽热时期近千份群众组织的报纸、杂志、传单、期刊等宣传晶中,其文革小报可谓珍品中之珍品。它从各种不同的侧面,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各派群众组织的一些具体活动。30年后的今天,翻阅这些文革小报,对于我们反思昨天,珍惜今天,展望明天,坚定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些文革小报,都是笔者在文化革命炽热时期(1966年8月起至1968年11月止)于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大学)读书时收集的。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合编的《红旗报》(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也编有《红旗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红联总部编的《红联战报》、湖北和湖南两省群众组织联办的《两湖战报》、河南二七公社主办的《火车头》报、广西联总的《广西“4·22”报》、武汉群众组织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合办的《三钢战报》、华中工学院《新华工》报、《新湖大报》(湖北大学和湖南人学两校学生组织的小报皆用此报名)、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的《红四院》等共50多种。上述报纸大都是八开四版,其基本特征是:
文革小报的编排格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是版式随意更改。其开面有从左向右翻阅的,也有从右向左翻阅的。有的报头刊名放在头版之上,有的放在4版之下,有的放在头版左,有的放在头版右。甚至还有的把报名放在第二版,第一版则专排语录、标语、口号或伟人照片。简化汉字使用也不规范,在同一篇文章中,有的使用简化字,有的使用繁体字。甚至在一句话中,同一个字的编排也有繁简夹杂的,前后互不一致。二是图案随意编排。对被歌颂的人物形象任意神化,—个人头照占一版篇幅;对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用漫画形式任意丑化,或大鼻子,或矮个子,或大肚子等,对其人格尽其侮辱之能事。三是语言随意夸张。对被歌颂的对象任意拔高,“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四个伟大”、“大树特树”等;对被打倒的对象任意贬低,“砸烂狗头”、“火烧”、“炮轰”、“油炸”等。四是文字随意移位。对被歌颂的伟人姓名除加上美化的前置词外,还用醒目的粗笔体字或套红字加以渲染编排,表示权力至高无上;对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人名用倒排或斜排的方式,以示蔑视、否定,这样文面就显得不规范。
文革炽热时期群众组织的小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其文革内容的特点,首先是千篇一律,鼓吹极左。基本上都是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党内一大批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把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把人民群众打成“牛鬼蛇神”,使极左思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次是煽动群众,挑起武斗。有些小报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借口,拉山头、搞帮派,煽起武斗歪风,造成流血事件。有的小报还把“四人帮”的头目江青捧为文化大革命的“旗子”,加以歌颂和美化,使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的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人员伤亡的不幸事件。其三是长篇大论,空洞无物。这些报都是小报抄大报,层层照转照抄,通篇语录,整版“首长”讲话,懒婆娘裹脚,又长又臭。即使是刊登一些政治色采极浓的杂文、小品、小诗,也不过是为了拼盘和填空补白的需要。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们所编报纸的发行方式也就处于“四无”的混乱状态,即:一无法人代表。他们不登记、不注册、不办证、不审批,盲目地、自发地办报,头脑一热谁想办谁就去办,谁有人、财、物谁就能办报。办报人谁也不负责任,谁都负不了责任;二无发行计划。办报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份,绝大部分报纸都是当做传单散发出去,大街小巷满天飞。据测算,全国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铅印小报达1万多种,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三无固定时间。文革小报绝大多数都是不定期刊物,办报人想啥时印就啥时印,想怎么印就怎么印。有的印了2—3期就停办了,有的既是创刊号,又是停刊号,还有的能连续办1—2年。这些都和该组织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办刊条件等相关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四无准确地址。绝大多数文革小报办刊地址流动性很大,随着“串连”地址的改变而改变。今天北京、明天武汉、后天西安。编报人走到哪儿,报纸就办到哪儿。这些人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寻找政治派别和社会气味相同的伙伴采取独办、联办、合办等方式办报。独办一般是在各地拉“赞助”或“借支”款,以该群众组织的名誉办报;联办一般是同相同派别组织联合起来办报;合办一般是今天与这家合办,明天又与那家合办。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选择适当的方式办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