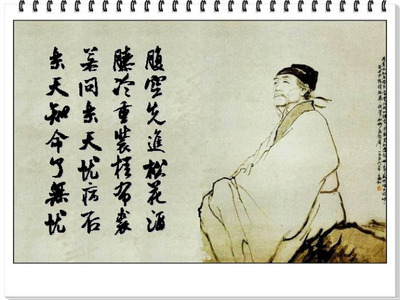写在前面
1978年,在中国整个20世纪100年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人们反复谈论并怀念的年份。其重要性,在于一个崭新时代在这一年被开启,犹如春风吹拂大地,人们往昔心灵深处的创伤开始康复并愈合——它的伟大和象征意义开始深植于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彻底否定。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且,被理论界誉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十多年以后,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评价邓小平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的艺术在1978年依然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将解放的期待和欢乐诉诸艺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化的承诺刚刚启动,物质世界的丰富还局限在想象中。在清贫生活中习惯了的中国人,眼界依然狭窄,很多东西尚未觉醒。但是,长久的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却培养了整个民族关怀政治的风尚。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忍受平淡的物质生活,但无法忍受对政治参与的剥夺。物质世界的改变需要时间和基础,而艺术的改变只需要观念的转变完全可以逐渐实现。
1978年,中国开启了一个不可改写的新时代,艺术在日后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有赖于1978年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它的启蒙意识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1979年作为关键的一年被载入史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万物苏醒,华夏大地显示出勃勃生机。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开始一次新的全面启动。而艺术作为时代的特殊形式,最为有效和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且,以传统的英雄情怀和启蒙话语参与了动员民众、共同创造未来以及走向彼岸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能忽视和取代的。
1979年,是中国艺术界最活跃、最重要的一年。1979年的中国,已经为现代艺术的萌芽和破土而出准备了土壤和条件。年初,北京出现了《迎新春——风景静物油画展》,上海出现了《12人画展》;年中,北京又有《无名画展》与观众见面。其中上海的《12人画展》倾向鲜明,几乎全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早期的风格与流派。秋天,首都机场壁画落成,由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鹤立鸡群,因画面上出现几个女裸体而引起不同反响,海外诸多媒体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与开放,也让人预感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同年9月,北京一群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自发举办了“星星”美展。这个以民间方式举办的展览使刚刚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国人感受到巨大的精神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人们在刚刚解冻的季节,感受到一种扬眉吐气的快乐。
1979年发生的一切,将成为艺术新时代的历史序幕。
2007年11月20日,“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隆重举行,各媒体以不同的版面和篇幅报道了展览消息。一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才意识到,这个被称之为“原点”的纪念展,距1979年的“星星”美展已过去整整28周年了。
28年前,我在长江人海口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参加一座全世界最具现代水准的钢城建设,那时媒体稀少,“星星”美展之类消息根本不予报道,我无缘亲眼观看“星星”作品。28年后,我专程赶往北京,瞻仰当年“星星”那一百余件作品。置身于展览现场,仿佛当年“星星”美展发生的一切就在眼前,让人似乎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前言简洁深刻:
“星星画会”在1979年和1980年分别举办了两届画展,在当时就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此开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道路。在今天我们对历史所进行的审视与整理之中,“星星”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原点。
在“原点”的展览现场人口,一段铁栏杆生硬而醒目,与整个环境极不协调。但是,我在进入展厅的一瞬间就明白这段铁栏杆的“用意”——其实,这是展览的策划者专门复制的当年中国美术馆东侧花园周围的一段铁栏杆,尺寸、样式一模一样——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忘记,1979年9月,“星星”美展的作品就是挂在露天这样的铁栏杆上。很快,那张“禁展布告”也张贴在这段铁栏杆上。策展人苦费心机,他是要在今日美术馆的展厅内还原一个当年“星星”美展的现场。让人们永远记住那段历史,同时,恢复正在丢失的记忆。
置身于展厅内,近30年前那个被称之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展览和具有颠覆性的作品,在眼前显得“陈旧”而“古老”,作品中原来的那股“新”、“猛”之气似乎早已散尽。整个展览的几个展厅内,没有装置、行为和录像等当今时髦的作品,更没有眼下风靡中国当代艺坛的观念摄影。展厅所呈现的,仅仅是绘画和雕塑。今日再看,当年那些影响整个中国的作品技术难称精湛,有些已经面目模糊,自然,还有明显对西方早期现代艺术的模仿印痕。即使如此,我仍能感觉到,当年“星星”依然在提醒当下观众: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时,这帮没有学历、没有接受任何专业训练的业余美术爱好者勇敢地夺过历史的接力棒,在刚刚解冻的中国,冲破种种束缚,创办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民间方式举行的美术作品展,从此开启了中国艺术自由的大门,拉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大幕。
中国当代艺术那漫长的青春期,正是从“星星”起步……
“墨墨”之火
1979年,尽管邓小平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为艺术创作的松动和风格多样化准备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条件,但艺术机构的运行机制还在原有的模式上进行。尤其是渴望创作自由的艺术家,依然没有展示作品的空间——因为,思想领域的解放和开放尚处在开始的状态中。尽管“伤痕”美术中的许多作品直接抨击了现实中的黑暗和痛苦,但其中往往被辛酸回忆的泪水浸泡并软化——留给人们的,只是指向已成为历史的表象及其产生根源的思考。
发生在1979年秋天的“星星”美展,曾给无数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和视觉冲击,也使无数中国人在一群追求自由的年轻人的实际行动中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如今,“星星”美展过去近30年,这个当年轰动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件正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消失,甚至,还有人根本不知其事。据说,在文化领域还有人无视它的存在,以及其中的价值和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陡峭石壁上攀登时。身心疲惫而造成的失忆。难道,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遭遇吗?!因此我想,只有将历史牢牢镶嵌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我们在反思昨天和面向未来的时候,才会清醒,才能大步向前。
那个被称作“原点”的纪念展,将我的思绪带回30年前,带回中国改革开放那个躁动的前夜,也带回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历史,往往以人们预料不到或措手不及的方式选择它在特定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换句话说,有人千方百计想进入历史,但一生未能如愿;而有人,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前行走时,无意中被历史接受。1979年初夏的一天,北京一群不甘寂寞的年轻后生,在东四14条76号的一个大杂院内,紧张而兴奋地商议事情。其实,这是一个不经意的夜晚,他们商讨要举办一个展览,一个完全自发组织的民间展览。或许,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简单、天真的想法和粗糙、懵懂的行为,已经站在中国现代艺术的最前端,正好站在中国历史的门槛之上。
1979年春天某一日,《今天》杂志举行诗歌朗诵会,结束后,一个名叫黄锐的诗人或称画家显得筋疲力尽,他感到一种从头到脚的失落——因为,在朗诵会上诗人出尽风头,但看不到艺术家的存在。不久,黄锐去找一位拄双拐的工人马德升,准备一起做个展览。毕竟,追求伟大和向往成功是每一个男人的天性。当年的“星星”美展就是从这种“不经意”中开始,历史那沉重的大幕也正是在这里被拉开。
“星星”美展最初的动议和想法来自黄锐和马德升,最早的成立会议是在北京东城东四14条76号黄锐的家中举行。“星星”成员钟阿城有这样的文字记载:
如约赶去参加筹备画展的聚会,地点在东四14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西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灯左马德升,灯后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要紧处,就挤到门口。(《中国现代艺术史》吕澎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黄锐在后来的回忆中,记述了当时选画的经过:
由我和马德升先看作品后定人选。在王克平的家里是戏剧性的,我和老马在他的屋子里,惊讶有不少奇怪的木雕。我说:“在展览里你的作品会最轰动。”他说:“是吗?那我就参加了。”可是他连最轰动的画家马蒂斯、康定斯基都不知道。在严力家,我们是去看李爽的画的。我仅知道严力是诗人。除了李爽的画以外,还有幅风格别异。严力说是他的画,并问:“怎么样?”“不错,有新东西。”我们回答。“来参加展览吧!”严力被突然的邀请乐坏了,据说当晚就喝酒喝出了毛病。(《中国前卫艺术》刘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979年初夏,“星星”美展的参展作品筹备基本就绪,发起人黄锐和马德升向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正式展览,刘迅在观看了作品之后表示同意安排,但北京市美协展厅日程已经排满,“星星”美展要等到第二年才能腾出展厅和时间。于是,“星星”成员商定,展览将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街头公园举行。
1979年9月27日,“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与此同时,“星星”美展正式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举行,所有绘画作品全部挂在公园的铁栏杆上,引来过路行人和大批观众驻步观看。在展出的150余件作品中,有油画、水墨画、钢笔画、木刻和雕塑等,观众对此产生极大兴趣,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专业美术工作者前来参观。甚至有观众评价,外面的作品比里面的(指美术馆内)作品更精彩。展览引起极大轰动。第二天,公安部门出面干涉,所有艺术家撤走展览的作品。9月29日,“星星”美展正式遭遇困难,参展艺术家王克平这样记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我一早骑车到美术馆,发现一些角落多了些警察,预感到不妙。又发现我们挂在美术馆前的广告牌也不见了。我奔向小花园,只见三幅大布告挂在铁栅栏上,几个警察背手站立其间,三幅布告内容一样用毛笔抄写,下边盖了两个大红章。
布告全文:
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秩序。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1979年3月29日《通知》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內,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处理。
此布。
(《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出版)
展览被撤以后,“星星”成员曾通过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同各方进行联系和协调,结果均告无效。“星星”们似乎感觉到,展览被彻底取缔。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理想与激情、真诚与信仰没有得到认同。
走进体制
可以准确地说,“星星”美展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体制外,以民间方式举办的艺术作品展。也许,正是这种民间方式的特殊性,惊动了有关部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公安部门的“禁展”决定激怒了“星星”。9月29日晚,“星星”成员做出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日之际举行一次游行活动。9月30日,刘迅出面调解,要求他们放弃游行,“星星”成员执意坚持。
1979年10月1日,“星星”部分成员与一些志愿者集合,在马德升发表讲演之后,游行队伍从西单出发,很多人加入其中,原有的23名“星星”成员,8人走进了游行行列。拄双拐的马德升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大家高喊“艺术自由”的口号。“星星”的主要发起者黄锐回忆道:
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走到府右街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警队,人群立刻散去,只剩下孤零零的30个人,连奋力喊出的口号也被风吹散了。散去的人躲在街角,退后2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个场景令我一生难忘。(《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出版)
游行队伍被警察驱散。
可喜的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游行虽然遭遇阻拦,但却获得意外效果。1979年11月20日,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突然通知“星星”成员,告诉他们展览可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公开举行,时间是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展期10天。
展览由23位艺术家组成,163件作品参加了展览,其中有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干预生活的作品,另一类是对形式的追求和探索。干预生活的作品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应。展览获得极大成功,北海公园画舫斋那清净、偏僻而古老的庭院挤满了前来参观的人群——还有许多人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人民日报》专门为这次展览刊登了“星星”自己出资的广告。展览在最后一天,共卖出8000多张门票。1980年,《美术》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星星”美展》的文章,同时刊登5幅“星星”美展的作品。
1980年初夏,“星星”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且,在北京市美术家协会正式登记注册。这就意味着,“星星”们由此走进体制。于是,第二届“星星”美展得到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先生的鼎力支持,并且,同意于8月20日至9月4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人民日报》8月26日再次刊登了“星星”美展的广告。展览又一次引起轰动,并延续到9月7日结束。在展出的16天中,观众多达8万余人,同时,创下了日卖票9000多张的记录。
今天,我们来讨论“星星”美展的展出和游行方式是否合法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无论官方或民间,历史已经肯定这一现象和他们当年的行为。从“文革”专制的黑暗中苏醒的人们,第一次呼吸到艺术自由的空气,第一次拥有了创作自由的感受。同时,在朦胧中感受到一种新的价值标准即将被确立。
遥想当年,所有的展览必须通过美术馆或美术家协会的组织方式举办,纯粹的民间展览根本不允许存在。“星星”美展以民间方式举办和走进中国美术馆的过程,形象地层现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现代艺术的道路。从民间到官方,从反抗到被认可,从街头展览到“星星”画会的正式成立并登记注册,他们堂而皇之走进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殿堂,而且从内心渴求被体制和权威承认的愿望得以实现——其实,他们最初将之视为一种自我价值的追求。黄锐、马德升和王克平在第二届“星星”美展之后成为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应该说,最初的“星星”是有尊严的艺术行动。那么,从展览走进美术馆和部分成员加入美协这两件事情上看,个别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现象上看,有妥协之嫌。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艺术群体或流派的经历比“星星”更加激动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星星”艺术家的价值远逊色于“星星”美展组织者的价值。1984年以后,中国各种各样的展览风起云涌——无论官方或是民间,很多功绩当属“星星”事件的影响!最早的“星星”美展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抗争,“星星”在美术馆东侧街头花园开展的当天,中国美术馆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同时开展,毫无疑问,这是策展人的蓄意安排。虽然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但是观众自然将馆内馆外的作品进行比较。10月1日举行的游行将这一事件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国外媒体不同角度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当第一届“星星”美展稍后正式展出时,在北京引起巨大轰动,美术界一些重要艺术家如江丰、刘迅、华君武、蔡若虹、叶浅予、黄永玉、张仃、吴冠中等都参观了展览。江丰告诉他们:“美术学院内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同样可以出艺术家。”这句话,是对这些在野艺术家的肯定。1980年第二次“星星”美展依然获得成功,中央美院学生会邀请部分“星星”成员走进美院讲堂。10月下旬至1981年初,他们接受邀请并走访了26个城市,山西晋城、西安市美协、四川美院、贵阳市美协、广西师院美术系、桂林市美术学校、广州美院研究生部分别举办了“星星”美展及当代艺术讲座。不久,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种现代艺术群体。“星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来的新潮美术运动开辟了前进道路。
1984年以后,“星星”散伙,成员各奔东西。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10年”纪念展并出版画册,意大利艺术史学家苏立文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十分中肯地评述了出国后“星星”之状态:
今天这里展出的艺术家们仍在从事创作,但他们现在要征服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对手。现在再没有明确的对象,如文化官僚,去供他们果断地挑战。他们现在的敌人更阴险,更难对抗。因为这些敌人是孤独和自我怀疑;是轻易得到的名望与财富;是无闻的孤寂与贫困;还有东京、巴黎、纽约艺术世界的竞争与物质主义。(《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出版)
无论如何,30年后当我们重新回顾“星星”美展时,我们通过30年间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对“星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星星”美展发生在“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前夜,中国信息环境完全封闭,展览由一群年轻人自发而成一一这是一种可贵的盲动状态,是本土屈指可数的艺术“另类”的一时骚动,是对陈腐单一的文艺教条的挑战。回望历史,我们发现“星星”美展最关键的是这群年轻人率先撞开了1949年到1979年30年来中国文艺管制的缺口。从此,缺口被滚滚而来和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大。今天,我们回顾“星星”美展时都会发现,如果没有当初的缺口,就不可能有汹涌激流,更不可能发生后来一系列的事件并涌现诸多艺术群体。尽管当年他们幼稚、混杂、粗糙一一甚至,他们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去做,且做得最早。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当年“星星”美展,深刻影响今日我们目所能及的中国当代艺术,虽然,至今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艺格局并未形成,但单一局面早已打破——中国不再有一统天下的艺术格局。遥望当年,那帮与我年龄相仿的“星星”成员,胃里装着缺少油水的粗食,“无限渴望他们当时并不了解的‘世界’,每件作品的物质感和混杂的观念,渗透着可敬的营养不良,那是我这一代熟悉的匮乏与不甘”(陈丹青语)。他们真诚渴望了解外面的陌生世界,他们不甘寂寞,他们对依然存留的旧教条全然不顾。今天,还有哪位年轻的艺术家敢放言比当年“星星”们还真诚,还有那般粗糙与直率?我敢说:一个没有!艺术家与作品
介入和参与,是每一位“星星”成员的社会责任和强烈愿望。“用自己的眼睛”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观察和认识世界,是每一位“星星”成员的探索与追求——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作品还很幼稚,但对于他们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只要能表达真切的思想感情,对于一切形式,首先采取“拿来主义”。正如主要成员王克平所说:“珂罗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
在第一届“星星”美展的前言中,艺术家们明确写道:
世界给探索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
岁月向我们迎来,没有什么神奇的预示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生活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把时间从这里割断,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不是艺术》栗宪庭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年8月出版)
从1979年到200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成千上万个当代艺术展中,“星星”肯定不算最好,但“星星”最为耀眼。那是个人内心充满愤懑、焦灼和批判的年代,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触动了每一个渴望变革与新生的神经。王克平从荒诞主义戏剧的语言转换出中国根雕的某些方式,塑造了许多被压抑、被扭曲的形象,语言上有明显的创造性。如他的雕塑作品《沉默》,巧妙利用树根造型,雕刻出一个嘴被堵塞,眼被封闭的痛苦形象,给人一种挑衅的感觉。黄锐的《新生》,画的是圆明园遗址,艺术家将圆明园的几尊残存的石柱通过变形描绘成类似于人的形体,色彩鲜明而强烈,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仿佛向后人告诫:新生是一种希望,在昏暗的痛苦中相互搀扶并站起,这就是希望和力量。正如展览的前言所写的那样:“我们不能把时光从这里割断,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态。”马德升的木刻《息》,以低垂的地平线横贯画面,采用了大面积的黑色。一丝暮色显露在天边,映衬出一副牛犁和一个赶牛的人形,近景是一张老人的脸和一只被拉长的手,凸现了佝偻状人形的挣扎状态,画面充满干涸和疲惫,表达了艺术家对农民的同情,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而他的另一幅木刻《六平方米》却与《息》相反,展现了一个属于艺术家的个人空间——竭力想在一个狭小的有限空间里把自己同作品之间的距离拉大,造成一种张力的效果,给人一种民国时期左翼木刻的感觉。杨益平塑造的落寞、怀旧的知青形象,带有强烈的疏离感和超现实意味。这些作品都较早借鉴了西方超现实主义语言模式——其实,这些依然是今日中国当代艺术中广泛使用的语言方式。所有这一切,在梳理当代艺术史时,都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比如发起人马德升,继承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木刻运动的传统,关注社会底层,关注民生痛苦,语言上吸收德国表现主义木刻的方式,他在木板上塑造的农民和平民形象,简洁、粗粝、纯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严力是朦胧诗人,其画也像诗一样善于使用意象,如他的《对话》,酒瓶子上的空缺造型,留下的仿佛是对话者双方对话过程的意象。毛栗子画的一幅平面的“墙”,用超写实主义的技法,留下了如纪实摄影般的那个年代“墙”的标本。甘少诚的雕塑继承汉代雕塑的简洁和大器。包泡强调材料和造型对比的抽象雕塑,以及阿城简练流畅以线造型的平民肖像等,尽管时过近30年,但依然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长思。
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史,如果遗漏了“星星”,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星星”的两次展览,对粉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多年的思想禁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敢于用自己心灵的语言将苦闷和思索表达出来,将自己心灵深处的创伤直言于观众——应该说,这是思想解放的开端,也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因为,它与这个历史时期民众共有的伤痕和渴望相同,因此,与思想解放极为吻合,从而也使它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尽管当年“星星”成员在艺术见解上存在分歧,但是,在“要把感情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看法上颇为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星星”美展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开始。
“星星”中的许多成员,大都生长于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10年“文革”使他们的命运在一种强烈的颠簸中度过,同时也开始了他们独立的生活旅途。
拄双拐的马德升,原是北京商业机械研究所绘图员,出生于工人家庭。虽然,上天没有给他一个健壮的体魄,但却给了他坚强的性格。这位身有残疾的人曾拄着双拐多次登上北京香山,还攀登过泰山等名山大川,展现了一个强者的形象。除了吃饭以外,他将所有的钱和时间都用在绘画上。也许,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精神寄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在知识领域中有许多空白,但作为一个人,我的爱憎感情是健全的。”于是,绘画成为他倾吐感情的工具。当他看到珂罗惠支的版画之后,猛然领悟并确定了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要有良心,不要看风头,阿谀逢迎,出卖灵魂,要把自己的爱与恨鲜明地表达出来。要用画笔从各个角度去反映社会,或歌颂、或揭露,都应该是这个时代的真情实感的写照。”他的作品给观众一种人生哲理的启迪。黄锐,《今天》诗刊创始人之一。黄锐写诗,在诗人眼里,他的身份是一名画家,或者是一个会写诗的画家。早年曾在内蒙古插队,几次高考因种种原因落榜,回北京后当锅炉工。画画顺应了他的兴趣,并且,毫不犹豫选择了抽象艺术的探索之路。他写诗、写小说,崇拜毕加索不断否定自己的革命精神,自己也成为艺术上不断变化的追求者。钟阿城与新中国同龄,父亲是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菜,是电影界首席大“右派”,“文革”期间家庭遭受巨大冲击,在云南边陲插队整整10年,饱受种种苦难,但他却成为一个精神上充实的人。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一个美学见解:给人有真实感的艺术,就是有力量的艺术。他的作品全部由线描完成,在刻画人物上,表达了一种力度。曲磊磊是作家曲波之子,父亲是小说《林海雪原》作者。他从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及传统文化熏陶,插过队,当过兵,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在艺术上经过早期的模仿阶段和后来的“自我表现”阶段,在“星星”成员中,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飞行并非为了觅食,而是为了不断调整自己飞行的姿势,去追求飞行的高度和速度。”王克平的父亲当年是天津文联主席,从小家庭环境良好。王克平敏感、锋芒毕露,作品总是给人一种辛辣的讽刺和无情揭露。如他在展览中的雕塑作品《沉默》,用木塞把人的嘴堵住不让人讲话,憋得喘不过气来,许多作品都是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总之,这是一群较早从现代迷信中觉醒了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相信必须通过自己的头脑去思索,因此他们的艺术也被认定为“思考的一代”,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在“星星”的大多作品中,在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中冲破禁区,正视社会现实,正视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丑恶、虚伪和冷酷,用艺术大胆干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大众心声。
当星星在黑暗的夜空中簇拥在一起的时候,它们能发出一个星系的光亮。然而,当他们各自离散,各奔一方时,它们的光也许不再明亮。当它们穿破大气层的那一瞬,它们发出耀眼的火花,哪怕火花之后是长久的寂寞,人们也永远会铭记火花闪烁的瞬间。
最 后
1979年早已离我们远去,过去30年间国中涌现无数展览,也有“85美术新潮”和1990年代的新艺术运动,还有许多今日在艺术市场中身居高价的成功者。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星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真正先驱,尽管光亮微弱,毕竟划破夜空。
如今,各类艺术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既安全还有规则的当代艺术中寻找自己的一席领域。他们顺应着本土体制和境外在华机构,以各自的不懈努力和“招数”拼命向“彼岸”爬行——他们今日为艺术做出的选择与回报或效益紧密相连。30年前的“星星”心中没有混乱,只有一腔热血!往昔“星星”倔强还粗野的性格如在今时很难适宜,甚至还会遭到白眼和唾弃——因为,土壤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流失。失去土壤,还谈什么栽培、种植和收获!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现代艺术中的一切变革,都紧紧镶嵌于思想解放这一主题之中。其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由空间。当年“星星”美展,正是大胆追求自由之壮举。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我想,这就是我们怀念并景仰“星星”的真正理由。
历史学家利昂,格劳伯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并不是一件过去的东西,而是被推挤到我们眼前的正在发生的事件。”上述零散文字,我不知道是什么,其实是什么并不重要。我想做的,权当是一个不完全的证据和不完整的记录。当然,其中更多的,是我对“星星”的敬意,以及对一个渐渐远逝的时代的怀念!
责任编辑 孔令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