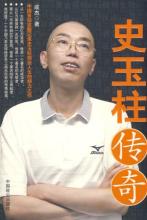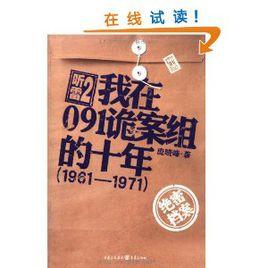这是我1962年参高考时的准考证,可以看到,考试时间是7月20日。印刷用纸是一种极其粗糙的浅黄色牛皮纸,相片是用钉书器钉上去的。
1962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我的高中三年都是在饥荒年中度过的,挨了不少饿。
那时的教育宗旨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然教育培养的是劳动者(那时的“劳动者”的概念与现在也不同,专指体力劳动),我们参加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每学期都得去农村劳动。但时逢灾荒年,劳动的时间和强度都少了不少。但是在教学上并没有重视多少,因为还要“又红又专”,要花大量时间去学习政治。
当时中学生的粮食定量为每月30斤(其他居民为27斤),再加上食油只有三两,蔬菜几乎没有,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来讲根本不够吃。为了减轻体力消耗,教育部规定,中学减少课时,可以不上体育课,我们学校规定下午可以不上自习,下课即可回家。所以学习和高考准备的是时间是很少的。
当时没有什么课余活动,放学回家我就喜欢看书,并把书上没做的练习题都做一遍。
那时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考大学热,人们认为考大学和不考大学没多大区别,大学毕业到工厂里拿的工资和工人差不多,还要多付不少学费,还要耽误几年拿工资的时间,不合算,不如早工作早拿工资。所以当时我们班参加高考的的人还不到班上的一半。
高考复习开始了,时间只有两个多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复习资料,除了原来的课本,只有老师自己编的复习资料,油印在原来用来写标语的彩色纸上,很难看清楚。
1962年7月20日,考试开始了,我们既没有紧张情绪,也没有兴奋感。不同的是家里给我带了一个纯玉米面的窝窝头和几块咸菜(平时吃的窝窝头里掺了不少野菜)。学校派了几辆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考场。
那年考题不难,都是些基本概念,比平时小考都容易。那年的作文题是两道:《雨后》和《说不怕鬼》?后者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我选择了后者,议论是我的长项。在理科方面我没感到哪道题不会做,也没发现那道题做错了。
高考结束了,好像没几个人去讨论考题和考得怎样,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去哪弄点吃的。我和几个同学去了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的菜地,义务干一天活,可以买100斤皎瓜回来。这样我们干了几天,当我母亲看着我嗤牙咧嘴地地背着100斤重皎瓜回来的时候,心痛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当我们正为吃的而费尽心机,差点忘了还有考大学这一回事的时候,突然一天一个佩戴海军上尉军衔的军官来到我家,说我已被哈军工录取,但是档案被北大拿去了,如果他们给你发通知的话你不要去。原来,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但同时学校又为我报了一所很有名气军事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军校不占报考志愿名额,提前录取,考不上不影响你原来报的志愿的录取。这个消息让我惊喜万分:我父亲、母亲、姨和叔都曾是解放军,我也渴望当解放军,能同时上大学,给家里解决不少经济压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啊!
1962年,哈军工招生简章上的宣传照片,这三位学长现在何处?
没几天就接到了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
过了两天,那位上尉军官通知我们到沈阳集中,并把我们带到了学院,于是我就开始了五年的解放军大学生生活。 哈军工给了我们良好的生活待遇,但是多重死的教育思想和繁重的学习任务让我们苦不堪言,但是这严酷的训练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时代变了,现在大多数人们再也不用为吃发愁了。家长、学校、社会都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希望他们成才,希望他们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我羡慕他们,祝福他们!但我依然无悔于我的高考之路。
高考——终于考完了!(图片来自网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