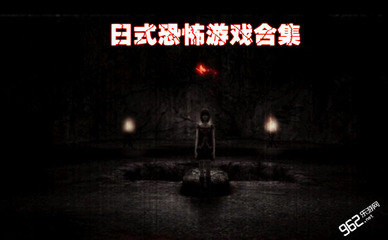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元顺帝时,丞相脱脱奏请哈麻担任了“统战部长”,哈麻在得到元顺帝的宠幸之后,偷偷向他推荐了一个会“运气之术”的印度僧人,这种“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法术叫做“演揲儿”。而后,资政院使、朝鲜人陇卜又向皇帝进献了一位西番僧人,这位西番僧向皇帝传授了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即藏传密教中的男女双修之法,这种修法听起来像是一场君臣共演的群交派对。
此外,《庚申外史》中还提到了一种名为“十六天魔舞”的藏传佛教仪轨:“[正当红巾军兵临大都城下],而帝方与倚纳十人行大喜乐,帽带金佛字,手执数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璎珞,品乐器,列队唱歌金字经,舞雁儿舞,其选者名十六天魔。”蒙古皇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因为“酷嗜天魔舞女”,不惜在宫中挖地道,每天“从地道数往就天魔女,以昼作夜”云云。

由此可见,《庚申外史》中记载的出现于元朝蒙古宫廷中流传的藏传佛教修法其实有三种,一种是所谓“演揲儿法”,另一种是“秘密大喜乐禅定”,还有一种就是“十六天魔舞”。但可笑的是,这些记载后来统统被明代修《元史》的人抄进了正史,而且还抄错了,据《元史·哈麻传》中记载:
初,哈麻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故有宠于帝,与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禡等十人,俱号倚纳。秃鲁帖木儿性奸狡,帝爱之,言听计从,亦荐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 “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 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如果将正史中的这段话与《庚申外史》中的记载对比,就会发现野史中“演揲儿法”与“秘密大喜乐禅定”这两种不同的修法在正史中被合二为一,而且“皆房中术也”,“十六天魔舞”也被描述成一种皇帝寻欢作乐的“淫戏”。因此,一段莫须有的野史就这样变成了元末宫廷修习藏传佛教史的官方说法。
中西方对藏传佛教的污名化想象
从此,藏传佛教也一变而为“房中术”、“淫戏”的代名词,甚至还是导致元朝不足百年而突然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元朝末年就有人总结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一统天下,遂使“中国一变而为夷狄”,而西藏喇嘛于蒙古宫廷传播的密法又使“夷狄一变而为禽兽”,遂使“堂堂人主,为禽兽行,人纪灭亡,天下失矣”。
但仔细考察《庚申外史》中记载的君臣言论,像“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显然是典型的汉人奸臣挑唆末代昏君的老生常谈,根本不像胡人说的话,因此无论野史还是正史,关于元末宫廷所传藏传密法的记载都不可信,唯一可信的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那些非汉语词汇,比如“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等,因为它们都是当时的人按照胡语发音用汉语记载下来的。
遗憾的是,虽然以上这些故事以讹传讹,真假难辨,但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元以来的汉文文献中,不断出现这些故事的新版本,并且常常流为色情小说的主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为明代著名江南才子唐寅所写的色情小说《僧尼孽海》。
《僧尼孽海》有一回名为“西天僧、西番僧”,即是根据《庚申外史》中有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宫中修“秘密大喜乐法”的故事添油加醋而成。有趣的是,唐伯虎还把汉人房中术经典《素女经》中的内容用来解释所谓藏传“秘密法”,将之演绎为龙飞、虎行、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鱼游、龙交等号为“采补抽添”之九势。
这种色情化的想象源远流长,直到当代都可见其例。1983年《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部题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短篇小说,它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作者于西藏的所见所闻。“实际上,马建在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大部分故事根本就不可能见于或发生于1980年代的西藏,它们不过是一些现代版的《僧尼孽海》式的西藏故事。”沈教授说。因为这部小说讲述的五个故事都涉及怪异、不伦的性行为,特别其中对三代乱伦和宗教仪式性的性行为,即上师以灌顶为名与女弟子(女活佛)发生的性行为的细致描述,而被在京藏族同胞们视为侮辱而演变为一场政治事件。
不仅中国人对藏传佛教存在误解,外国人也一样。13世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方面称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另一方面则批评西藏人是最肮脏、最没有性道德的人,比如为了换取一件可以说完全不值钱的小礼物,藏族母亲能随时把自己的女儿献给外来商人、僧人等等。年轻女子获得的这种礼物越多越受人羡慕,马可波罗甚至挑逗性地鼓励西方青年去西藏,随便享用白送给他们的“室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