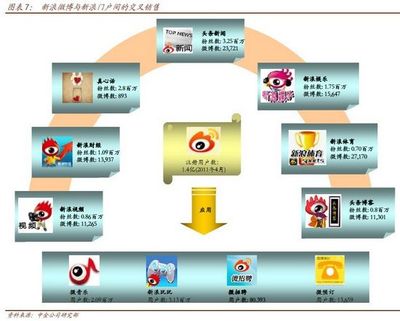在全国首个高调登场的私人医生工作室开业的现场,张黎刚先生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改和医疗服务业形成了一个‘堡垒’,不管是民众、政府,包括医生团体、医护团体都希望打破现有的瓶颈,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体系。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政府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探索,也有很多政策方面的鼓励,特别是政府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希望能够真正解放医生……”但是,不尽人意!说实了,就是长期以来政府定价把医生的服务价格定得低得不能再低了,却又紧紧把医生圈死在药品、检查等创收的商业模式上。这个“堡垒”就是半市场而无公益的体制。
就目前公立医院所提供的服务而言,它的服务与社会办的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在服务价格上没有多大的差异,而服务的价格与内容(产品的属性)又极不相称。公立医院在提供“半公共产品”(自负部分也不少)的时候,又为要求专属服务的人群提供“私人产品”(特需服务),而这种“私人产品”不仅不能体现市场的真正价格,也没有体现医生真正的价值。甚至我们很多人把有钱没钱与医疗检查联系在一起,认为“ta有钱”,就该多做检查,“劫富济贫”。这种制度既扭曲了医生的医疗行为,也违背了政府办的公立医院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最近,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有一篇评说中国医疗60年带给世界的教训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专业主义精神”。作者认为,中国医患矛盾的对立清晰:一方面是严重缺乏医疗保险覆盖的病人,另一方面是医院全神贯注于“创收入、图生存”,和(这种制度下)医疗从业人员无“专业主义精神”。实际上,普遍流行的新经济规则和激励机制,强烈鼓励医生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主那般行事。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对医疗系统并没有完全放开不插手了,它还牢牢控制着一个要素——定价权。政府试图通过压低价格,确保民众在缺乏医疗保险的条件下也能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控制的定价权真正能压低的,只剩下医生和护士的劳动力价格了。与此对应的是,政府却给药品和技术设备相当“慷慨”的定价,例如高级影像学技术(与药品公司和设备供应商的公关能力和议价能力相比,医生和护士的议价能力实在是太低了)。政府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医院和医疗从业者大量增加药物和顶级医疗设备的使用,推高了医疗服务的费用,却降低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使没有医保的人看不起病。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这篇评论并非一家之言。前几天,德国政府年轻行政干部考察团在访问我省(广东省)的时候,很巧妙地问了我一句话:“尊敬的廖巡视员,我想学习你们中国的设备如何惠及百姓!”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是讽刺呢,还是什么?他们真的想学习中国?我很坦率地跟他说:“很抱歉,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在药品定价和医疗检查上的制度非常严谨,监管也非常有经验。”目前,我们医改的一些理念来自于德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体制有点不伦不类,最为遗憾和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学到德国和美国两种体制的核心价值。医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仍在努力追求。
在说到医生与医院的关系时,我不得不再举一个例子。五年前,纽约的一家区域性医院,也是当地唯一的一家医院倒闭了,开始引起了市民的恐慌——“我的病谁来治?”他们的研究显示:事实上,这家当地唯一的一家医院的倒闭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很大的改变,医院倒闭并没有对死亡率、医疗花费、住院时间产生影响,对急需救治的病人如外伤、中风和心脏病患者这些脆弱的患者也没有影响。另一个指标表明:出院后三十天之内再回医院的人数减少了。还有,社区内因住院治疗三十天内死亡的人数也下降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