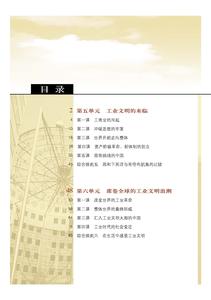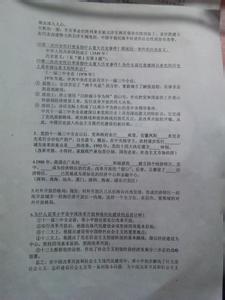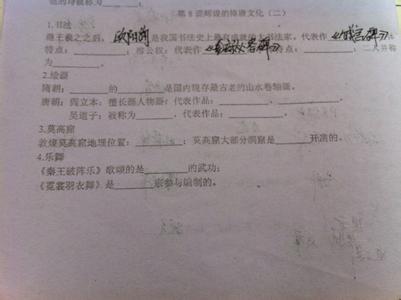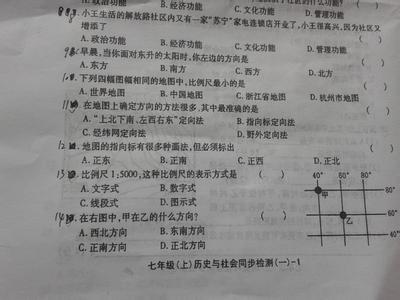今年年初,《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一书再版,并邀请雷颐、郭世佑、崔文华等知名学者、作家名人举行了一场座谈会。会上,学者们围绕这本由文史研究大家王伯祥和宋云彬先生合编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展开讨论,畅谈再版的意义、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演变,并延伸到历史观的发展、历史教科书能不能去政府化、学历史的意义等问题。以下是活动的全部内容。
刘丽华(主持人、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下午来新星出版社来参加我们的读书活动。今天下午的读书活动是“从一本历史教科书说起”,请来的专家都是对中国近代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今天刚一开始 ,策划人对我说,刘老师,首先这个谈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一本80年前的教科书在现在这么受欢迎?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近些年来我们很多老书都受到了欢迎,比如说我们高晓岩老师出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也是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反响非常好。这说明这些书都已经进入经典行列。为什么百、八十年前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的欢迎呢?下面我请某位学者老师来先谈这个问题,或者大家开始讨论。
雷颐:教科书的变化与教育制度紧密相连
雷颐:我来讲一下,我也没有对这本教科书做更多的准备,但是在耳濡目染下,毕竟我是研究近代历史的,我夫人就是研究近代教科书,研究清末明初教科书,很多情况我都是听她讲的,家里有很多资料,也就多少受点影响。这本教科书的作者之一宋云彬,他的的那个《宋云彬日记》前一段时间出版了,非常受欢迎,他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是浙江省文联主席,再后来被打成右派,写的《宋云彬日记》。王伯祥后来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老先生。
从这本教科书谈起,它是从三十年代编的。在有新学制新学堂以前,中国是没有分科的教科书的,就只有传统的四书五经和发萌的千字文这种,从19世纪末,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涌来,新学制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觉得中国比较落后,觉得日本整个学制,整个现代化学校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虽然没有废科举,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办新学校了,新学校就得有教科书,但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教科书,从来没有过分科,所以开始的教科书都是大量翻译日本的,从1903年左右,中国人开始做了一些尝试,开始编教科书,编教科书就得按照现在学校的分类的,有历史数学之类的,在历史教科书中比较早的就是《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教科书大致而言是有些进步的,毕竟这些教科书是分了科的,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管写得好不好,毕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教科书,但不可避免的还是按照王朝史来写,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出了一本历史教科书,更细了。1906年开始废科举,这时候学校已经很多了,基本上按照小学中学来编历史教科书,紧密的扣紧了当时的新学制的改变,所以教科书的变化是跟教育制度紧密相连的,我们能从教科书的变化感受到教育制度的变化。可以说1904年的这个历史教科书是比较正式的,和1903年相比,虽然只过去了一年,但内容丰富了,虽然也是按照王朝史来编的,但毕竟也算是一个大进步。辛亥革命时历史教科书从内容什么来说变化并不是很大。较大的变化是从1922年实行了新学制开始的,从前我们的学制是仿照日本的,1922开了一个教学会议,胡适蔡元培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美国的学制比较好,那时候确定了“六三三学制”,直到现在也没有变化,这八九十年间曾经很多次想改变一下,但改变都不是很成功,都退回去了。有的学校,像北京的景山学校想学学苏联的十年一贯制,从小学到高中十年,也就这一个学校,试试也还是不行。有的地方想把小学缩短,也不行。
新的学制需要新的教科书,1922年胡适就作为嘉宾(虽然不是他编写,但是他是作为嘉宾的),一批最有学问的参与了新教科书的编辑。1934年出了这本教科书,这是非常棒的。这本教科书也反映当时的一些特点,实际上是反映了编者自己的一些特点,当时的编者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书里。
我注意到了原编者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观点都加进去。比如说他有一个解释,完全是按照列宁的解释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讲中俄关系,言简意赅,大事都讲到了,普通的一个教科书很难做到这点,他讲到沙俄对中国的侵害讲了很多,他说,那时候的俄国,完全是帝国主义,这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同。我看到就在想,编者怎么写这段呢。他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一方面他承认了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嘲讽的态度。
我反复强调这本书是1934年出的,当时正是国民党围剿的时期啊,为什么这个作者的观点,比如谈到苏联,谈到俄国,非要加一句“和现在的苏联主义”,这反映了什么呢?实际那时候的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的教科书都是审定制,教育部有一个纲要,符合这个纲要谁都可以编,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是固定制,就是由政府定制这一本,你必须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之后就是固定制了,从90年代初开始改革,虽然还是很严格,但已经开始向审定制发展了,允许历史教科书有好几个版本,北京版,不同的版本。这个教科书这么短,却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包含了,介绍的相当的简洁,文字也很好,白话文字上又有文言,这种文体值得我们学习。
我觉得编者前言写得非常好,又简洁又详细,把这个教科书的特点介绍的非常好。
刘丽华:谢谢雷颐老师的发言,下面郭老师继续谈,他也是教历史的老师,原来是在政法大学,后来调到同济大学。
郭世佑:历史教科书能不能去政府化 启发真正的历史观
郭世佑:按照顺序来我压力很大,感谢新星给这么一个机会。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千里编辑发出感慨,像千里这样的老编辑人,编辑的眼光是比较独特的,他不止一次得跟我讨论关注民国时期的那批历史书,我和雷兄是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我中学时候是没有学过历史的,都是取消牛鬼蛇神帝王将相那一套的,就背毛主席语录。历史课就被毛主席语录取代了,外语就更不用说了。说实话至少我自己是属于对历史有误会才学的历史专业。到大学的时候也没有那个老师跟我们提开明书局的历史书。我的本科是林增平先生,林先生提出陈恭禄的书,我们自己书店去翻,真的是黄色的书籍,从头到尾都是黄色的。看了这本书,我的想法是中学的时候如果有这本书那对我们历史的构建就好多了,大学再看到话稍微会浅点,我刚才翻了一下还可以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出来。
我作为近代史的研究者,可能看近代部分会浅点,但是古代部分很精炼,它的历史观刚才雷兄讲的非常清楚,用马克思的观点进化论的观点,淘汰我们以前那种叙述方式。它在当时很有新意,有一些理论的构建,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梳理的很清楚,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我经常遇到一些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让我们来推荐历史方面的书,从现代人编的东西来看要找这样一本书很难,现在有了新星出的这个书,可以让一些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用比较准确的信息知识来了解这样一段历史,这是很有帮助的。我不知道这本书的销量怎么样,但它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很大一部分读者的需求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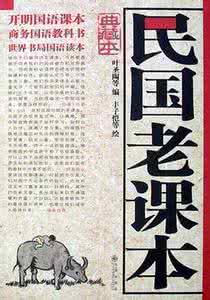
座谈会现场
第二点是当下民国史很热,这个热主要是两个热,第一个是民国本身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很关注。还有一个热是民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民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这个也很热。包括这本开明课本,其实我们看的是民国人如何述说他们的历史,民国人如何认识汉字,或者民国人如何陈述他们的历史,其实历史从过去到民国,包括到昨天发生的事都是不可重复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各种史料,各种视角的资料汇集的越多,或者各种证据汇集的越充分,对民国,他们的认识,他们的历史呈现的越多,这本身也是在清除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对历史写作和研究带来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历史写作或者历史学的研究有一种张力,有一种趣味,或者有一种审美的快乐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我们在识别各种视角的差异。读某些老师的书,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甚至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史料,但他就看出来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历史学为什么会有快乐感,事件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经过不同人的评说,对某个事件的呈现,我觉得这本书在事件的取舍,尤其是对古代的事件的呈现,其实还是体现了这种历史趣味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些的历史资料都是很重要的,无论它很次要,无论它是教科书,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资料,对于复原一面失去的时光,复原民国的时光或者是民国的精神我认为都是有价值。因为这本课本不仅是两个作者的历史观点,它通过教科书,已经影响了当时很多国民,对当时很多受过教育的国民肯定也是用这种观点看待历史的。我觉得研究教科书本身,可能对民国人如何认识他们的历史,如何对历史进行判断,特别是被删减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味。当时他们怎么写当代史,当代史他们如何表现,是不是有什么技巧,确实是有趣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民间的历史学研究或是民间历史呈现,其实已经开始摆脱了76年以前那种单一的历史叙述观的那种,但是教科书仍然没有摆脱,教科书仍然是一种政治正确,或政治形态操控下的这种,这种我个人认为是对中国的民族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害的。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出版社也好,其实出这种书的目的,也是想彰显跟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不同的一种史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历史教育的变化,我觉得应该多找一些中学老师来谈一谈,如何推动中国历史教育,教科书的变化我觉得更重要,比我们写出一百本历史书(这些是自然读者,几百本),但是一本历史教科书形成的损害是几千万人,甚至一亿人的损害,这种损害永远无法停止,一旦被洗脑,想改变的话,是很困难的。现在,民间其实很多人主动地找历史书来读,也跟这些教科书带来的损害也有关系,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无法从教科书中或者人群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或者无法明白自己在当下,我们的历史教育就是让你的认知一片糊涂,根本形成不了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而我们在读这本书时,我们就能感觉到那个时代气息,我觉得这本书更大的意义是让人民反思,当然,这可能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是异己分子,它是那个时代的异己分子写的书。其实我觉得教科书最重要的就是不仅让民众只知道历史的政治正确,更要知道,历史对生命和文化承担的道德责任。
所有的历史,真正应当承担的责任应该是对个体如何认知自己的行为,如何认知自我与他人与国家的维系这样的一种责任,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它的历史观表述得很不成熟,但对它的呈现本身你可以进行自我判断。这就牵涉到第三点,我觉得中国历史学家和西方历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孔子开始,从儒家开始就把历史当做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中国人认为明史就是明道,治史就是治道。中国人是把史和道,史和哲学,把史和一切有关真理的东西统一起来的。所以我们看这本书的史观为什么那么少,因为中国历史一直是不强调史观的,它没有超越历史实际上的一个研究方法,一个观点,一个方法论。基本上就是我如何呈现最真实的历史,把这个当做第一要务。我只要呈现了真实的历史,我就完成了真正的自我呈现。那么,这种历史观,我们反过来看,对于民众有什么好处。要求每个读者,都主动地参与到历史的解读中。就像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是一定要去研究历史的,你必须从不同文本的历史的呈现中,同样的手段中,境界不同,或者认知水平不同,读出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讲读者和被教育者对历史的参与,发表意见,所以书里很少表现出一种观点,它只是陈述事实。因为中国人把历史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强调每个读书人人的自我教育,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和西方后现代学的行为历史学思想很多方面很相似的。所以中国人讲六经皆史,所有的经书都是史书,经史不分,史书也是经书这种观点。最后再讲司马迁的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现在所有的史学家对这三句话都非常熟悉,但是其实中国的史学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究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说的人很少,今天我们的历史很多都是强调人事,没有看到天机,只是明白有,但是不明白无,其实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漏,比如我们看到的很大的历史事件,其实都是偶然的历史事件。未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实依赖于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无法预测,但是无论是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现在的历史,能改变历史走向的,往往就是这样的黑天鹅事件。这种天机的出现,值得当下历史学家研究一下。
刘丽华:叶匡政讲得非常好,他讲了如何认识史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中国人就是大家有时候就常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圣经,他陷在历史里头,而没有对真的追求,西方这个学科很早就分出来了,从希罗多德那时就有历史,柏拉图是研究哲学,他对真的追求和对历史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他从这个当中能够分出来是和非,就像历史的是和非,然后通过哲学家的进一步追问,那么刚才叶匡政也说了,在历史当中,缺乏这样一个东西,而且在历史当中,而且往往我们读了历史,很多人形成一个观点,就是胜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了,他就成了一个这样,觉得历史就是谁有势力谁有权力谁就是赢家(叶老师:越野蛮的人越掌控历史)对,他就不问是非了。在这个历史当中,这才叫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他不问这个了。我觉得叶匡政从这个角度说的非常好。还有刚才杨老师(杨献民)说现在的学生你问他什么历史事件都不知道,什么九一八不知道,三一八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不赖学生,还是赖教科书。因为它把历史事件写成一个干巴巴的东西,你想谁爱读啊,肯定都不爱读。而且我在想,它肯定有一个意识形态在掌控,学生很反感,所以他就根本不想知道你这个历史。我举一个例子,我认为一个小孩,原来他特别特别聪明,从小,刚五六岁吧,爱看基督教的一些东西。但是,到了中学以后,拒绝读书,就是你怎么让他读书,就跟要杀了他一样,最后大学也不考了。为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应该是一个开悟的孩子,但是就是这个教育,等于把他这个人断送了。为什么,就是这些教科书太害人了。所以我刚才觉得他们俩讲的不管是例子也好,观念也好,都提醒我们,这个历史教科书应该怎么写,史学家在他写历史的时候,应该把他的一个什么观念呈现给读者,我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下面请崔老师来接着讲。
崔文华: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吗? 人为什么需要历史?
崔文华:刚才听了诸位老师的发言,我深受教育,也非常感谢新星出版社给我们这个机会。我简单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和通过读这本书引起的一点想法。书寄给我之后我很认真地看了,看了之后我觉得即使我已经年近花甲,也读了不少历史书,我依然觉得这本书对我是有用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大概从传说当中的黄帝轩辕氏开始,他就设立了史官,创造汉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那么这样算下来,由国家政府设立的历史记载机构和专职人员至今有五千多年了。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几千年从未中断的史文化。我们用自己的史文化建构起了我们的文明,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们中华民族,依然是一个热爱史学的民族,我们的电影,我们的通俗读物,到处都是以历史作为基本内容的,不管是戏说还是正说。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可能所有的侧重史学研究,乃至于做历史哲学研究的可能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而执政者却非常明白他为什么需要历史学。所以说,站在不同维度上,对历史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人,比如说一个青年,一个退休老头可能读历史是一种消闲阅读。而对当今执政者,他需要历史可能是需要通过历史的阐述,来论证自己文化上存在的合法性,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在《论历史哲学》中有一个说法。他说,历史其实是胜利者的历史。胜利者通过著述自己认可的历史来证明自己是历史大趋势的承担者,是历史意志的实现者,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秉承历史传承,合法执政。我们就看到了老百姓读历史和执政者要建构历史和执政者要著述历史,需要通过教育来让国民懂得他所表达的历史的目的和诉求。这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来理清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从一个普世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呢,我们抛开执政者,抛开具体个人不讲,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呢,我们每个个体,不管是掌权者还是不掌权者,我们每个人自己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当中,却知道在我们之前有人,之后也有人,我们知道历史流程相对于我们这个个体的短暂生命而言是漫长的。所以我们需要历史来掌握我们这个类群,我们这个族类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是什么,从普世的价值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历史的。
美国有个经济学家,他在论述问题时说过一句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人和狗的不同是,就在于,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狗,在自己之后也有狗,而我们人恰好知道在自己之前有人,在自己之后也有人。那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之前有人,在我们之后也有人呢,在无文字时代,通过的是口头叙述,在有文字时代,那就是把我们过去的文字历史历程用历史记录下来,系统化之后就成为历史和历史学。正是历史和历史学的这种积累,这种长期的积累,我们因此建构了我们的文明,试想,我们如果把以前所有过往记录全部消除归零,显然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历史,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建构历史学建构了我们的历史文明,通过记录我们的过往,形成了今天的文明,今天的文明成为了过去我们积累的诸多生存经验的结晶,也是我们重要的思想资源,生存资源,生产资源。这是我们从大的类群的发展历程当中对历史提出的需求,那么从个体来说,我们毫无疑问得承认,历史学的研究是我们建构个体人性的需要。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不难感到,一个从不阅读也不愿阅读的人,一定是一个灵魂粗糙的人,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一个人性有很多缺陷的人,哪怕他手握重拳,哪怕他拥有亿万资产。
培根讲“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读史为什么可以使人明智,因为在读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人类过往经验汲取了。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建构了我们日臻丰富的心灵,我们日益完整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于是我们明智了。我们不是执政者,我们不需要论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我们希望我们活得更人化和人性化,所以我们读史,那么,从我们读史的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我们读这样的史书,毫无疑问,能够帮我们建构人性。如果今天的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愿意读这样的史书的话,把自己建构的相对的心智健全,精神平衡,感情丰富。我们设想他到五六十岁进政治局了,甚至当皇帝了,他来执政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相对人性的,明智化的执政者。我们知道中国隋唐五代时期是一个极其野蛮血腥的时代,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掌权的军阀们,每一个都是那么血腥,随随便便是可以屠城的。屠城不是自日本人始,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读五代史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屠城的,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的那些军阀,没有人读书。五代史中有几个皇帝压根儿不识字,奏章来了要大臣看。我们就知道,不读史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史,而好的史书对我们是何等必要。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好的史书。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是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学的。这很有意思。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学,每个时代的著史者,都在自己的时代水平写作自己的历史著作,现代阐释学告诉我们:阐释者是个什么水平,他就会把我们的时代阐释成什么水平。在我看来,这是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如果你是个激进分子,中国五千年历史在你的眼里就是个完全激进化的东西。你就会大肆张扬,充满了破坏的农民起义过程竟然是推动了历史的重要举动。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著述历史,解读历史也就是这样严格的。事实上是,长期的历史的诠释权,阐释权被专制者垄断。历史阐释权的中央集权式的文化垄断,垄断了从自有文字记载的正史到1911年帝制结束,凡是被正统认可的历史,都是由专制者垄断阐释权的历史。到了隋文帝,他非常明确地禁止私人注释,那是不是隋文帝之前,历史阐释就是自由的呢,也不是,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就不要说极端化的秦始皇了。在历史阐释权高度中央垄断的时代,也使用过他们的模式,比如所谓的“五德终始”,说金木水火土,五行循环,对应着每个朝代,很多史学家就用“五德循环”来构筑他们著史的观念框架。任何一个著史者,都必须有自己的一个观念框架,没有观念框架,就无从落笔。“五德终始”就是中国史学家们曾经引用的历史著述框架,这大概就叫作历史哲学。那同样的,既然历史是一个专制者统治的正统历史,那么王朝,自身认为自己是正统统治者的这种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构成了他们著史的唯一角度,正统角度,皇帝为什么说自己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什么运呢,实际上就是“五德终始”的德运。
著史的史家只能站在自己所处时代,把自己所处时代认为是正统时代,然后,从自己这个时代的正统出发,去对前代进行总结,就像我刚才所引用的阿尔都塞的话:历史是胜利者著述的。所以像明智如李世民,他让人写他的历史的时候,也得把他干的一些缺德事儿全部删掉。其实,比如说南朝,每个小朝代都不到一个世纪,南朝的皇帝也得让他手下的史官把一些糟心事儿去掉,一个光鲜体面的历史留于后人,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正统史就是这样一个史。如果说司马迁时代,班固时代还是本朝人可以写本朝史的话,那么大致从唐代开始,就是后朝写前朝。唐人写了《隋书》《晋书》,宋人写了《唐书》《五代史》,然后元人写了《宋史》,明人写了《元史》,那么后代写前代,就把自己写成非常正直的一个承担者。前代是暴虐、荒淫,后起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推翻他们。这种所谓的历史哲学,深刻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著史,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中国的某些正统史史观就结束了,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还得经过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史观,也得跟中国著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中国史家把中国的正统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正统历史权利的统断到1911年结束呢,那就是帝制结束了,王朝用正统观念垄断历史阐释权的时代因此就结束了。民国产生了,不管袁世凯篡夺了多长时间,那个时代毕竟是比以前时代要自由得多,多元思想开始产生。
那我说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学工作范式的转换。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库恩,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科学概论,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范式转换。他的这套范式科学理论其实在社会科学也有很大影响,我觉得每一个喜欢历史的人,认真的看看库恩这本书可能大有启发,我们真的是应该、早就应该进入中国历史学的范式革命时代,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难道还要坚守五德终始这套历史学说吗?我们还要用自己皓首穷经的这种做法来诠释当下统治的合理性吗?我们应该是无障碍的接受各种人类精神思想资源,赫本假说学术是人类获知的最高成就。全人类那么多一流的大脑,创造出那么多新的学术范式,我们为什么要死守一家一户一派呢?我们今天的史学需要进入一个范式革命的阶段。
而我们的中学生还在形成思想阶段,我们这些教他们的人却还用着正统史观,用着“五德终始”论来教着他们这种思想,那不是太可怕了吗?
依然落到这本书上,这本书给了我们启发,最后我讲一下文风问题,著史是要有文风的。中国正史不管有多少思想的缺陷,却锤炼出了非常精炼的文风,精准至极,欧阳修那样的大文豪,甚至可以写淫词艳曲,但是一旦他秉笔书史,他就讲究非常精确,那么这个历史传统,就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史书,都是写得一惊一乍,写得玄之又玄的,这非常可怕。书的序言写到了开明书店,引进了叶圣陶,夏丏尊这些人,叶圣陶说过一句名言:“文风即国风”。在我看来,真的是至理名言,今天,当我们准备写字,或者铺排成篇的时候,我们想想这句话,也许大有裨益,而这本书的文风,真的是我们写白话文的人值得取法的。我就说这么多吧。
刘丽华: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活动现在就到这了。谢谢大家的到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