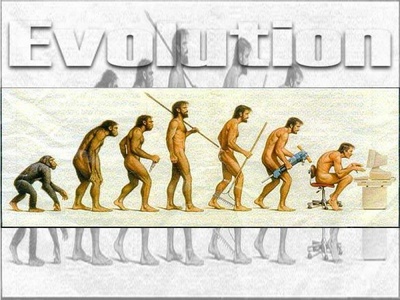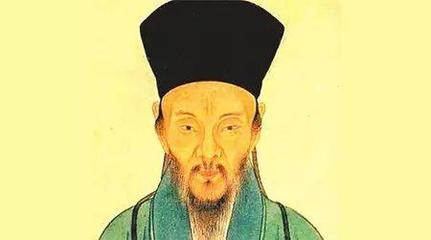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加上流亡日本多年,对阳明心学服膺有加,他曾经称赞阳明为“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并表示王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是因为他在程朱理学笼罩一统天下,以极大的勇气,挺身而出,用“心即理”的学说之与抗衡,以“知行合一”理论戳穿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的新说,对当时社会,“像打一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吐出很大光芒”。
梁先生曾在《德育鉴》中指出,日本维新豪杰都是王学后辈,“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梁本人以阳明心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之时,“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
梁先生在晚年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屡屡谈及阳明心学。《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其中直指当时只重知识传授,轻视德性培养和实际运用的教育弊端,今天读来,对照现今的教育体制,非常有现实意义。演讲很长,此篇为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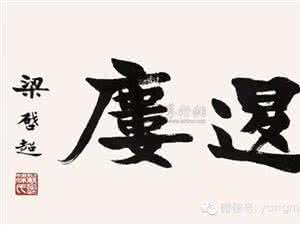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代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青年毛泽东喜读梁启超在报纸上的文章,“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习近平总书记前一段曾引用的《少年中国说》,即是梁先生的名篇。
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1931年其子梁思成设计墓园,1932年葬于北京,现北京植物园内。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引论
现代(尤其是中国的现在)中国式的教育,种种缺点,不能为讳,其最显著者,学校变成“智识贩卖所”。办的坏的不用说,就算订好的吧,只是一间发行智识的“先施公司”,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上几年,肚子里的书像蛊肠一般,便算毕业,毕业之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若想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在讲到修养身心、磨练人格那方面的学问,越发是等于零了,学校固然不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去教,教的人也没有自己确信的方法来应用,只好把它搁在一边拉倒,青年们稍微有点志气切实为自己将来前途打主意的,当然不满意于这种畸形教育,但是无法自拔出来,只好安慰自己说道:“等我把知识的确装满了之后,再慢慢修养身心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就修养方面论吧,把“可塑性”最强的青年时代白白过了,到毕业出校时,品格已经成型,极难改进,投身于万恶社会中,像洪炉燎毛一般,摆着边便化为灰烬。就实习方面论,在学校里养成空腹高心的习惯,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最终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高等无业游民完事。青年们啊!你感觉到这种苦痛吗?你发见这种危险吗?我告诉你,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知行合一是一个“讲学宗旨”,黄梨洲(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人之得力处,亦即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羲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明《儒学案》发凡)。所谓“宗旨”也,标举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头,包举其学术精神之全部,旌旗鲜明令人一望而知为某派学术的特色。正如现代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之“喝口号”,令群众得个把柄,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则成功自易。凡讲学大师标出一个宗旨,其自己必几经试验、痛下苦功,见的真切,终能拈的出来,所以说是“其人得力处”。这位大师既已经循着这条路成就他的学问,他把自己阅历甘苦指示我们,我们跟着他的路走去,当然可以事半功倍而得和他相等的结果,所以说是“即学者入门处”。这种口号式的讲学法,宋代已萌芽,至明代而极成。“知行合一”就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们学术史留下的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口号之成立与传播,须具备以下各种要素:(一)、语句要简单,让人便于记忆、便于持守、便于宣传。(二)、意义要明确。明谓显浅,令人一望而了解;确谓严正,不含糊模棱以生误会。(三)、内容要丰富,简单的语句要能容纳多方面的解释,而且愈追求可以愈深入。(四)、刺激力要强,使人得着这个口号便能大感动。而且积极地向前奋进。(五)、法门要直接,依着它实行,便立刻有个下手处,而且不管聪明才力之大小,必都有个下手处。无论政治运动学术运动、文艺运动……等等凡有力的口号,都要如此。在现代学术运动所用口号,还有两个消极的因素:(一)、不要含宗教性,因为凡是近于迷信的东西,都足以阻碍我们理性之自发,而且在现代早已失去感动力。(二)、不要带玄学性,因为很玄妙的道理,其真价值如何姑勿论,纵使好极,也不过供极少数人高尚娱乐之具,很难得多数人普遍享用。
根据这七个标准来评定古今中外学术之“宗旨”——即学术运动之口号,我以为阳明知行合一这句话,总算最有永久价值而且最适用于现代潮流的了。阳明所用的口号也不止一个,如“心即理”如“致良知”都是他最爱用的,尤其“致良知”这个口号,他越到晚年叫的越响,此外如“诚意”如“格物”都是常用的,骤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其实他的学问是整个的,是一贯的,翻来覆去说的只是这一件事,所以我们用知行合一这个口号来代表他学术的全部,是不会错的,是不会遗漏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