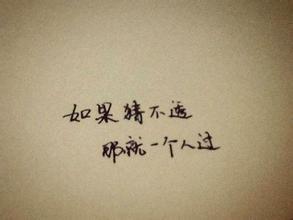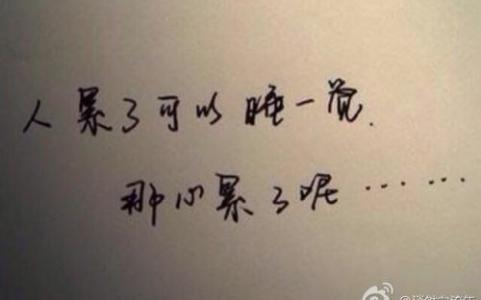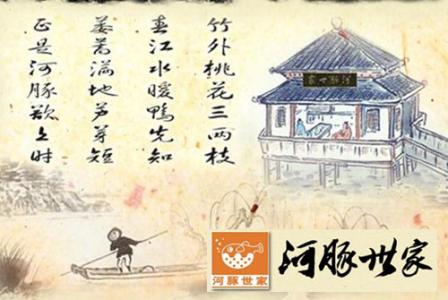朱屺瞻:作画时容不得一点杂念
整理编缉_《当代国画》
文章来源_网络
风格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生活基础和绘画实践中发展形成的。元、明各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风格,时代特点。我们也应画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创出一种时代风格,不能泥古。要多看当前的实物,留意当代的生活,多速写,多写生,才不至于脱离时代精神。
佛像来自印度,经数百年的雕绘,不知不觉中取得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种“中国化”的过程,值得研究。如何创出“中国化”“民族化”的油画,与如何吸取西画的优点融入国画的问题上当有所启发。
若干年来,我多少抱有一个心愿:努力跟着时代变,努力引导我的画向着一个方向推进。那就是:风格要浑厚一点,色调要强烈一些,笔意要拙朴一点。
拙朴最难,拙近天真,朴近自然。能拙朴,则浑厚不流为夸张,强烈不流为滞腻。
作画时,容不得一点杂念。名利心固然要不得。古人笔法,世俗偏见都是“乱我心”的尘垢。古人“正心诚意”之说,于此还是用得上的。主要在“诚”字。把全副精神百分百地集中在创作之中。这就是“诚”。
偶读杨城斋句:“雪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这透脱是指胸襟通达超豁,不缚于世俗成见,不执著,不粘滞。希望从生活体验中,对事物认真探索,以求通晓;孤高犹言一无依傍,自有树立。周汝昌注引《扪虱新语》:“读书须知出入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学画也正如此。不亲切则入无由。不透脱,则自缚框框,如何得出。不入,谈不到出。不出,又何用于入?
生活与环境的变化,审美情趣也会不断改变。我在北京饭店看到新建筑光线充足,室内摆着新式的家具,墙上挂着贝壳画,颇有不和谐之感,这使我悟到,建筑风格的改变,作为室内布置画的画风,也必须有所改变,才能与新建筑谐调。
从前所谓“暗房亮灶”,在空阔的老式厅堂中挂上长条巨障、画上清淡疏朗的山水或花鸟,在柔和的光影里,是很有情致。然而,新建筑既改变了原有的结构样式,又产生了新的光影与空间效果,画面应有强烈的对比效果,才能在充足的光线中“站得住”。
作画须有“宇宙感”。此意的明确体会,我得自林畊青。我国传统艺术论“意境第一”。诗如此,画亦如此。林畊青点出“意境有高低;叹老嗟卑,意境限于个人;感时忧世,意境胜了一筹;最高的意境,则需与天地同脉拍。这就是‘宇宙感’。表现可有两面:感到无穷时空的‘微茫’处,与感到生化天机的‘微妙’处。屈原《天文》可代表前者的情怀。曾点浴沂(见《言论》卷之六)最可说明后者的志趣。简单寻例的话,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属于前者范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诗,属于后者的典型。
这两者表现虽不同,实质仍不二。他们的作用都可以超出个人与历史。在中国画史上,陶渊明的主题得到了尽致的发挥。陈子昂的情调此后还有待发展。”
林畊青这段话,对我启发良多。画出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究竟停留在个人情趣平面,还是能进入历史的范畴,而更趋入于宇宙范畴?要写出生化天机的“微妙”,我确曾向往。要表达无穷时空的“微茫”我不曾想到。我最近作《浮想小写》十二图,可看作为我对两种“宇宙感”的尝试。
读到前贤“厚生以养民”之句,甚觉艺术亦如为政,作用须是“厚生”,有助于丰富人生,增加一点人的生意生趣。
我作画,喜“厚”字。觉得厚近仁,人近生。 唐荆浩论笔法云,“必全其生意”。画家能做到此点,其他都是末节。谢灵运梦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为“工”。句无雕琢,写出了天地间那点“生意”便是“大工”。
写生须写出其活出,写出其生机生意。写得四僵僵无生意,便根本违背了写生的本旨。要写出生机。这是中国“生生之道”的宇宙观之要求。

“画意重生机”石涛曾言之矣。石涛云:“天以生气成之,画以笔墨取之。”又云:“必得笔墨之生气,与天地之生气合并而出之。”所谓巧夺天工者,夺得的就是此生机生气。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