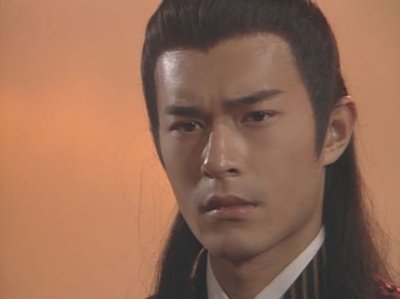我曾想:用一辈子的光阴去珍视,属于我的东西。但我并不知道,所有一切都将跟随时间的流动而不复存在。记下三毛写的那句:“世上的人都喜欢看悲剧,可是他们也只是看戏而已;如果你的悲剧变成了真的,他们不但看不下去,还要向你丢汽水瓶。”这才发现:所有结局和人生其实是一段距离上的两个不同的端点。而结局难道不算是悲剧吗。<?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地球上孤独的旅行者。从出生的那一天我们早已为自己策划好了明天。但人生总会历经风雨,却时常伴随“结局”展开着新的生活;他们都是人生的探险者,希望迫切得知什么是“真”。那么,请问什么才是真呢?在我历经的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之中,我有过太多无法抗拒的卑劣的念头,但最终取胜我的——是人生中永恒的理想与希望。
它们,不知所终。有人说:“生命其实是一团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叔本华)。也有人说:“人的一生总是在不停地尝试拥有与放弃,人的一生终究在不停地追求,追求着自由与理想”(杨佳虹)。顾城说:“《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江红说:“有时候我忘了自己活着,我只来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来,但是这个道理我却这么容易忘记。一走了之的心态谁都有过,在走与留之间有着我们灵魂的出口。”我还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色彩,却不会频频的栩栩如生。只有当你承受起不可复制的人生之旅,才可能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我后来又说:“人生就像一张白纸,填满字后不是成品,就成了废品。”而结局也是,明知道终必成空,却要让世间种种围绕日月星辰,不断的交替。
每个人都不可能拥有相似的人生,每个人也不能全权体会我们所受到的苦难。面对人性荒凉与人生的错谬,我们真的要背过脸去向隅而泣吗?有时,我恨不得这一撞一切便不了了之。因为人性的荒诞,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顷刻间萧然不存。除了自己,谁比我们更清楚。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有的人活下去,有的人危在旦夕?为什么同一场车祸,有的人幸免于难,有的人难逃死劫?为什么同一根鱼骨,有的人从喉咙取出,有的人能刺穿阑尾?为什么同一台手术,有的人能度过难关,有的人却不能平平安安?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却把社会分成“整块”;任各自奔走在365行的行业之中,无怨无悔?我们的婚姻、生活比谁都清楚,试问除去自己,谁又能够真正的体会?有如《楚辞》中记载:“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烈士屈原,被流放后,抑郁成积,从而向占卜者郑詹尹求诉龟壳之谜。詹尹告诉他:“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也!”事实上,那些理所当然的想法,正如新加坡作家尤今所说的那样:“往往与实际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关于悲剧,三毛又说:“你聪明的话,应将那片幕落下来,不要给人看了。连一根头发也不要给人看,更不要说别的东西。”如果这样,那你也不要哭了,因为你也不要演给自己看——假如我们都不喜欢悲剧。我们不放弃任何事情,包括记忆;我们不纵容自己,包括伤心;但,所有人都有烁亮的眼睛,我们看到的表面,却看不到别人的坚强;反之要说不够坚强。假如要澄清一个事情,我们是否也要像精国英雄岳飞那样,含着莫须有的罪名,在秦桧和百姓面前,掉以眼泪的写下“天日昭昭”四个大字,然后令后人瞻仰?还是像屈原那样怀着对国家的忠心,怀着抑郁与一时的反差,抱着石头以长江清洗?还是像武则天那样,留下一块不全的字匾。百年的历史,日月的积淀,仿佛也没有人真正的受到昭雪啊。况且人生并非需要证明,况且他们又与个人何干?事竟以此,只有丢在自己身上,才感觉得到它的份量!
有人说世界是我们的,我多么伟大的挥笔写下:“永别了世界”但它其实不属于你,我们用不着给予抛弃。就像我在少年时期写下的那句:世界本没有属于你的东西,反过来你却拥有着整座世界(时间)。虽然没有一样事物是肯定属于谁的,也不会有一个人属于任何的另一个人;但我们也要珍惜,方知人生是最珍贵的财物。因此,我们用不着嫉妒,我们无所谓攀比;因为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极短,就像意大利著名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三杰之一的拉斐尔。这位年轻、俊貌的《西斯延圣母》画作的英才,在其37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我们飞来飞去,探索奥秘,却从未发现在身旁的一切其实就有外星的因子。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用现在的科技和眼光,靠着光速传递再反射回来的信息。其肉眼所看到的行星,只不过是四十多年以前的物体。人还有色彩的构造和“看不见的东西”(比如魔术),假如我们拥有动物或植物的灵性,对于整个世界与社会的理解是否会更深一层。
当然今天的科技在日益升华,可是这么理智的社会,却频频缺少珍视他人的人才。我们不能拿嫉妒当饭吃,不能拿结局作命宝,不能拿功名使手段;纵然百姓做不到的,也可以用言语。而应该去瞧一瞧《红楼梦》里所假设的“太虚幻境”,去看看真正的人生和自我的价值。通灵宝玉又算得了什么,道士的“风月宝鉴镜”的正面才能清晰地瞧出丑恶。
什么是幸福呢?人生就是幸福,生活就有味道。只有当一个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才能打开人类的第三只眼睛。为什么人死会永不瞑目?因为他们看清楚自己身前所不清楚的事实,他们终于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所有的追求、不过是要我们珍惜人生的点点滴滴。大概会有人说我悲观主义,像叔本华或者尼采,但是人们并不拒绝悲观。也只有悲剧的诞生,才令人格外清楚。难道2012这部电影,还没唤醒沉睡着的人们?
我想世人勾画出《白蛇传》来,并不是要我们多批评与怜悯,而是希望我们在欣赏人间诗化的同时,对事物的本身进行一次从新的认知。假如“白蛇”是一种真实的妖孽,那么法律与法海,又是今天的什么。假如《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真实的人生写照与虚幻的梦境,你对此又有何解?而今,作家鲁迅对悲、喜剧的认识是这样写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因此,追求结局,歇斯底里的都是一种枉然;当然放弃,一定会有无奈。但人生也是有价值的东西,每个人却拥有不同的观念。我们对于同一件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却在追求上满足自己相似的欲念。
人生不过是驾驭我们前行的一艘隐形的航帆,我们却要时常保持着笑容以对的心态。面对倒着行走的光阴,去感激每一块一分币的恩情。接受你所不能承受的意外,并且告诉自己:我们比死亡更荣幸。在爱情的国度里也是这样,爱一个人,也许并不是你所爱,但最后相守的却是最合适你的那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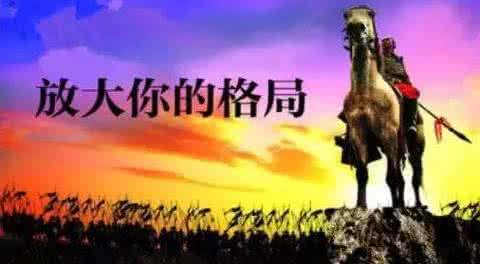
结局与人生是开始也是分离。我们所说的真,其实就是生活中最实际的体验。而作家三毛最终选择了“临走”,那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结局”。因此,生活无需问得太多;人生也不过是一章填满赞美的历史。竹雪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