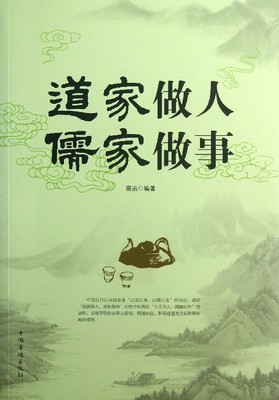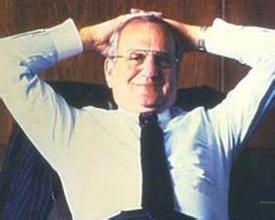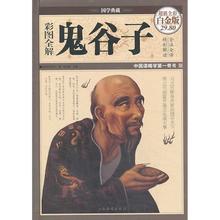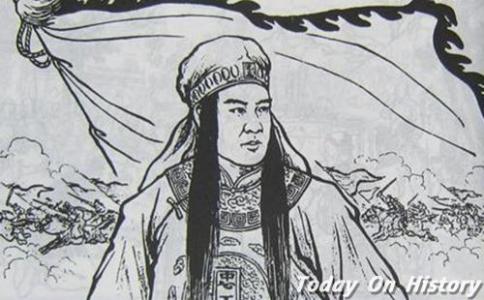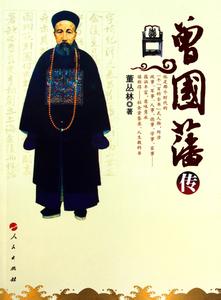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
曾国藩虽然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向他人借来,但其家境要比洪秀全殷实,可以一门心思读书科考,不必为生计担忧。洪秀全则是举全家之力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秀才不中,只好自谋生路,一边开馆授徒,一边准备科考。曾国藩得益于耕读传家的宗族渊源,最先就学于父亲,书也读得扎实而系统;洪秀全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读于他人,书读得杂,学习方法不如曾国藩得当。两人资质自然都不错,算得上聪颖灵慧,但并非那种所谓的天才、神童之类。只是洪氏家族将洪秀全视为光耀门庭的支柱,洪秀全本人也在期待、吹捧的氛围中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从小便萌生了一种“救世主”的味道与派头。而曾国藩家教极严,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虽务农为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农民,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还考了个秀才功名,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祖父曾玉屏常以不少警句似的大白话教育曾国藩:“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鼓励与督责兼而有之,还教他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这些,都成为曾国藩终生受用不尽的座右铭。因此,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从小便懂得自我节制、适可而止,他常说自己天性“钝拙”,无超常之处,哪怕位居人臣之极,也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从未居功自傲。父亲曾麟书留给儿子的是“积苦力学”,以孝治家,并以儒家理念要求后辈,他曾自撰一联道:“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曾国藩从母亲江氏身上则继承了敢与困难周旋的倔强之气。这些,都培养了曾国藩克勤克俭、倔强自立、坚持不懈的优秀品格。
当然,科考成败是决定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洪秀全哪怕仅仅考中一个秀才,恐怕也不会转向基督创立上帝教揭竿而起。不过,要是曾国藩终生连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话,肯定不会走上信教反清之路。他的故乡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比洪秀全的故乡更为偏僻封闭,曾国藩当时到得最远的就是省城长沙,长沙不是通商口岸,连个基督教的影子也见不到。加之曾氏家族有着不信医巫、不敬鬼神的传统,祖父曾玉屏教导曾国藩要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因此,哪怕曾国藩遭受再大的打击,肯定不会陷入装神弄鬼、走火入魔的地步。以曾国藩的家教及环境而言,如果他未能取得科举功名,也只能是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奉行“以耕养读”的传统,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终老故乡。
然而,曾国藩最终走出了大山的环抱与封闭的故乡,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封建官僚运转机构重要部位上的一颗“螺丝钉”。此后的道路与发展,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更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成为一对悬殊极大、反差强烈的比照:
洪秀全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典籍,捣毁庙宇偶像;曾国藩以书生举兵,有意淡化满汉之争,打着维护恢复儒家名教的旗帜以复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为目的。
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吸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曾国藩虽然走出书斋,率兵作战,但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常常手不释卷,他严格规定自己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孜孜不倦,正如他自己所言:“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这种阅读给曾国藩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好处,就是对文字的感受能力相当敏感。因忙于军务政务,他不得不放弃诗文之类的创作,专写奏章、文告、书信、日记之类的应用文。曾国藩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专著,但他的应用文堪称古代此类体裁的典范之作,言之有物,要言不烦,意尽而止,决不多置一词。以至《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曾胡治兵语录》等相关书籍成为后世畅销之作。
洪秀全金田团营不久,就开始腐化堕落,定都天京后更是深居内宫,躺在无数女人的温柔之乡;曾国藩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自己,对自己的私生活相当自律,他不近女色,不奢侈,不铺张,一生勤俭朴素,似乎不懂得什么叫享乐。
洪秀全自天京内讧后,不信他人,任人唯亲,只信洪氏一门,先封两位兄长为王,后封洪氏宗亲大王、小王无数,他们不仅未能帮助洪秀全建功立业,反而鱼肉百姓,蛀空天国根基,特别是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自己本事平平不说,还一个劲地牵制石达开,不断“使绊子”,最终导致石达开离京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曾国藩对自己的几个弟弟及其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写信督导他们如何学习怎样做人,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十分争气,特别是曾国荃率军攻破安庆、天京,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儿子曾纪泽作为晚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利用国际惯例和个人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取得的外交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曾国藩留下的一部《曾国藩家书》,不知感染、教育、勉励了多少后人。
洪秀全起事不久即称天王,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似乎从来就没有“节制内敛”一词。既为“天王”,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文化文明,全都不在话下,只要他心血来潮,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上帝之子”的名义将所有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曾国藩一生如履薄冰,时时告诫自己,约束自己,哪怕湘军攻下天京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自我意识也没有膨胀,而是谨小慎微,主动裁军,自剪羽翼。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与落脚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洪秀全走不通科举之路,目光不由得转向他方,结果他得到的只是一本《劝世良言》,仅凭这样一本《圣经》中国版普通读物,便在中华大地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闹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民主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满清的颟顸、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曾国藩所代表并与之抗衡的,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之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身疮痍地苦苦挣扎不已。而曾国藩所吸取的,却是儒家思想之精华,正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性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由孔子到董仲舒而朱熹,再到曾国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涌动着一股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有幅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反清起义,立德与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借助剿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