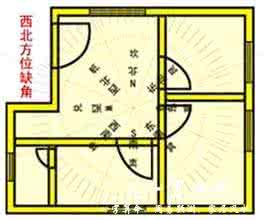——写在吴让之逝世140周年之际
吴让之是扬州文化史绕不过的话题。但就我接触到的扬州老一辈书画家而言,他们很少提到吴让之。有一次我从西泠归来,和一位书画老前辈谈及某西泠名家对吴让之的评价时,这位老先生竟火了起来,甚至把这位西泠名家给他刻的一方印章掷到地上,使我非常尴尬乃至不知所措——原来老先生不喜欢吴让之。又有一次我和一个较为年轻的篆刻家谈及吴让之,他竟然不知王渔洋、吴让之哪个年长。我想,这样的一个吴让之,百年之后竟如此的落寞,百思不得其解。吴让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书画篆刻在扬州文化史上乃至中国书画史上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一、刘铁云笔下的吴让之
有人说晚清四大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鹗),家在扬州北小街一带。我查罗振玉的《刘铁云传》得知刘为丹徒人,家在淮安,不事科举,善数学、医术及水利测量。自年轻到终老都活动在山东、北京、上海。后遭袁世凯迫害,流放新疆,1909年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年仅53岁。也就是说,刘鹗纵然到过扬州,亦是流寓,而且时间极短。但淮安与扬州甚近,所以他对扬州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天热无事,偶读刘鹗的《老残游记》消暑,发现一段评价清代扬州书画界的文字。在《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老残游泰山斗姥宫时,和姑子逸云有这样一段对话。逸云问道:“扬州本是名士的聚处,像那‘八怪’的人物,现在总还有罢?”刘鹗借慧生的嘴说:“前几年还有几个,如词章家何莲舫,书画家吴让之,都还下得去,近来可就一扫光了。”这是书画界之外旁观者的评价,相对比较公允。刘铁云的这一段评价,说得很轻松随意,但站得很高极有分量。也就是说,就扬州书画史而言,“八怪”之后,就是吴让之,吴让之之后,扬州书画坛“一扫光”,不值一提。堪谓点石成金之评。
吴让之作画,起步较晚,50岁始和郑芹父学画。但由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书法修养超群,下笔便脱尽时俗,他笔下的花鸟,自由活脱,一派大家气象。汪砚山评说“馀事作花卉,亦有士气。”“士气”者,董其昌的概念,它相对于“秀才酸气,乡先生腐气,和尚酒肉气,女人脂粉气、贾贩葱蒜气,守财奴臭气,衙门仆隶恶气”,是一种儒雅纯正之气也。吴让之的画应作如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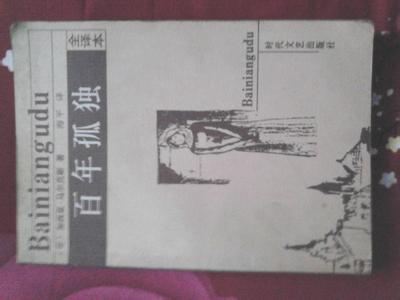
至于吴让之的书法,兼工四体。世人皆知其篆书如何如何,其实他的魏碑得邓石如真传,较之花描的赵之谦更胜一筹,结体开张,笔力雄健厚实,晚清写碑很少有堪可比肩者。但后之评者只提赵之谦、李瑞清,而不提吴让之,实不公允。
二、吴让之和欢喜冤家赵之谦
当今的流行歌曲有首《思念不如不见》,印象深刻。其意是,还是沉醉在往日的思念中好,相见还不如不见,它可保存完整的美好记忆。若再见面,时过境迁,人我俱非,会使你大跌眼镜。这种失望和痛苦更甚于思念的刺痛。这首歌对于吴让之、赵之谦这对欢喜冤家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在没有见到吴让之之前,赵在浙江偶然见到吴让之的印章,叹服不已。赵之谦不止一次向人夸示:“近人能此(治印)者,唯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思贤心切,恨不能只身飞越关山,一会吴让之这位高人,以解思贤之渴。由于战乱之故,赵之谦无法亲临扬州,只好拜托好友魏锡曾了。几经周折,魏终于在泰州找到了吴让之。为什么?其时扬州已被太平军占领,吴让之因避兵乱而流寓泰州。魏见到吴之后,说明来意,吴让之亦尽地主之谊,分别为赵之谦、魏锡曾各刻了两方印章,还为魏书写了若干篆书魏碑以赠。之后魏拿出赵之谦的印谱,请吴让之作序,并将吴让之案头所刻印章钤拓为二册吴让之印谱,吴均一一应命,可谓不薄。魏在得到吴的印、书、序文及吴让之印谱后,取道北上,在北京和赵之谦会合。文人交流是一件好事,可促进友谊,推动艺术与时俱进。谁知,这一次例外,令人大为意外的是,它却引发了一场晚清印坛最大规模的论战,不只是论战,简直是“世界大战”,直至今日仍无定论,一直喋喋不休地延续着。何以至此?原来赵之谦看了吴让之为自己的印谱所作序文后,勃然大怒,一气之下写了一篇《书扬州吴让之印稿》的长文,以表自己对吴让之及当时印坛的看法。该文大体上分三个层次:对吴让之印的评价,对浙派的批评,对晚清印坛发展方向的看法。此文传至上海后,有当时的名公魏锡曾、吴昌硕、曾熙、黄质、高时显、张丙炎等人的跟跋。这些大名家发表了对赵对吴对浙派的不同意见,一时热闹非凡,且旷日持久,影响至今。在这里,我不想对赵之谦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评说,只就吴、赵二家的个人恩怨,谈谈自己的看法。
三、理论是灰色的,小说把吴让之打入冷宫
曾经有人问我,吴让之和赵之谦之争,责任在谁,是谁不好。我当时肯定地回答,是吴让之不好,这场争议是由他引起的。问题出在吴让之为赵写的序上。其序云:“刻印以老实为本,让头舒足为多事。”“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邓石如)室,何得更赞一辞邪?”在这之前赵之谦有“今日能此者,唯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并且请朋友冒着被太平军杀头的危险,辗转至泰州,拜会你吴老先生。想不到你吴老先生不但不给面子,而且给赵当头棒喝,这怎么能不叫年轻气盛的赵之谦怒从脚下起,恶言口边出。用现在的话说,吴让之不识抬举,必然遭报了。赵在读了吴序后,随即也给吴的印谱作了一序。即上文所说,其中有:“让之于印,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什么叫能品,心力交瘁,马马虎虎成印也。这种评价和之前赵的“一人而已”判若两人。其时,吴让之在泰州为赵作序时,吴65岁,赵35岁,相差30岁。吴让之作序时多少有点从自身走过的路为训来开导小青年赵之谦,话说得不好听,意思还是好的。也许这一刺激,成为赵技艺大进的动力。但赵却不这样理解,更咽不下这口气。不仅在序上出恶气,又在给魏锡曾的信中说:邓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叱吴让之“天一人九”。这样连吴让之的“祖孙三代”都骂上去了。叱其对手“天一人九”不等于自诩为“天九人一”吗?这样就把一场严肃的学术争鸣变成了带有个人意气的人身攻击。这也太过分了,简直是恃才傲物,狂悖之至,故尔引起印坛诸老之不满。这就难坏了中间人魏锡曾,魏在《吴让之印谱》跋中不得不说:“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者固推撝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若至人书俱老,岂直过让之哉?病未能也。”行文虽偏向赵之谦,但总算说了公道话,亦算是一个折中调和的公判。
但故事并没有了结,老实巴交的吴让之在给赵之谦印谱作序时忘记了“不畏前贤畏后生”的古训,他万万没有想到,不过十年,赵之谦竟成长为海派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沪上的跟风者岂能让他们的领军人物为扬州土老头子所“辱”,于是吴赵之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故桑愉先生文革期间曾赠我一本油印小册子——陈子奋先生的《颐谖楼印话》,内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坊间小说记赵撝叔与吴熙载一事云:赵似杨炯之,不肯居王(勃)后。与吴同寓上海卖画时,一日戏吴曰,我与君当易地鬻艺。或京津,或苏杭,各择一地,以阄定之可乎?吴噢诺。拈得京津。遂之津三月,几典衣付旅费。不得已再之京,求者寥寥。赵则赴苏杭,求者踵接,未半载获三千金。从此,吴赵之优劣分矣。
如果上引坊间小说是真实的,必须服从以下两个前提。其一,事件必须发生在1863年(同治二年)吴赵二人因印谱序文龃龉之后;其二,事件必须发生在太平军失败之后,因为小说中的地点都在太平军的活动范围内,即在1863年之后。考:天京陷落,67岁的吴让之回到郡城扬州,寄居石牌楼观音庵,与莲舟、海云和尚为伍,同住者还有王小梅,以卖书画为生,没有发现有沪上之行,更没有到京津卖书画的记录。而赵之谦自35岁到44岁,主要活动于京师,“屡试皆黜”,直到44岁才被放到江西做个小官,至56岁(1884年)死于南城官舍。嗜官如命的赵之谦哪有工夫到上海去和吴让之斗法?在这其间吴让之已于同治九年(1870)在扬州去世。现代画论研究,我们查不到赵之谦到沪上卖艺的记录,也没有和海派艺人直接交往的记录。近年来上海《书法》陆续发表了赵的信札,可知赵的书画是通过友人及子女传到沪上,并影响海上画派画风的改变及形成的。由此可知上引坊间小说,纯属海上粉丝子虚乌有的捏造和对吴让之的污蔑。
歌德说,生命是长青树,理论是灰色的。自吴赵因序文引起的争论以来,有谁作过对上述故事的考证?纵有智者叱其荒谬,又有哪个书画商去读书去研究正史?而书画家的生命及艺术价值往往生存于画商及粉丝的“口碑”之中。例如人们宁可相信《三国演义》中忠义双全智勇过人的关羽、安邦定国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而不相信正史中有勇无谋、傲慢自大的关羽及急功近利、不能审时度势的诸葛亮。这样,坊间小说击败了正史和理论研究。百年以来,赵之谦的身价越走越高,而吴让之的身价越走越低。本来在伯仲之间,而时至今日,赵、吴的身价差在十倍、百倍以上。运交华盖,“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吴让之也就更加落寞了。
四、吴让之、赵之谦艺术之比较
平心静气将吴让之和赵之谦比较,吴赵创作涉及的范围几乎相同,各有长短。就诗而言,都能诗,都“不多作”,都平平。就书法而言,都兼工四体。就篆书而言,吴达到晚清极致,赵有“我朝篆书邓石如第一,近人唯吴熙载”语,自愧不如。就魏体楷书而言,吴沉稳、朴实,而赵则内刚而外秀,各有千秋。就画而言,都是“八怪”的馀脉。吴以平淡雅正见长,而赵大开大合,多装饰趣味,色彩浓丽。吴见古典美,而赵开海派画风之先,见创新美。就画而言,吴不如赵。就篆刻而言,两人都是邓石如的分支。赵在形式美上发展了邓石如的“疏处可走马,密处不容针”,而吴在形式美上真正实践了“印从书出”的要旨(邓石如的印,取法汉碑额,还算不上“印从书出”)。篆刻对吴赵二人而言,标志着二人诸多艺术种类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影响最大。赵的印章合浙皖为一,吸收汉魏六朝碑版及造像化入印章边款,开风气之先,影响甚大,后称之赵派。齐白石就是受赵的《丁文蔚》印的启发而成派的,亦可见其成就之高。而吴的印章影响更大,发展完善了邓石如的体系,其成就直接导致吴昌硕派和黄牧甫派的诞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技巧小聪明会被时间蒸发,美学的追求和实现将化为永恒。今天回过头看看,“天九人一”的赵之谦终敌不过“天一人九”的吴让之。吴让之篆刻自然分布的和谐美学准则远远高于赵之谦的对称均衡法则。吴的“若无所视,神游太虚”使赵的刀笔凸显得更加怯弱疲软。换句话说,吴让之篆刻上的成就和影响大大超过赵之谦。但这只是圈子里的话。悲哉!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光绪二年,镇江来了一个名叫李维之的人,他在扬州泰州转了一圈,以极低的价钱竟把吴让之晚年的精品之作来了个一扫光。目睹现况的张丙炎十分惋惜地说:“今砚山、仲海、仲陶印,十之八九在李维之处。”这是令人撕心裂肺的历史文献。其时,距吴让之过世不到五年,那些一口一个恩师的学生们,并不穷,却卖掉了老师十之八九的精品杰作,对其“恩师”何其薄也!这简直是对老师的背叛。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时的扬州文化人并不真的珍惜吴让之。这是吴让之瞎了眼,竟带了这样的学生。这是扬州文化史上一大悲剧性的事件。
一次我读西泠学者陈振濂的一本书法史,内有这样一句话:“伟大的吴让之,书印一到他手中就变美了!”这位目光深邃如潭水的专家竟是浙江人!他的评价令我们扬州人汗颜。当年元稹在杜甫过世一百年后作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有诗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也”的二十字评价,于是沉寂百年的杜甫一跃而为诗圣。当然,陈振濂先生不是元稹,吴让之也不是杜甫,沉寂了百年的吴让之,能走出他的“华盖”阴影吗?
扬州人没有为吴让之留下墓志铭和传记,我们不知道他死于1870年的几月几日,更不知道他葬于何处。近日浏览吴让之书画印作品,可知吴让翁大约过世于这一年的夏秋或秋冬。故此,引发了这篇文字,借以表达对乡贤的敬意和怀念。
(作者为扬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