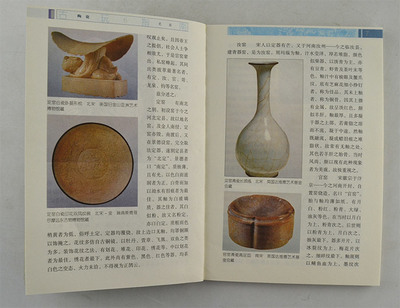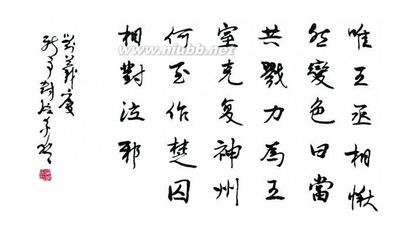《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是六朝志人小说名著,作为一部编撰之作,其编撰体例及取材宗旨很值得研究。今本《世说》全书条目共计1130条,各门分布不均,最多的是《赏誉》篇,计156条,最少是《自新》篇,仅有2条。由《世说》“以类相从”之体例和“丛残小语”之形制所决定,这些条目除按时序先后排列外,仍具有松动灵活(如个别条目放在另一门类里也未尝不可甚至更为恰当)、可再生递增[1]等特点,这也是后世《续世说》、《世说补》之类著作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说》的编排不够严谨、体例有失完善,恰恰相反,《世说》的条目设置,堪称匠心独运,在全篇乃至全书中的作用不容低估。今姑将部分条目和另一些尚存悬疑的条目略作考辨阐发如次。
《德行》第1条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此为《世说》开篇第一条,首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该篇总纲,交代《德行》篇的撰述中心乃为品行高尚之人;同时,此条也是全书之总关目,是我们把握全书选材、布局、主旨的一把钥匙。
首先,此条确定了全书记载时间断限的大体上限。《世说》为何要以汉末陈蕃事开篇?这一问题颇耐寻味,学者多有议论。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述缘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2]余英时则以为:“《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党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语》所收之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大于其下限也。”[3]“清谈之全集”说也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说也好,无不注意到《世说》这开篇第一条,实乃探寻全书结构及性质之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其次,“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一语,最早见于蔡邕《陈太丘碑文》,作“文为德表,范为士则”。而《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作“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蔡邕以“文”“范”对举,当与陈寔谥号为“文范先生”有关。[4]而陈寿以“文”“行”并称,则体现了当时以“文行出处”作为评价标准的时代风气。《世说》为记载名士嘉言懿行的小说家言,故将“言”“行”并置,既符合儒家“察其言,观其行”的人物评价标准,又彰显了全书通过“言”、“行”来表现人物——当“世”之“士”——风貌精神的命意主旨,同时也暗示了《德行》篇所载言行的“楷则”和“示范”作用。
“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晋宋时期之流行语。最早见于史籍对党锢名士范滂的评价。《世说·赏誉》第3条注引张璠《汉纪》:“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阳人。为功曹,辟公府掾。升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闻滂高名,皆解印绶去。”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传》亦称:“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赃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可见,范滂是此一评语的最早受用者。陈蕃(95?-168)为汉末清议领袖,在“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的人物品评中,被尊为“三君”之一。《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可见其在士林中影响之大,故“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用在陈蕃身上毫不过分。范滂(136-169)略晚于陈蕃而在党锢名士中最为著名。张璠和范晔用“升(登)车揽辔”描述范滂均为实写(受任之际),大概《世说》编者以为此句用来形容初到豫章任上的陈蕃之高标懿范也很恰如其分,故径直挪用,而手法上则是概括性的叙述。这一句虚实相生,气势沉雄,一下子就为读者打开了一幅苍茫悠远、风流蕴藉的历史画卷,此后的阅读,直仿佛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行”,但见嘉言懿行纷至沓来,如“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5]了。
要而言之,以清议名士陈蕃开篇,实则(1)奠定了《世说》全书的基调,体现了编者的编撰取向和宗旨。(2)确定了全书取材之大体限断,即鲁迅所谓“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这是编者对这一时期学术、士风嬗变内在联系整体把握的结果。(3)规定了全书以名士言行为中心的“志人”特质,后之学者,或以之为“清谈之书”[6],或喻之为“名士底教科书”[7],均可在此条窥其端倪。
《文学》第66条
此条为著名的曹植“七步成诗”故事,是《世说》全书中最能见出作者编撰思路的一个条目。《世说》各门所记,均按时间先后依次排列,一般先后汉,次三国,再次西晋,复次东晋,可谓井然有序。独《文学》一篇例外。该篇第1-4条记东汉马融、郑玄及服虔事,5-10条记三国何晏、王弼、钟会、傅嘏事,11-20条记中朝名士事,21-65条记东晋名士事,按照记载内容,依次是经学、玄学、清谈及佛学,几乎是一卷故事本的“学术流变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65条正记“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而至66条,忽云“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乍一看,时间和空间从东晋跳回至三国,打乱了全书的编撰体例;然细读之下,不难发现,第66-104条之所以又“从头开始”,乃在于其所记载的内容为诗、赋、文、笔之类,与前面的学术思潮判然有别,属于我们今天所言的“纯文学”领域。明人王世懋评之曰:“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这“一目中复分两目”,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奇怪的是他的哥哥王世贞在删汰何良俊《何氏语林》作《世说新语补》时,不明此理,竟将原书顺序打乱,复按时间顺序排列。故凌濛初谓其“按《补》依时次溷列,便失作者之意。”[8]
这里的“作者之意”,大概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属于篇章结构,即“一目中复分两目”,这是形式层面。其二,形式必然受制于内容,这一结构的形成,无疑与当时“文学”观念的嬗变密切相关。“孔门四科”中的“文学”一科,几乎是“学术”的同义词。曹丕《典论·论文》首倡“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章”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文体“八科”之论,又直接开启了陆机和刘勰的文体论。但是,真正从实践上对魏晋的文学观念加以系统梳理,还是南朝刘宋初年设置儒、史、文、玄四馆以后的事。如果说萧统的《文选》是对齐梁时代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学-文体理论的实践总结的话,那么,《世说新语·文学篇》则是魏晋文学观念反映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突出代表。[9]“一目中复分两目”,既保留了传统“文学”观念下“学术”的演变轨迹,又及时地总结了“文学自觉”的时代风气下,诗文歌赋历史变迁的“花絮”,体现了“纯文学”观念的日益成熟。
此条居于《文学篇》结构之要冲,上挂下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地位、作用之重要,非“七步成诗”之掌故名典不能当也。
《捷悟》第3条
此条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关于此事真伪,刘孝标颇有疑问:“按曹娥碑在会稽中,而魏武、杨修未尝过江也。” 又引刘敬叔《异苑》云:“陈留蔡邕避难过吴,读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寮,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祢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以此事属祢衡。《殷芸小说》卷四《后汉人》亦云: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魏武见而不能晓,以问群僚,莫有知者。有妇人浣于江者,曰:“第四车中人解。”即祢正平也。祢便以离合意解云:“绝妙好辞。”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10]
《殷芸小说》采录《世说》不少条目,但此条当从《异苑》中来。然考诸史实,祢衡与曹操嫌隙甚深,只做过地位低下的“鼓吏”,不得为“僚属”,而杨修曾在曹操帐下多年,若此事果有,也似属之杨修更为妥当。
然则,刘注的疑问又当如何解释呢?对此,陈垣在《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一文中解之甚详:“考孝女曹娥碑事,当时传播甚速而又甚广。唐以后载籍无论,最早虞预《会稽典录》载之;袁宏《后汉纪》载之;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又载之;刘义庆《世说新语》、刘敬叔《异苑》均载之,皆晋宋间人也。……至于原碑在会稽,魏武未尝过江一节,刘孝标注《世说》时已提出疑问,后来《三国演义》改为壁间悬一碑文,遂将《世说》注文轻轻解答,著者可谓聪明。《宋史》卷四二《谢枋得传》:枋得被系北来,因病迁悯忠寺,犹见壁间有曹娥碑,则又何必过江然后得见此碑也。”[11]
原来,曹娥碑既属名碑,仿刻自然众多,曹操、杨修所见,或即该碑众多“版本”之一,不必定为原刻也。《三国演义》不可尽信,而《宋史》当所言不虚。至于“妙解碑文”的故事,有杨修、祢衡二说,则是道听途说导致的传闻异辞,对于故事旨趣的传递毫无影响,倒也不必斤斤计较了。
《规箴》第4条
此条为今见唐写本残卷(仅存51条)首条,故颇引人注意。其文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上谏曰:“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刘注引环济《吴纪》称:“(休)锐意典籍,欲毕览百家之事。颇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为此时舍书。”陈寿《吴志·孙休传》与环济《吴纪》文字略同,然不提群臣规谏之事。细玩此条文意,群臣虽有直谏,但叙事重心则落在孙休辩解之语上,置诸《言语》篇或许更为允当。按《世说》乃纂缉旧文之作,分门隶事时不免模棱两可之处,王世贞作《世说补》,每每打乱旧局,以《德行》、《言语》之事属之《品藻》、《夙慧》之科者所在多有,如以“郭林宗造袁奉高”、“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等条入《品藻》,以“徐孺子年九岁”、“孔文举年十岁”、“钟毓兄弟小时”、“梁国杨氏子九岁”等条入《夙慧》,皆是;而《政事》、《方正》诸篇招致的非议就更多了。此其一。
其二,孙休射雉的爱好当是受到其父孙权的影响,而纳谏的雅量则相去甚远。据《三国志·潘濬传》注引《江表传》:
权数射雉,濬谏权,权曰:“相与别后,时时蹔出耳,不复如往日之时也。”濬曰:“天下未定,万机务多,射雉非急,弦绝括破,皆能为害,岂特为臣姑息置之。”濬出,见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坏之。权由是自绝,不复射雉。
此事既状写规谏者潘濬神情如画,又见出孙权的顾全大局,更合《规箴》之目。故余嘉锡加按语云:“今读《世说》及《吴纪》,知权父子皆有此好。但权闻义能徙,而休饰辞拒谏,以故贻讥当世。”[12]这里的“贻讥当世”,当据刘注引《条列吴事》“休在位蒸蒸,无有遗事,惟射雉可讥”数语。
问题是,《世说》为何不取孙权采纳雅言之事,而偏爱孙休“贻讥当世”之举呢?这就与《世说》的撰述旨趣相关。诚如鲁迅所言,《世说》乃“远实用而近娱乐”、“为赏心之所作”,故其遴选割舍,每每以“个性”、“趣味”为先,一本正经的题材反而不为所重。此条孙休答语,虽属巧言,但婉转关生,比之孙权的“不复射雉”,孙休的“耿介过人”一语,实属夫子自道,更可见其真性情。《世说》之门类,虽各有定规,然“经”、“权”之间,决定取舍的杠杆,仍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在这个“人”字面前,国家大势、仁义道德、是非功过等等,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和“陪衬”。
《轻诋》第24条
《世说·轻诋》第24条记载: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又《文学》第90条: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
两条对照,可知王珣(字东亭)所作《经王公酒垆下赋》,才是导致“《语林》遂废”之原因。按此条“王公”当为“黄公”,即《伤逝》2所载王戎叹逝所经之“黄公酒垆”。[13]
王戎是否有此事,后人颇有怀疑,该条刘注引《竹林七贤论》称:“俗传若此。颖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事,皆好事者为之也。”王珣所赋当即为王戎此事。谢安显然赞同庾亮的说法,故庾龢(字道季)“读毕”该赋才会出言讥讽。但谢安之所以“都不下赏裁”,除了《语林》传写“不实”外,当还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在起作用。谢安与王珣素有嫌隙,王珣、王珉兄弟皆为谢家女婿,因猜疑致嫌,谢安既绝珣婚,又离珉妻,由是王、谢二家遂成陌路。上引《轻诋》第24条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此事说:“时人多好其事(指《语林》),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庐》,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对谢安的“滥用权威”和时人的“个人崇拜”大加驳斥。
事实上,如此条末句所云:“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可知《语林》并未就此“遂废”,至少至《世说》成书的刘宋时期还“健在”,只不过去掉了开罪于谢安的那两条而已。刘孝标作注时或许也见过《语林》原书,其大量援引《语林》入注就是明证。周楞伽论及《太平广记》转引《殷芸小说》实多出《语林》时,说:“《世说·文学篇》所记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后因记谢安语,被安诋为不实,其书遂废,然读者仍欢迎不衰,传写者乃冠以《杂语》、《杂记》、《小史》等名,究其文,无不采自《语林》,故非《广记》从《小说》转引,反系《小说》从此类杂题书名中传袭《语林》之文也。”[14]
这里的《杂语》当即孙盛的《异同杂语》。既然檀道鸾就可以对谢安“挫成美于千载”的行为表示不满,那么,孙盛暗中将“裴氏学”溷入自己的著作(如《杂语》)使其流传后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其实,何止一个孙盛,《世说》编者大量采用《语林》入书,不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表现么?今之学者多以此条故事为口实,论证当时小说偏记亦必须“征实”,进而坐实《世说》亦全写“真人真事”的主观臆断,恐怕难免失之不考。
《方正》第34、35诸条
《世说》的条目安排,看似纷繁无章,实则乱中有序。其一,一门之中,以所记人事的时间先后为顺序;其二,就全书而言,一个人物的众多故事被打散,归入不同的叙事单元,统整起来不啻为一篇篇“人物列传”;而就每一门类而言,记事的链条又每每以人物为单位,环环相扣,组成一组组藕断丝连、相对独立的“故事链”。这样的“故事链”一般有两种情况。其一,连续的几条故事有同一个人物作为记述的主体(主人公)。例如,《德行》第2-3条记黄叔度,4-5条记李元礼,6-8条记陈太丘父子;《言语》第3-5条记孔融(153-208)及其二子;《雅量》第4-6条、《俭啬》第2-5条记王戎;《豪爽》篇1-4条记王敦;《贤媛》第6-7记许允妇;《任诞》篇连续十余条记阮籍、刘伶;《假谲》第1-5条记曹操;诸如此类。其二,连续的几条故事虽不共有一个“主人公”,但却有一往来穿梭的“线索人物”,表明所记载的人物大体处在相同的时段和空间,只是“主”、“宾”的位置在不断变换。例如,《言语》第55-61条分别记桓温和简文帝,二人仿佛轮流“坐庄”一般,叙事的重心也随之变换。《雅量》第27-35诸条,所叙人物有桓温、郗超、谢安、王坦之、孙绰、支道林、戴逵等,但起到关键的“枢纽”作用的却是谢安。此外,还有一些条目,由于前后关系至为紧密,似乎是一对被拆散的“孪生兄弟”。比如,《方正》篇的两条故事便透露了其中消息: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雠,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 (《方正》34)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阁下不愧荀林父耳。” (《方正》35)
这是紧邻的两个条目,所记的主要人物是钟雅。有意味的是,“钟雅”之名在两条故事中只出现了一次。后一条的“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这里“钟”,显然是承接上文语意,所指当为“侍中钟雅”。也许,这是编者的一时疏忽,因为类似情况在《世说》中仅此一见。但它十分清楚地显影了编者在编撰时的匠心所在。关于此点,古人亦有会心。南宋刘辰翁批点此条说:“按此‘钟’因承上文,遂不言名字;《世说》原有断而不断之意,不得擅改。”[15]这里的“断而不断之意”,不是将《世说》编撰体例的幽微妙处一语道破了么?
有趣的是,因为“断而不断”,有时还会出现“合二为一”的现象,如今本《世说·赏誉》第5条:
锺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余嘉锡按此条说:“‘吏部郎’以下当别为一条。”他的根据是:“‘吏部郎’以下出王隐《晋书》,见《御览》四百四十五。”细审文意,余氏所言诚非妄语。
当然,由于这样一条“故事链”的存在,各个相邻条目的故事,就未必能够完全遵守“时序”来排列。比如《言语》篇3-5条记载孔融(153-208)及其二子的故事,从孔融十岁到他被杀,时间跨度为几十年;而紧接着6-10条记载的陈太丘父子、荀慈明、袁阆、祢衡、庞统以及刘桢等人的言行,有的还在孔融被杀的208年以前。不过,为了编织一条条相对独立、引人入胜的“故事链”,任何一种对体例的“不忠”都是值得的。
【注释】
[1] 据《太平广记》及《御览》所引,不排除今本《世说》有删去古本个别条目的可能。
[2] 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页217。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307。
[4] 《三国志·陈群传》注引《先贤行状》称:“大将军何进遣属吊祠,谥曰文范先生。”
[5] 见《世说·言语》第91条。
[6] 此观点以陈寅恪为代表,见前引《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不过,诚如余英时所说:“按陈先生注重清谈思想之流变,故重视《世说》年代之下限,其说诚不可易。但若从士大夫新生活方式之全部着眼则尤当注意其上限,清谈特其一端耳,而《世说》所载固不限于清谈也。”参见《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想》,载其所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转引自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页170。
[7] 说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鲁迅全集》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09。
[8] 参见刘强《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页145。
[9] 关于《世说》文学观念对文学理论之影响,今人萧艾撰文指出:“当前跻于‘显学’的《文心雕龙》以及素负盛名的昭明《文选》,问世晚于《世说》六十余年至八十余年。前两者都着重于文体分类,在各种文体中以诗赋为主,不能否认皆对后者有所借鉴。凡《世说》所写到的诗、赋、序、颂、赞、论、书、表、牋、诔、册文、露布,《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都纳入了文学范畴。惟裴启《语林》、袁宏《名士传》均见弃于外。而这恰恰是刘义庆文学眼光高于刘勰与萧统之处。”见前揭《世说探幽》,页147。
[10] 参见周楞伽校注《殷芸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页89。
[11] 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573。
[12] 见前揭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页551。
[13] 《世说·伤逝》第2条载: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14] 见前揭周楞伽校注《殷芸小说》,页158。
[15] 参见刘强《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页192。
(按:此文写于2003年,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2期。收入《世说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世说新语》精读参考资料
一、历史 —古代
1、《后汉书》,[南朝宋] 范晔撰,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
2、《三国志》,[晋] 陈寿撰,[宋] 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3、《晋书》,[唐] 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4、《宋书》,[梁] 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5、《资治通鉴》[宋] 司马光撰,中华书局1956年校点本。
二、历史—现代
1、《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撰,万绳南整理,黄山书社,1987。
3、《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撰,上海三联书店,1955;《续编》,1959。
5、《东晋门阀制度》,田余庆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中国文化史》,柳诒徵撰,东方出版中心,1988。
7、《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朱大渭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三、思想、哲学、宗教
1、《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撰,中华书局,1999。
3、《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撰,人民出版社,1957。
4、《魏晋的自然主义》,容肇祖撰,东方出版社,1996。
5、《魏晋思想论》,刘大杰撰,商务印书馆,1939。
6、《魏晋玄谈》,孔繁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7、《魏晋清谈》,唐翼明撰,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8、《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9、《佛教征服中国》,[荷] 许理和撰,李西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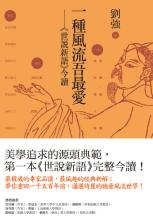
四、文学、艺术史
1、《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撰,《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中古文学史论集》,王瑶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中古文学系年》,陆侃如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撰,中华书局,1996。
6、《美的历程》,李泽厚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六朝美学》,袁济喜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8、《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9、《中国小说源流论》,石昌渝撰,三联书店,1994。
五、影印《世说新语》古本
1、唐写本残卷,民国五年( 1916)罗振玉四时嘉至轩影印本。
2、宋绍兴八年( 1138)董(分+廾)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本。
3、清 光绪十七年( 1892 )王先谦思贤讲舍本, 198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六、《世说新语》校注
1、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国学论丛》第一卷4号;《序》与《凡例》分别见于《文学同盟》11、13期、1928年)、
2、李审言《世说笺释》,(《制言》杂志第52期、1939年七,收入《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3、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文哲季刊》7卷2、3期;1942、1943年)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 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 ,中华书局, 1984。
6 、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7、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台北宏业书局, 1969。
七、《世说新语》研究专著及工具书
1、王叔岷《世说新语补证》, 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5年。
2、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3、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 1992。
4、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5、蒋凡《世说新语研究》, 学林出版社, 1998。
6、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探究》, 台湾学生书局, 1973。
7、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
8、张振德等《世说新语语言研究》, 巴蜀书社, 1995。
9、井波律子《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学林出版社, 1998 。
10、王守华《世说新语发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11、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
12、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3 。
八、《世说新语》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 部分 )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余嘉锡《世说新语辨证》,(见《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 1980)。
3、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6期)。
4、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语跋尾》,(《清华学报》2卷2号;1925年)。
5、傅增湘《世说三卷:日本帝室图书寮观书记》(《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4 卷1 期、1930年2 期)。
6、赵罔《世说新语刘注义例考》(《国文月刊》83期,1949年2期)。
7、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星期评论》1940年10期,后收入《美学散步》)。
8、冯友兰《论风流》(《哲学评论》第四卷3期、1944年)
9、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1期)。
10、白化文、李明辰《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文史》第六辑)。
11、周本淳《世说新语原名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3期)。
12、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探》,(《文献》1986年1期)。
13、钱南秀《传神阿堵:〈世说新语〉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文学评论》1986年5期)。
14、刘文忠《世说中的文论概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三辑)。
15、王能宪〈〈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文学遗产》1992年2 期)。
16、段熙仲《〈搜神记〉与〈世说〉》,(《南京师大学报》1981年3 期)。
17、汤亚平《〈世说〉中的文学理论概观》,(《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古典文学专辑)。
18、程章灿《从〈世说新语〉看晋宋文学观念与魏晋美学新风》,(《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1 期)。
19、张丹飞《论贤媛之“贤”:从〈贤媛〉门看〈世说新语〉品评妇女的标准》,(《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3 期)。
20、萧艾《中国文化史上第三大转折时期上流社会的真实写照》,(《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21、汤用彤《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历史研究》1954年3月)。
22、汤一介《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学术月刊》1963年1期)。
23、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文史哲》1981年6期)。
24、宁稼雨《“世说体”初探》,(《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六辑、1987年10月)。
25、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与清谈之关系》,(《文学遗产》1997年1期)。
26、[韩]金星迳《〈世说新语〉:历史向文学的蜕变》,(《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3期)。
27、梅家玲《论〈世说新语〉的叙事艺术》,(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1994年4卷 期)。
28、侯忠义《〈世说〉思想艺术论》,(《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4期)。
29、刘强《20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0年4期)。
九、与《世说新语》相关的部分其他古籍
1、《老子校释》,朱谦之校释,收于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
2、《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1983。
3、《人物志》,[魏] 刘劭撰,收入《汉魏丛书》。
4、《西京杂记》,[晋] 葛洪撰,程毅中校点,中华书局1985。
5、《裴启语林》,[晋] 裴启撰,周楞伽辑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6、《搜神记》,[晋]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
7、《古小说钩沉》,鲁迅辑校,《鲁迅全集》第8卷。
8、《颜氏家训集解》,[北齐]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