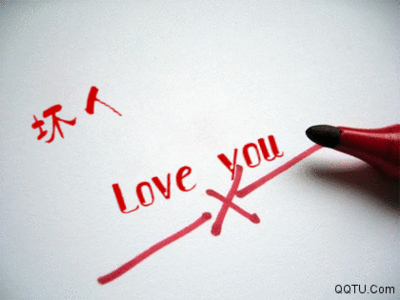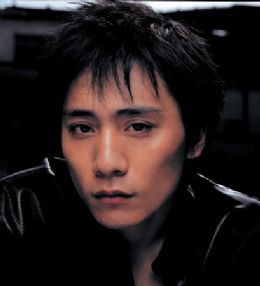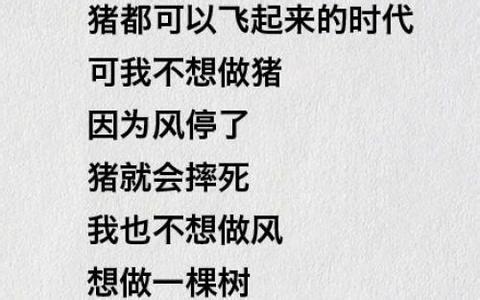摄影/王凯
“屏风”这件中式家具,好像早已退出家居舞台,跻身到“收藏品”行列。但我在淘宝搜索时,查出“屏风”的产品有28.39万件,比家家都有、再平常不过的“鞋架”的搜索结果27.63万还要多。
真是意外,这件诞生于传说时代的家具,竟然有这么长的生命力。
摄影/王凯
《物原》里记载着“禹作屏”,禹,就是那个治水的大禹。《礼记》中,说周公(姬发的弟弟)在明堂向各地诸侯颁布制度法令,在布置明堂时,就借助了屏风。这时的屏风分隔区域、昭示身份,代表着权利。
时代更迭,屏风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的传世名画里,随处可见的屏风身影。它不止丰富了中国画的美与趣,还有画师对“时空”深深的思考。
可点开图片稍看细节
元
刘贯道
《消夏图》
画中主人在仕女环绕中乘凉,他身后有一个屏风,屏风中画着主人坐榻,小童手奉博山炉立于侧,在画中深处,还有一座山水屏风。这种画中有画的“重屏”样式,是五代以来画家喜欢采用的表现手法,十分有趣。
明末清初
陈洪绶
《西厢记》插图
中国人绘画,讲究“疏可跑马,密不透风”,这幅画的笔力全着于屏风之上,整个画面除屏风之外,别无他物,但是,也营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室内空间。屏风之前,崔莺莺站在一个私密的角落,读着张生的信;屏风之后,红娘探着头,能看出她传递这封信的状态,和替小姐高兴的心情。
明
仇英
《竹院品古图》
供图/故宫博物院
仇英的《人物故事图册》全册十开,这张“竹院品古图”藏于故宫。两座屏风立于竹林前,一画花鸟,一画山水,文人坐在画屏内,品玩古玩字画。竹林之中,清风摇竹,方桌旁边,两只狗嬉戏,古代文人好不悠然自得啊。
明
仇英
《园居图》

明正德年间的王献臣敢为直谏,不满仕途的险恶,远离皇宫,在故乡苏州建起“拙政园”。仇英为其画了一幅《园居图》,将这位儒臣的理想园林绘于笔下。这幅长卷中的主屋,前堂陈设有一架山水屏风,点明空间的“中心”之位,也显示出中式园林若隐若现的神秘美感。
五代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
古人爱临摹名画,《重屏会棋图》原为五代周文矩所作,今已逸失,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相传为宋人摹本,美术史家巫鸿认为,与宋本相比,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明代摹本更符合原作者的原意。宋本中最后一重屏的左右两扇是对称的,而明本中右扇比左边的长出近一倍。
局部
全图示意
五代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的这处局部很有味道。若通读画卷(上图示意),会发现隔屏“交谈”的这两位来自不同时空:男子身在“清吹”一场,却背靠屏风开着小差,与“散宴”场景中仕女交谈;仕女轻倚屏风,手臂抬起似有所指,仿佛在邀请男子移步惹得观者费尽思量,浑然忘记屏风所起的转换空间作用。
明
商喜
《朱瞻基行乐图》
中规中矩的帝王行乐图中也可见屏风身影,不过在这副名为《朱瞻基行乐图》“马球”一场中,屏风的作用,不再是过渡,而是借助作为球门的存在,“预示”出了画面未及展示的马球比赛高潮。如此巧思,令人莞尔。
明
仇英
《弄玉吹箫图》
春秋时,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箫,和也善于吹箫的仙人箫史结为夫妇。穆公筑凤台,两人吹箫引来凤凰,后双双乘龙凤升天而去。这张图就描绘了弄玉在凤台吹箫,引来凤凰的情景。 图中的高台上屏风之后,仕女正摆放古董,可见画作者将自己带入了故事中,借用小小屏风,让生活风雅的明代文人,当上了战国时浪漫故事的男主角。
供图/艺博
古代不少屏风现在的确是收藏品中的贵族,不仅因为工艺精细、世间少有,还有就是太美。这是嘉靖年间,一位扬州工匠将宝石、象牙、珊瑚等名贵材料组合,发明了富丽堂皇的家居装饰手法“百宝嵌”,图为“百宝嵌”的传世十二条屏。
供图/corbis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传世屏风流传到了海外。虽然很难切身理解其中韵味,但西方人还是喜爱屏风所带来的神秘典雅的东方味道。图为已故著名美国摄影师Gordon Parks坐在他心爱的东方屏风前。
摄影/王凯
也许人们会说屏风的实用性不足。但如图这样精美的屏风,置放于中式屋宇内,人们除了享受其带来的静谧典雅之外,谁还会去计较其不可坐、不可卧、不可储物的缺点?
资料与图片来源:
《中华遗产》2011年10月
编辑整理/风物君
END
1497年有什么特殊吗,其实就是文中画家仇英出生的那一年啦
本文由地道风物(didaofengwu)微信编辑组整理编辑,欢迎转发分享,转载请于微信后台留言,勿擅自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