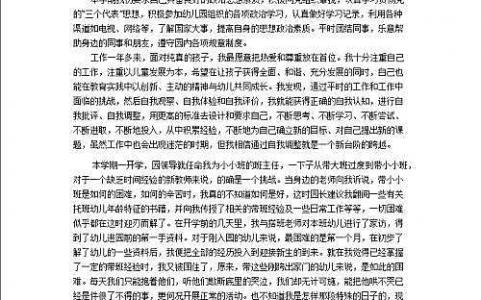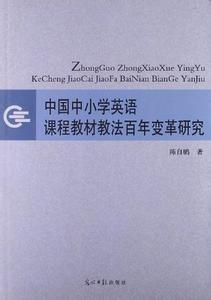《哆啦A梦:伴我同行》
很多年过去了,往事已如云烟,可是那个雪夜,她陪着我散步,温暖了我人生的路。
前言
一周前,“人间”编辑部向所有读者发起了关于“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失联了”征文。
感谢读者们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或是遗憾、或是难舍、或是不解、或是感怀的故事。
无论我们是否依旧拥有,希望那些曾经的感动和幸福,能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1.
从小我就是个孤独的孩子。虽然有兄妹,可是很少交流。
在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叫艾苹。比我大一岁,圆圆脸,说话细小,总是微微笑的样子。
假期里我们总是一起玩耍。两个十岁多一点的小女孩,曾经拿着十块钱,就坐车一起去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又傻傻地坐车回来——仿佛做了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满足的样子。
每到过年,艾苹总有一些可以自己支配的压岁钱,而我的都会被我妈拿走还给亲戚家的孩子。她用压岁钱在新华书店买了很多书,直到现在还有一套《红楼梦》放在我家,几经迁徙,我一直舍不得丢弃。
偶尔夏夜里睡不着,艾苹会悄悄从家里溜出来,走过两条街,到我家敲我房间的窗户,然后我俩就在半夜黑暗的小街上溜达——直到她妈妈猛地发现女儿不见了再出来找——从不曾有人会发现我夜里不见了。
就这样度过整个青少年时光,直到各自读书工作离开了家。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她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她去了上海打工、又辗转去了新疆。再到后来,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个当地黑社会成员。在她的描述中,他是那种只有一碗粥也会留给她的人。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送她走的,只知道第二天,我冲动地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长信,大意是:你改过罢,这样才能真正给所爱的人幸福。
一周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到楼下去捡被风吹落的床单,经过大门时,一位个子不高,似乎在那里站了很久的人向着我说话:“你是不是xxx?”
我看一眼,并不认识这个人,就转头离开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艾苹的丝毫消息。
托父亲去帮我打听她父亲,也说是退休后就搬走了。又是十多年过去,估计我们是不会再见了。
可是那个腼腆而倔强的女孩,如今在哪里呢?你还好么?
——anemone
2.
大学时,我曾经和一个学姐感情甚好。
毕业后我应邀搬去上海和她同住,两人磨刀霍霍,决心一起干一场大事业。大约过了半年,创业的热情冷却下来,她也在父母安排的几轮相亲后,认识了喜欢的男孩。直到有一天,她跟我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还是比事业更重要。当时我正好失恋,又没工作,在我不知道该拿生活怎么办的时候,她礼貌地请我搬出她的家。
断了念想,我搬回香港,找了份工作,安心地开始一个人的新生活。刚开始我们偶尔也有交流,她家境优渥,生活无忧,男朋友事业有成,两人感情很好。没多久她又投身于新的创业计划,猫屎咖啡馆,民族风什么的,最后似乎都不了了之。我们各忙各的,渐渐也就疏于联系。
两三年后她找到我,通知我参加她八月的婚礼。可能因为那时处于旧日同学结婚高频期,我变成了个极端主义者,对婚礼很是排斥。我跟她说择日专程拜访叙旧,婚礼还是不参加了。
我当时想,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吧,没想到她却很生气。
很快,在微信上,我们先是严肃地探讨了一番价值观上的分歧,然后,不知怎么的,两人开始翻起“同居”时的旧帐——谁吃完饭老是不洗碗,谁烤了饼干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对方而是送去给隔壁新结识的邻居……什么烂谷子的事儿都不顾情面地挖了出来。
她说我自私老想着探索新世界新朋友,全然不念旧情;我反驳她,说她是公主病小心眼……就像两个心胸狭隘的女中学生,以友情的名义不断相互指责。
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拉黑了对方,从此再无往来。
后来当我看到那句“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黑色幽默时,心想真是生活洞见啊。
之后的几年,偶尔回想起,只觉得自己当时幼稚得好笑。
一起居住的那段日子,我们一起看电影聊文学讲黄段子,欢乐远多于矛盾。
前些日子我重回微博,看到了她的近照,依旧漂亮,又得知她刚刚生了孩子。她调侃自己25岁前忙着建立各种世界观,25岁之后又忙着将其一一推翻;她笑自己也不免俗地在计算机里为女儿新建了一个名叫"My Angel"的相片文档。
我想,她应该过着她想要的幸福生活吧。至于我,依旧未婚,偶尔不安分,日子也踏实自在。主动找她和解的想法有时会一划而过。
但,还是就这样吧。

——李不圆
3.
我总觉得自己是因为成绩,弄丢了自己的发小们。
小时候,家人从没管过我学习,记忆中,我总是等到第二天上学时,在老师们的冷嘲热讽中抄着王珂欢的作业,然后才能回座位上课。
就算后来家人开始管我学习了,我也养成了根本不记作业的习惯,每次回到家,还是会灰溜溜地跑去问王珂欢,今晚作业是什么。
还有邱政圆。那时候,每次写完作业,邱政圆都会来我家看《恐龙骑士》的光盘。妈妈答应我,只要我表现好,就带我找邱政圆玩。我记得两人总是恋恋不舍,直到临走时,邱政圆还半赖皮半认真地说,“你一秒钟之后就要回来!”
后来,大概是我学习一直不好,家长们衡量自家孩子“朋友”的标准,就是他的成绩是不是前20名。我的发小们,很快就像不认识我一样。
上了高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遇到了邱政圆,当时很惊喜,但更多的则是失落——他一直是班级前五名,而我呢?
他见到我很高兴,一直摇我的肩膀,和我说话。可我却只是一直默默地看着他。
如今,我终于上了大学,一切都好转了。能把我的朋友们都还给我吗?
——刘匯洋
4.
高二的时候,数学成绩奇差,一个人能拖整个班的后腿。班主任费心劳力,把数学课代表安排在我旁边,坐了整整一年。
心形脸,长睫毛,姑娘的字龙飞凤舞,很有男子气概。她教我做题,扯我去操场偷看她喜欢的男生,还教我对着老师的背影翻白眼来缓解压力……
一次课上,数学老师布置了一道难题,她目光遍扫了全班,最后像是戏谑一般,拖着腔调念出了我的名字。后排的男生全都笑了。
我在黑板上磨磨蹭蹭地做完了第一问,就再也无法继续了。老师脸色冷峻,瞟了我一眼,“你看我干吗?我脸上有字吗?”
待老师巡堂走远,背后有人小声喊我,一回头,第一排的同学迅速扔给我一个纸团。我手抖得厉害,打开,里面是她写的答案,龙飞凤舞的。可还没来得及往黑板上写,就听见老师在背后大喝一声:“手里捏的什么?拿出来!”
是否被体罚,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一顿羞辱忘不了。我被赶出教室,课间接受了整层楼的“参观”,她也被老师说了重话,在教室里罚站,等我们都坐下来,两人哭作一团。
高三,学校提了一个“火箭班”,安置在教学楼顶层。她选上了,我没有。我还是会等她一起吃饭,一起放学,但很快她就有了新朋友,年级前几名的那种。
高考前三个月,连着两天她都没有上学,我很担心,问同学问老师,大家都说,“她压力太大了。”月考年级排名下滑10名,她正处在一本线的边缘,她的班主任甚至向我抱怨:“她妈妈像疯了一样,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问她的情况。”
那天下午,我第三次去顶层,终于看到了她。喊了半天,她也没有动,最后出来递给我一张纸条,红着眼说:“以后,你不要来找我了。”她奔进教室,我打开纸,是龙飞凤舞的字:“我妈不让我跟成绩差的学生玩,三个月,你要加油!”
我只知道在社会上,人没钱会被忽视,却不知道学生时代成绩不好,也会被抛弃。那天,我穿了一件黄色毛衣,一身的冷汗,一脸的泪。
后来的故事就很老套了,我是那届高考中窜出的一匹黑马,还竟然和她上了同一所大学。听同学说,她母亲得知我的成绩后感叹:“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四年里,我们只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狭长的楼道中,我们四目相对擦身而过,她先低了头;第二次,她站在教学楼的平台上问了我一句:“最近怎么样?”
第三次是在图书馆,那时候已经大四了,她正备战考研,看我坐在不远处看闲书,顿时面色凝重。
不一会儿,她就拉起同学匆匆离去。我放下书,走到她的桌边,看到废纸上的那些字还是龙飞凤舞的。只是,再也不能揉成一团了。
——萝卜君
5.
他是我高三时的室友,插班来的复读生。
他很聪明,所有的问题似乎总是看一遍就懂。可那时的他,却总是做着“艺术家”的梦。
他很少去上课,只是一个人在宿舍里不停地画呀画,画他眼中的世界。他的字也写得很夸张,连在一起看有种很飘逸的美感。
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得了精神病,只和哥哥相依为命。看起来,他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却和我无话不谈。
那年毕业,他还是没考上大学。我离家上了大学,再也没有他的确切消息。
听说后来,他再次复读,考上了和我一个城市的大学,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联系上一个人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直到2003年,我去上海金茂大厦游览,坐上电梯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他。
我确信那一定是他,他举着小旗子,带着一对国外的老太太游览。待我回头再找时,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很遗憾的,就此擦肩而过。
——Zh
6.
我高中偏科严重,班主任便安排她坐我的同桌。
我至今依旧记得她飘柔气息的发梢,左边脸颊小酒涡,两颗小虎牙,芬芳馥郁的呼吸。
她的温柔耐心成了我的药。
高考结束后,我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她发挥欠佳只考上了二本。那年暑假,她和同村的另一位男孩骑了六十里的摩托车来我家,极力劝我回去和她一起复读,还说愿意继续帮我补课。但我害怕再回高三的炼狱,拒绝了她。
大一时,我总能收到她的“每周一信”,怕打扰她冲刺高考,我从没回过。
第二年秋天,我又不断地收到她从遥远大学寄来的信、围巾、毛衣、手帕,以及许多许多的书,书里还有她夹着的一些照片。偶尔跑去传达室接听她打来的长途电话。我总是不知所措,始终也没有回过信。
后来我就先毕了业,工作结婚生子,与她也失去了联系。
多年后,我们在深圳偶遇,她说自己过了30后,被父母逼着结了婚,两年后又离了婚,独自带着儿子,在深圳做国际贸易还算不错。
我们在露天咖啡厅说笑,她冷不丁问我,那几年你为什么不理我?我说我成绩不好,一想起你总会觉得自卑,再加上那时候一直以为你有男朋友。她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我又一次沉默离开。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坦然面对这段谈不上是初恋的“初恋”。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学渣,更是人渣。
——刘华
7.
同学录里有她的笔迹,我和她的大头贴,都没有发黄。
五年级时,班里转来一个女生,和我一样留着短发,比我高了一个头。自那开始,放学路上,夕阳西下,总能看到我们俩在打打闹闹。
她的家我只去过一次。
村里的窑洞大都是依山而建,一排排嵌在山上。那天中午,我们顶着烈日,爬了一级又一级台阶,到头来我也没记清她家究竟是第几排。
她家的院子有两孔窑洞,家里的地板擦得光亮,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也没有沙发。她的母亲散着头发,穿着朴素,坐在炕上缝着衣服,见我们回来,温柔地笑了起来,和她一样。
转眼上了初中,她去了乡镇中学,由于父母总是忙于生意,她成了住校生。渐渐地,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带着小礼物去看她。教室的窗户里透出了阳光,在深秋中稍许增添了一丝暖意,教室里她一个人在上自习,陪伴她的只有一些呆笨的桌椅。
见到我来,她开心极了,我们又像以前一样,愉快地聊起天来,直到太阳从窗边移走。
很快,她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高一的时候,她寄住在亲戚家。亲戚家有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初中,再加上她。屋里点着昏黄的钨丝灯,但仍旧黑乎乎的,狭小的空间里挤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东西。
我去找过一次她,依旧没记住具体是哪一排的哪一孔窑,只记得自己进屋没多久,便急忙把她拉出了乱哄哄的家。
很快,进入考准备阶段后,她也消失了。不知从哪一日起,她的QQ就再也没有回复了。没有手机号,我只能不断地给她的QQ发消息。偶尔在路上遇见小学的熟人,就赶快凑上去问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但我一直没找到她。
直到高中结束之后很久,她的最后一条空间状态仍然没有变化。我幻想过她去我家找我,但或许她并不知道我家在哪里。也想去找过她二姨家,却怎么都认不清是哪一孔窑洞,也许她二姨早已带着孩子搬走了。
她也许去了兰州。我想。
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对于兰州,县城是那么小、那么远。
——党彧卓
8.
我和他在一条街上长大的,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15岁那年,他杀了人,我偷家里钱坐车去看他,给他送吃的、送穿的,在铁窗的对面,他流着泪说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说那就没人会来看你了(他父母我从未见过)。
后来他自杀了,我也就真的没见过他了。
——清醒夜
9.
杨大鹏是我整个高中时代最特殊的存在。
关于他的轶事,在我还没跟他正式成为室友之前,就已有所耳闻。
他浑身上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头坚硬地如同一根根钢针的头发,加之天生浓眉大眼,很容易让人在看到他时,自然联想到“怒发冲冠”。他能用舌尖轻轻松松就舔到鼻尖,这个绝技为他攒足了人气。
复读那一年,似乎只有他是永远快乐的,当他穿着明显不合身的“七分裤”,蹬一双布鞋,在寒冬腊月,蹦着跳着,从校园里经过时,收获的回头率简直令所有人都甘拜下风。
我记得那时,杨大鹏和我一起端着大碗,蹲在初春的校园一角,披着阳光大口吞面。我嚼一颗蒜瓣,搅拌着面条,漫不经心地问他:“你感觉压力大吗?”
杨大鹏咂着嘴,操着满嘴红油:“兄弟,有啥压力不压力的,考上就考上,考不上也不丢人,开心就好!”
我把碗里漂起来的肥肉直接扔到杨大鹏的残汤里,他拿起筷子小心翼翼夹起来,甩进嘴里,很享受地嚼一嚼,仰起脖子喝口面汤。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反射初春的阳光,晶莹透亮。
老天有时候也偏心,复读那一年,他勉强爬过分数线,去了河南一所普通院校,我们都为他感到遗憾。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曾试图通过关系,拜托同乡打听他的下落,但他就像忽然消失了一样,留给大家一个谜。
——马鹏波
10.
往事如烟,翻起来也是满满的眷恋。
2000年冬天,期末历史考试前,教授把自己的包往讲台上一放,就转身出去了,几个同学赶快跑上前,翻看起教授的讲义来。正当他们看得入神,“教授来了”的呼喊声让所有人一哄而散。
我坐在座位上看小说,并没有上去看题,教授大声质问是谁偷看了题,没有一个人回应。
忽然,教授指着我,“你看了么?”
“没有。”
教授发出几声冷笑,又叫了几个人的名字。自然都问不出什么。
教授气不过,把我们几个全部叫到办公室,让我们写都是谁看了题。我想,反正法不责众,就把班同学的名字全部都写了一遍。
结果,我想错了。其他几个人全写的胡编出来的名字,而我,则成了全班同学的敌人。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班里都没人理会我。在挂科等于不能毕业,且考试成绩全看教授心情的专科学校,大家对我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那时候,班里有一个此前与我关系很普通的女生牛慧丽,她辗转找来历史教授的电话,还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有一天,还专门陪我在雪地里散了很久的步。
尽管后来,班里没有一个人因此事被挂科,我却看清了人心。
毕业后,我也请牛慧丽走了一段路,当时已经有了其他想法,可是由于种种,我们失去了联系。
2003年,单位有了网络,我四处找寻过她。可是大家四散在各处,没人知道她究竟在哪里。
很多年过去了,往事已如云烟,可是那个雪夜,她陪着我散步,温暖了我人生的路。
——上下
11.
那三年,所有的记忆都和她有关,就像谈了一场恋爱。
刚上初中那会儿,学校举办迎新运动会,我早忘记自己报了哪些项目,只记得在观众席上坐着,旁边两个姑娘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聊着某部漫画。可能天生不会招人待见,我到底还是忍不住插了嘴:“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个漫画比起XXX根本不算精彩……”
旁边的姑娘果然立刻扭过头,却眼睛发亮地看着我:“你说得太对了!”很快,我们便一起,聊完了整个运动会“上午场”。
当时学校操场没有真正的观众席,椅子都要学生从教室里自己搬下来,椅子腿是铁铸的,很重,上下台阶容易打到腿。我们班在最高的5楼,那天下午,我到得比她早,一个人径直把两把椅子扛下楼。
一切顺其自然,我们在放学后骑一辆自行车奔往书店,如果路上要下雨,她就帮我把自行车骑回家(她家离学校近),让我坐公交,虽然好几次雨下得太快,把她浇成“落汤鸡骑士”。
冬天我要坐公交,她陪我在车站一等就是半小时,等我上了车,她一个人在冬日寒冷的夜幕里独自走回家;周五放学早,我们一天份的话还没说完,站在学校附近的路口继续聊,时间不知不觉从4点走到6点,直到我家人放不下心来学校找,横竖都少不了一顿骂。
很少听她谈起她的家人,每次电话打到她家,接电话的都是姥姥,用朝鲜语说着我听不懂的“喂喂”;她的资料卡上,民族那栏填写的是:国外朝鲜;她也有两个名字,“日华”和“日花”,“日花”是朝鲜语的,发音很好听。当时的我,不明白这些有什么意义,交朋友和家庭有什么关系?何况她会的朝鲜语都不超过10句啊。
直到升学的时候,她和别的同学才显露出不同,她是永远的“借读生”,能上哪所高中,不取决于成绩,只取决于哪所学校肯收她爸爸给的借读费。
我们依旧固执地约定上同一所学校,那是县城里最好的一所高中,她家人据说已有所打点,而我只要再努把力就能得偿所愿。
我最终顺利上了那所高中,报道的人群里却没有她。在初中时代最后的那个暑假,她的父母忙于离婚,没人帮她申请新学校。
她告诉我,“晚一年,晚一年我就会去上学了。”
“嗯,等你。”
上高中后,我依然常常给她打电话,最开始是打到姥姥家,后来渐渐变成了各路亲戚家,我在本子上记了她四五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等我打给你吧,让他们接到电话……嗯,不太好。”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穿着初中时的旧毛衣,但当时天已经渐暖,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我还是什么都没问,依旧说等她早点来学校。“我应该不会上高中了,他们给我找了一所中专,毕业分配工作那种。”她佯装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她祝我生日快乐,“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礼物,下次见面就能送给你啦。”然后我们在依旧熟悉而天真的快乐中挂了电话,我恨自己的天真。
在那之后很多年,我家都没有换过电话号码,却再也没有接到她的下个电话。我终于忍不住开始找她,电话打到她亲戚的店里,最开始回复是“不在”,后来声音也换了新的一批,很快,再没人认识她了。
也曾试过在社交网络上找她,“日华”和“日花”都搜过,从最开始没有这个名字,到后来重名的都注册了好几页,从来都没有她的影子。
10年里,我总时不时幻想与她重逢的场景,从最初的戏剧性,到后来的渐渐尴尬。10年前,我想过等将来赚了钱,请个私家侦探;10年后,我已经放弃了寻找。
不是不想见她,只是突然意识到,她再不联系我,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她不想再见我了,我成了她抛弃在旧时光里的朋友;二是她发生了什么,或许人已不在,而无论哪个结果,都是我无力承担的。
而我,也渐渐学会对身边的朋友更好,不无谓地索取。只是那个让我有最多亏欠的人,却在人海中再也不见。
——侯思铭
投票截止时间为11月29日中午12点
人间theLivings
网易非虚构写作平台
只为真的好故事
活 | 在 | 尘 | 世 | 看 | 见 | 人 | 间
微信号:thelivings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回复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窥探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马场的暗夜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外孙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女神 | 农民 | 非洲 | 何黛 | 切尔诺贝利
毕节 | 反诗 | 木匠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最后的游牧
行脚僧 | 北京地铁 | 高山下的花环 | “下只角”的哀怨
华莱士 | 创业领袖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褚时健 | 十年浩劫 | 张海超托孤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口水军团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更多“人间”文章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爱华网www.aIhUaU.com网友整理上传,为您提供最全的知识大全,期待您的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