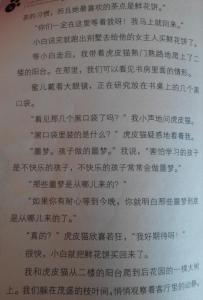柯云路爱情心理小说
《爱人》
连载(3)
成年人常常忽略小孩的性意识,他们不会想到,八岁的小男孩和二十岁的年轻女老师同居一室、同睡一张大床时,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
茅弟知道,对两年故事的追叙不能光停留在床上,那很容易引起读者误解,似乎小男孩的生命史都在朦胧而炽热的情欲中。茅弟也十分清楚,性的萌动确实是小男孩生命史中重要的内容,当他作为受精卵隐蔽出现在世界上时,已经具有了以后的全部性特征,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宇宙,受精卵就是宇宙初始的状态;然而,性并非是小男孩生命史的全部内容。
他和白兰老师两年的共同生活自然有更便于公开叙说的故事。
因为是他的老师,又因为同居一室像他的家长,白兰老师对他的学习与成长表现出双倍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和茅弟小男孩的小野心结合在一起,使得茅弟成为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在白兰老师的鼓励下,小男孩的野心又表现为帮助同学,在课外学习小组中茅弟成为小组长,辅导班里几个学习一般和较差的同学,做了一个小小的英雄。
在那个年代,英雄像最光荣的植物生长在田野上,英雄的故事像泡沫一样堆积在人们身边。小女孩崇拜英雄,小男孩渴望做英雄,田野上每一株植物都异想天开地争夺阳光特别的照耀。
小男孩的野心很茁壮地成长起来。茅弟是敏感的,聪明的,沉默寡言的,又是有心思的,他像一头勇敢的大田鼠,在四通八达的地洞里构造自己英雄的理想。

瞒着爷爷奶奶,瞒着白兰老师,也瞒着整个成年人世界,他开始做一件自认为了不起的事情。他联络了一些同班同学成立了反特小分队,主要成员是他那个学习小组的,外加了几个男女同学。课外学习完了,他们跑到茅弟家院子后面的大池塘周围秘密活动。他们选了反特小分队队长,自然是茅弟,又选了两个副队长,都是女生。
反特小分队开始了每天的战斗行动。他们渴望抓住一个或更多的反革命特务,然后他们就会成为英雄人物登上报纸,戴上光荣的大红花。
每天上学时,他们注意着小镇街道上的行人,看有没有鬼鬼祟祟的嘴脸。特别是起雾的早晨,他们认定是特务出没的时候,眼睛瞪得格外大,满街模糊的人影都十分可疑。有人在雾中东张西望,他们就警觉了;有人一边走路一边交头接耳,他们就发现了敌情;有人在街上相互交换手中的物件,他们更认定是特务活动,倘若有两个以上的小分队成员在一起,他们就会兵分两路分别跟踪一个人。大雾浓密得几步不见人影,他们分别失去目标,又汇拢来交换情况,然后才匆匆赶往学校。
反特小分队的成员开始有人迟到,白兰老师在课堂上对迟到的同学提出批评,他们缄默地坐在座位上,偶尔隔着满教室的同学相互看一眼,表明他们神圣的同盟。
下午放学后,完成了作业的小分队成员照例聚在池塘边的大树下开会,七八个人煞有介事地交换一天来的敌情。有人说,小镇上卖豆腐的老头像特务,有人说,小镇上打铁的瘸子像特务,还有人说,唐桥镇小学看大门的孙老头像特务,也有人说,茅弟家院子里每天仰着脸泼皮耍赖的白脸婆像特务。这种讨论当然从来没有结果,茅弟这反特小分队队长却在每日编织着他的英雄梦。
终于有一天,这个英雄梦受到打击。
他们坐在池塘边开会,开着开着就抓起池塘边的螃蟹,池塘岸边临近水面的黑泥中布满了乒乓球大小的孔洞,每个洞口都有螃蟹爬进爬出。当他们将抓特务的热情转到抓螃蟹时,立刻有了收获,大大小小的螃蟹被他们捉住,扔到茅弟跑回家拿来的脸盆中,听见它们在脸盆中吱吱哇哇地爬行。脸盆被螃蟹爬满,伸向池塘中心供担水洗衣服的小木桥却被他们拥挤踩翻,一半人掉了下去,另一半人高声呼叫。
大人们跑来了,将他们从满身污泥地拉了出来。
一贯疼爱孙子的爷爷瞪着眼,拿起藤条抽打茅弟的屁股,骂道:“你不想活了?”白兰老师回来了,挡住气怒不已的爷爷,将泥水淋淋的茅弟领回房间,听到爷爷还在过厅里叫骂,白兰老师轻轻掩住门,在脸盆里舀上清水,加上热水,让茅弟好好洗。
茅弟看了看白兰老师,白兰老师坐在写字台前说道:“你洗吧,我不看你。”茅弟脱下湿上衣,拧着毛巾洗脸洗胳膊洗上身。大概是从声音听出他洗得不得劲,白兰老师扭头看了他一眼,走过来说:“你怎么不好好洗?”她拿过茅弟手中的毛巾,挂在脸盆架上:“你的毛巾太小了,洗不好。”然后拿起自己肥大一些的毛巾,在脸盆里搓了拧干,捉住茅弟的肩膀给他擦洗脊背,又拧了一把,给他擦洗前后脖子和胸脯。
茅弟觉出了自己胸脯的瘦削,他闭着眼又羞愧又温暖地承受着自天而降的洗浴。
白兰老师又劈头盖脑地把他的头和脸擦洗完毕,搓了毛巾,倒了脏水,再换了干净水,将毛巾放到脸盆中说道:“这条毛巾就送你了,我还有毛巾,你自己接着洗下半身吧。”看到茅弟犹豫不决地站在脸盆前,她拿起一摞学生作业本:“我去过厅,你洗吧。”她说着拉门出去了,听见她和爷爷奶奶说着话。
茅弟迅速脱了裤子,擦洗完毕,换上干净衣裳。
第二天,白兰老师从落水的同学中问出了反特小分队的情况。放学后她把小分队的成员都留下了,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告诉他们做游戏是可以的,影响学习是不应该的,尤其不该做有危险的事情。她要求小分队从此解散,并要求茅弟写一个检查,要当着全班同学宣读。
白兰老师的神情十分严肃,茅弟老老实实将检查写好了,晚上临睡前交给了白兰老师。白兰老师在台灯光下看了又看,圈出几个错别字,转过头对茅弟说:“你再抄一遍,自己保留着,在班上就不用念了。”
追叙的事情就到此为止,茅弟又和读者一起回到故事发生的第一个夜晚。
茅弟认为,小男孩这个夜晚的经历十分重要,小男孩在这个夜晚的种种心理活动,包含着成年男人常有的全部心理特征。他甚至想到《爱人》可以换一个副标题,叫做一个男孩的情爱与野心。
读者也许会想到不爱江山爱美人、不爱美人爱江山的类似说法,茅弟并不希望自己的描述与分析有什么着意,只是希望放平心态,在尽可能无意识的境界中唤醒几十年前的全部体验。
他和读者共同回到了台灯照亮的房间里。
茅弟这才意识到需要向读者交代,南方夏日大床上张着蚊帐,小男孩是在蚊帐中面对着在台灯光照射下熟睡的女人。
台灯本来就压低了头,又经过蚊帐的过滤,自然比较朦胧,然而对于茅弟来讲,这却是破天荒的,他第一次在灯光下面对熟睡的白兰老师。仰卧的白兰老师发出鼾声,那鼾声比平日劳累得多。他侧身一动不动看了一会儿,又坐起来,背靠着墙抱着双膝,像条蹲在地上的狗一样看守着熟睡的女人。
茅弟写到这里,发现灯光的照明及白兰老师的遭遇很显然地改变了小男孩与女老师之间的关系。小男孩失去了往日在美丽的女老师身边睡卧的温暖与冲动,多少有些安静地打量着女人,然后就把下巴枕在膝上想入非非。那大多又是茫无目的的想入非非。也许在那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大一点的男人,也许他什么也没意识到。
茅弟眯眼凝视着几十年前的画面,细心地回想着。
小男孩在盲目的想入非非中看到一串景象:白兰老师在课堂上束手无策地问着同学:“老师没说错吧”;白兰老师站在大雨倾注的木桥中央茫然地看着同学们四散远去;白兰老师在黑夜的小镇上小心谨慎地推开一家家房门。这一连串景象模糊带来的感觉是,白兰老师需要他的保护;当然,对于七八岁的小男孩,这是他并不能自省到的朦胧感觉。
在他眼前浮现的另一个画面是,讨厌的刘文俊晃着红头鼻子与白兰老师隔窗说话,他们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很清楚。他想到他和同学们成立过的反特小分队,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刘文俊应该是反革命特务。
茅弟写到这里,除了体验到小男孩对刘文俊的敌视以外,对小男孩其余的心理活动都有似是而非的感觉。他能够明确回忆起的是,小茅弟又用比较长久的时间看着灯光下熟睡的白兰老师,这是他两年来最从容端详这个女人的时刻。
她的脸白净漂亮,上身穿着一件白色汗衫,夏日的被单被她自己从熟睡中掀到一边,整个胸部在白汗衫下干干净净地隆起着,灯光的斜射使得他可以透过薄薄的白汗衫看见乳头和乳晕的深色。下身是一条白短裤,露着两条光润的大腿,她的双手搭在肚皮上。茅弟写到这里,知道那时的小男孩远不足以概括自己的感觉:白兰老师当时的样子颇有任人宰割的驯良,供小男孩任意端详已是这种驯良的一个注释。
茅弟又能明确回忆起来的是,小男孩觉出了自己的尿意,他要越过女人的身体下床去。
在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对他下床的动作看得比较清楚:他是将一手一脚同时伸过去,越过女人的身体落在床上,然后再抬起这边的一手一脚。在跨越女人身体的过程中一旦滑倒,就必然整个趴在女人身上,这个曾经有过的失误我们前边已经做了叙述。这一次因为有灯光,又有一点从容,他自然是顺利地跨越了过去,顺利地掀开蚊帐下了床,趿拉着鞋来到墙角,掀开痰盂盖开始撒尿。
也可能知道白兰老师已经熟睡,前半泡尿撒得比较大方;也可能又想到了刘文俊的红头鼻子与反特小分队,后半泡尿撒得小心翼翼起来,时收时放地沿着痰盂壁尿着,消失了坦率的声响。
接着,小男孩蹑手蹑脚走到贴窗而放的写字台前,他记得白兰老师临睡前曾经很长久地坐在这里写着什么,他在台灯下看到几张白纸,上面写满了一行行字,第一行就是那句说错的话:“谁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在这句话的后面,像批改作业一样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再下面一行行钢笔字都是那句正确的口号:“谁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每个口号后面,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对钩。一页一页翻下去,写满了画对钩的这句口号。
茅弟不禁想到白兰老师经常让同学们这样做,对于那些屡犯的语文算术错误,她都会让同学们写一遍错误,自己画上×,再一连写十遍二十遍正确的答案,自己画上钩。
茅弟又想到了刚才白兰老师站在这里与刘文俊隔窗谈话,也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反特小分队,他像侦察员一样翻看了写字台上堆放的其他东西,那不过是同学们的作业本。在一摞作业本下他看到白兰老师的日记本,他知道她每天晚上有记日记的习惯,今天有了侦察一下的欲望。
然而,他警惕地听到窗外有轻幽的脚步声,屋里亮外面暗,纱窗在台灯光下发着灰亮的光,他看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他立刻关了台灯,雨已经小多了,现在是屋里黑院子里亮,他看到一个黑黑的人影站在窗外的屋檐下。隔着斜对面窗户朦胧的灯影,他看出这黑色的人影很像尖下巴的白脸婆,她一定是想到窗前窥探什么,屋里灯一灭,只好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溜走。
茅弟在黑暗中眯着眼想了想,又想到了自己的反特小分队,他悄悄打开纱窗,院子里的景象看得更清楚了,四面的房子和围墙很黑地围着一方积水的院子,斜对面那扇昏黄的灯窗映出的光亮照得院中的积水微微反光,一扇门开开又关上了,那个黑影就消失在那扇房门里。
茅弟确认了自己的判断,关上纱窗,在黑暗中回到床边,掀开蚊帐。
刚才是在光明中跨过白兰老师的身体,现在则在黑暗中跨过白兰老师的身体,这两种跨越完全不同。黑暗模糊了灯光照亮的一切,朦胧中觉出身体下女人的温暖,他像每次夜晚跨越一样,有了克制不住的冲动。他像一朵白云浮在上升的热气流上,白兰老师关于云为什么浮在空中的讲解使他有了这种联想。
他在自己的床位上躺下了,黑暗中睁着眼安安静静地想着什么。
茅弟写到这里能够做出的结论是,小男孩此时的感受既和刚才灯光下俯瞰白兰老师不一样,也和过去黑暗中躺在白兰老师身边不一样,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
他躺在那里,编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个故事,刘文俊和白兰老师都是反革命特务,他把他们侦察出来,抓住了,他成了戴红花登报纸的少年英雄。这个故事的情节颇为惊险曲折,作为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刘文俊是反革命特务,他要拉拢白兰老师,茅弟帮助白兰老师识破了反革命特务分子,最后茅弟成了少年英雄。
另一个故事就和反特小分队无关了,和少年英雄也无关了。在这个故事里,白兰老师还是最干净明亮的人,还是他每日最依恋的人,他要帮助她渡过难关。这个故事很朦胧,很凌乱。
当薄弱的睡意有些朦胧地袭来时,他从做少年英雄和不做少年英雄两种遐想中稍稍脱身出来,在若有所思的状态中又将头滑下枕头,将脸轻轻贴在了白兰老师光润温暖的手臂上。这个动作比以往的夜晚做得从容,也比以往的夜晚做得生疏,他的双手又轻轻抓住了这只手臂。
茅弟写到这里,知道当时的小男孩正处在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中:这是一个他最依恋的女人,他怕失去她;这又是一个经常保护她的女人,他更依恋她;这又是一个现在十分难过的女人,需要他的保护;这又是一个糊涂的女人,还在受刘文俊那样的坏男人的欺负;这又可能是反革命的女人,他要抓住她,当少年英雄。这种种分析叠加在一起,也不能真正道出小男孩那时的心理感觉。
我们只知道他在半从容半生疏的依贴中,渐渐复苏起一个男孩的欲望。
他用脸和嘴唇轻轻摩挲着这只手臂,而后闻着女人腋下发出的好闻气息,一只手又像蟒蛇的头一样沿着手臂向上摸过去,钻入宽大的背心短袖,轻轻摸在女人的乳房上。这一次抚摸远不像过去那样紧张激动小心翼翼,不仅多一点从容多一点生疏,还多一点其他的意味,而这又和这个女人今天的困难遭遇有关。
我们可以说这是小男孩对母亲一样的女人的惟恐失去的依恋,也可以说他有保护他所依恋的女人的男人的责任心,然而这些说法都有点似是而非。
茅弟写到这里不得不承认,小男孩这一次对女人身体的触摸有种邪恶的成分,倘若这事发生在成年男人的身上,其实很有些乘女人之危的意思。小男孩就这样脸贴着女人的手臂,若有所思地慢慢抚摸着女人的乳房;令人惊愕的是,他在这长久的触摸中,始终没有往日那种害怕白兰老师惊醒的小心和紧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