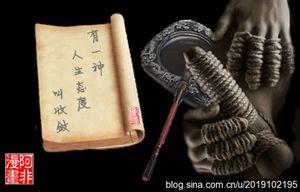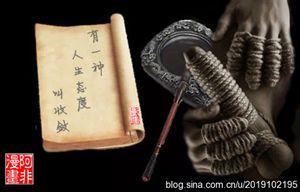現代聖人梁漱溟
(1893—1988)
一、出世入世間 秉性自浩然
梁漱溟,名煥鼎。始字壽銘,後又取字肖吾、漱溟,並以漱溟行於世。1893年 10月18日(清光緒<?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十九年九月九日)生於北京一個世宦之家。祖籍廣西桂林。遠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帖木耳”,旅居河南汝陽,明朝建立後,因所居為戰國時梁地,故改漢姓梁。自其曾祖梁寶書時遷居北京,曾祖、祖父均為清朝知州,這種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的輾轉遷徙,使梁氏家族兼具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與氣質,即既有北方人的豪邁、爽朗、尚俠、仗義,又有南方人的飄逸、灑脫、精明、幹練。這在梁漱溟及其父親身上表現尤為明顯。
他的父親梁濟,字巨川,40歲時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曾任清內閣侍讀,官至四品。據梁氏後來回憶說,他父親雖非天資絕高之人,但秉性篤實、豪邁、精明,意趣超俗而又滿腔熱忱,一身俠骨。凡事以“認真”、“務實”一為本。他身當中國大地風雲激蕩的年代,痛感外侮日烈,國勢日衰,而力主事功之學。認為一切學問當以富國強邦為本,否則就是無用。基於這種功利主義思想,他痛斥八股、科舉之弊,而極力推崇維新派之變革主張。梁氏一生受其父親影響很大,他的早年教育就正反映了他父親的這種新思想。
梁漱溟的早年教育是與眾不同的。在“三綱五常”仍統罩著中國,“父為家君” 仍是中國家庭的最高戒律時,梁濟卻有意去培養父子間親切自然關係,注意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而梁濟給予梁漱溟的正式學校教育更顯出少有的開明與進步。在別家的孩子照例進私塾,囫圇吞棗于四書五經時,梁漱溟卻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學堂裏學習ABC和《地球韻言》等。課外讀物則是通俗易懂的《啟蒙畫報》和《京話日報》等,這對豐富他的知識,培養他洞察社會的能力很有幫助。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順天中學堂,開始了長達五年半的中學生活,現代著名學者張申府、湯用彤都是他這時的同學。學校所開科目除國文外,還有英文及數理化各科。在班上,梁的學習雖不算太好,但卻是一位肯獨立思考、富有個性的學生。他在自述中說:“回想我從讀小學起一直到現在,似乎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主動的,無論思想學問作事行為,都不是承受於人的。”(《朝話》)比如他在作文時,就從不落俗套,喜歡獨出心裁,做翻案文章。對此,有的老師非常討厭,一位姓王的國文先生就曾憤而寫下“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的批語;而有的老師則非常喜歡、倍加讚賞,一位姓范的國文老師就在驚歎之餘,寫下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讚語。
在中學時代,課堂講授遠不能滿足他那強烈的求知欲。於是,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課外閱讀上。他在中學時的課外讀物是得天獨厚的,這包括: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大冊和《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本,以及《國風報》、《民主報》等報紙。他對於這些難得的資料反復閱讀,寢饋其中達三四年。在這些資料中,梁啟超那淋漓曉暢、飽含激情的文風,深邃通徹的思想,有如一股清泉,滋潤著梁漱溟的心田。他在後來一篇紀念梁啟超的文章中寫道:“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啟發甚深之一人”,“至今想來,我還認為是我的莫大幸福。”而革命派那激進的主張和昂揚的鬥志,又如一股颶風震盪著梁漱溟那敏感的心靈。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學習條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認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對於人生與社會的獨特認識。他自己後來說,對人生問題的探究,使他成為了哲學家,而對社會問題(即中國問題)的探究,又使他成為社會活動家。其一生行事治學,皆是圍繞著這兩個問題來展開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學畢業,由於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便毅然放棄升學機會,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會京津支部的機關報《民國報》當記者。整日出入總統府、國務院、學校、團體與街頭巷尾,目睹風雲詭譎的政情。1913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梁因與國民黨政見不合,遂離開了報社。
同他父親一樣,梁漱溟開始亦傾向於立憲派,但不久即轉向革命派,並積極投身於革命運動之中。但是,辛亥革命並未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國家反而因軍閥割據混戰而變得一天比一天糟,這使熱心革命的梁漱溟極為失望,並引起了他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漸由一位熱心革命的青年轉變為一個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觀厭世,曾兩次企圖自殺。儘管他後來出佛入儒,結婚成家,但卻終生保持著茹素不葷的習慣。
1916年,袁世凱帝制失敗,梁漱溟也度過了自己的精神危機,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終於出佛入儒,選定儒學作為自己的哲學信仰。這種思想轉變最終在他任教北大期間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而得識于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聲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開始在北大系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歷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此書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獨到的見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到 1929年,此書即已印行八版,並被翻譯成12國文字。此書的出版,把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之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一種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哲學的產生。
1924年夏,梁漱溟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辭去北大教席,遠赴山東曹州中學試辦高中部,並想以此為基礎成立曲阜大學。但不到一年,他又懷著失望的心情回到北京,先客居清華園,編印其父遺稿。後又與十多位從山東追隨而來的學生在什刹海共住共讀,互相敬勉。在這段時間裏,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學方式——朝會。他後來回憶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臺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刹那,抑揚朝氣,錘煉心志。朝會制度從此開始,以後他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時仍堅持不懈,後來還將朝會所講輯成《朝話》一書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濟深(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廣東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籌辦鄉治講習所,並任省立一中校長。在這裏,他首次明確地提出並闡述了自己的鄉治理論,主張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簡而言之,就是“以農立國”。1930年1月,由他參與籌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開學,梁擔任教務主任並主講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是年暑假,又應邀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問題之解決》的講演。闡述他的“村治主義”。他明確指出: “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鄉村運動的實質就是一場文化復興運動。
1931年,因蔣馮間中原大戰。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同年1月,受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之邀,梁漱溟帶領部分同仁赴山東籌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並以此為中心,以鄒平縣(後增至14縣)為基地,廣泛地展開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主張以“鄉學” 代替區公所,以“村學”代替鄉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實際上,所謂“鄉村建設”就是他的新孔學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貫徹。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種近乎傳教士般的自我犧牲精神,與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東鄒平度過了25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期間,他還先後寫作並出版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鄉村建設文集》(1934)、《鄉村建設大意》(1936)、《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鄉村建設的理論及其具體實踐方案。他試圖通過鄉村建設這一帶有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藉著創造根本的道德共識和精神凝聚,重整業已崩潰的鄉村社區,以達到復興中國固有的倫理社會結構,挽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落後狀況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的隆隆炮聲中斷了他那田園牧歌式的鄉建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的救亡呼聲,使他再也無法沉醉於他那塊藉以恢復“聖道”的樂土,而毅然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中,開始他長達十餘年的為國事奔走的傳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一文,提出抗戰“要實行系統化、民主化、國力化”的觀點,並提出了實行戰時教育制度改革的14條具體主張。8月14日,應蔣介石電邀,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共商國事。山東淪陷後,又親率山東鄉建院之學生兩百余人投入軍事委員會戰幹團第一團,在武昌軍訓後遂組成軍委會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開赴山東抗日。1938年 1月,梁漱溟又以“國防參議員”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訪問。他訪問延安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看共產黨轉變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領導人就實現國家進一步的統一交換意見。在三周時間的考察訪問中,延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裏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 尤其令梁漱溟難忘的是與毛澤東的八次長談(其中兩次竟是通宵!)內容廣泛涉及中國的現實命運與前途及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談話氣氛極為和諧、融洽,最後雖未達成完全共識,卻堅定了梁氏抗戰的信心,加深了對中共的瞭解,相信中國共產黨反對內戰、主張聯合抗日是堅決而真誠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與著名軍事家蔣百里一起巡曆華北華東各山地,長達八月之久。途中歷經千辛萬苦,曾幾次與日寇遭遇,險遭不測。在這次考察中,他痛感國共摩擦嚴重,深為統一戰線內部隱藏的危機而憂慮,尤其是1941 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形勢更加嚴峻,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1年3月1 9日,以梁漱溟、張瀾、黃炎培等人為首,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之前身),旨在聯合各民主力量,促進國共合作與團結,黃炎培被推為主席,梁漱溟作為發起人,既是13位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也是5個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 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難,衝破國民黨設置的各種關卡,隻身一人遠赴香港,在朋友的幫助下,創辦了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公開發表了同盟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宣傳同盟之政治主張。此事令國民黨大為惱火,對梁極盡百般刁難、威脅、利誘,但梁始終不為所動。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光明報》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歷經艱險,經澳門返回桂林。
抗戰勝利後,梁漱溟二訪延安,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希望維持國內和平。19 46年,他出任民盟秘書長,參加舊政協,並擔負起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調停人之重任。儘管他多方奔走,盡心竭力,卻因國民黨多次背信棄義,屢起事端而終未能扭轉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無望,回天乏術,遂在1946年10月力辭民盟秘書長一職,並公開宣佈退出民盟,離開政治舞臺,並申明從此以後對國“只言論,不行動”。梁漱溟於11月6日離開南京,來到重慶,在他創辦的勉仁書院,一面講學授業,一面撰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冀以我對於老中國之認識,求教於世。”1949年6月,此書寫成並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面對這個歷史巨變,梁氏並未感到不安。他自認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盡過力的炎黃子孫,一生所行,問心無愧。為此,當有人力勸其遠赴香港時,他堅決拒絕,執意留在了大陸。
新中國並未忘記梁漱溟這位愛國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周恩來還在天安門城樓上,頗有感慨地對各界朋友說:“今天梁漱溟先生沒有來,很遺憾!”毛澤東亦有同感,並指示有關部門務必儘快把梁漱溟請到北京,共商建國大計。

1950年1月,梁應中國共產黨之邀,離渝赴京,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但他對毛澤東邀請他參加新政府一事,卻以“如參加政府就不便說話”為由,敬辭不受。後接受周恩來之建議,從4月到9月,梁漱溟到華北、華東、東北等地參觀,深感新中國氣象萬新,遂漸改初衷,表示願與共產黨共事。1951年,梁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
梁漱溟作事極為認真,秉性剛直,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是黨和政府難得的諍友。 1953年9月16日,梁以政協委員資格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會議,會議主旨是討論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梁漱溟聯繫自己的所見所聞,就“總路線”中過分突出重工業而忽視農業、輕工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並針對當時社會上已相當明顯的“工農差別”,提醒共產黨不要“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而應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但遺憾的是,梁漱溟的耿耿直言,卻招致眾口批判,毛澤東更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公開發表,從而把梁漱溟推入了一場以他為主角的批判運動大潮中。各種批判文章和專著接踵而出,鋪天蓋地而來,步步升級,並無限地“上綱上線”。這是梁漱溟始料所不及的。但他對這些批判心不悅,口亦不眼,並以沉默作為回答!
1966年,中國大地開演了一場曠古絕後的大悲劇!在這場大悲劇中,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再次罹難。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畫和手稿被燒個精光;連衰朽之軀也倍受折磨、白天拉出去遊街、批鬥不說,晚上還被鎖在一間小屋裏,勒令寫“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身錮陋室,面對一疊白紙,思潮起伏,感慨萬千!但縈繞他腦際的卻始終是這樣的信念:“書籍燒了,但思想是銷毀不了的!”正是憑著這一信念,從1966年9月21日開始,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其淵博的學識和驚人的記憶,用寫“交代”的紙、筆,偷偷地撰寫《儒佛異同論》,歷時月余,全文四萬餘字。接著又馬不停蹄地撰寫《東方學術概觀》。 1986年,巴蜀書社終於將這兩部著作合而為一,正式出版。
1973年10月4日,是夏曆重陽節,梁漱溟剛在家中寂寥地度過他的80壽辰。中國大地又狂飆突起。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懷著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批林批孔”的運動。梁漱溟對此深不以為然,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只能 “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協、民主黨派的學習會上。他雖每會必到,卻只洗耳恭聽,緘口不言。一他不願隨流而進,講違心話。然而,樹欲靜卻風不止,沉重的政治壓迫和某些與會者的軟硬兼施。逼得他非開口不可。君子坦蕩蕩,言則言矣,何懼之有!他明確表示:“我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持保留態度!”並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歲之高齡,手拿皮包,身穿長袍,衣冠整潔儀態莊嚴地站在政協會議室的講臺上,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授課那樣,以《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為題,繪聲繪色地講了兩個半天,為孔子辯護。並在最後公開宣稱:“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這番“反動”言論的直接後果,是招致了長達七個月的“批梁運動”,他再次成為運動的“主角”。但他唯一的反抗武器是:沉默!直到9月23日,在專門針對他召開的一次總結性批判大會上,在主持人的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長時期的沉默,將滿腔義憤與堅定信念融鑄在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中:“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此言一去,即令在座諸人瞠目結舌,茫然失措。
1976年,隨著“四人幫”的垮臺,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和全國人民一樣,梁漱溟為祖國春天的到來而歡欣鼓舞,但他考慮更多的卻是中國未來的建設與發展。1980年,他在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的同時,又被選為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致力於使國家走上法制建設的道路。80年代初,他還以90高齡,擔任了全國最大的民間學術機構中國文化書院主席,並重登講壇,發海潮之餘音。以其大哲之哲,啟後學之思。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梁漱溟雖在耄耋之年,依然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人心與人生》、《我的努力與反省》、《東方學術概觀》、《憶往談舊錄》等著作。尤其是1984年自費出版的《人心與人生》,歷時半個世紀始才完成。它是繼《中國文化要義》之後,總結其一生思想的結晶之作。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梁漱溟在為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殫精竭慮,勞攘奔波近一個世紀之後,終於感到累了,該休息了。1988年6月23日淩晨,這位愛國老人平靜而安詳地告別了這個喧鬧紛攘的世界!
二、探人生真諦 究東西文化
梁漱溟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而真正萃集其思想精華的主要是以下五部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和《人心與人生》。這五本書並非單純的學術著作,而是他面對其當下直接的問題(即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由煩悶而苦索,進而提出答案並付諸實踐的一個完整的過程。
對於梁漱溟一生而言,其思想雖迭有修正,但其思想之根抵與理論架構則奠立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此書是他的文化哲學與其人生哲學、歷史哲學交織融鑄而成的一座思想豐碑。它的出版,標誌著梁氏哲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建立。在此書中,他首次提出並闡述了他的人生哲學、文化哲學、歷史哲學和解決中國文化危機的紙上方案。在這一博大而龐雜的體系中,建基於本體論之上的人生哲學是其文化哲學的理論基石和邏輯起點,文化哲學是人生哲學的邏輯推論,而歷史哲學則貫穿於其對東西文化的具體闡釋過程中,體現著他本人對文化歷史發展的根本看法。三者互相涵攝、相互交融,構成了梁漱溟哲學思想的有機整體。
在梁漱溟的早期思想中,以“生活”(或“生命”)、“意欲”為中心範疇的宇宙論,構成了梁氏哲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他從西方非理性主義哲學(主要是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中得到啟發,先驗地設定了一個具有本體意義的概念“意欲”作為其一切理論的根基。他認為,所謂宇宙就是“生活”,而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那“沒盡的意欲”。意欲乃世界萬物產生的本原,意欲的發用流行即形成“生命之流”,而宇宙就是這“生命之流”所形成的一個大生命。在他看來,宇宙並非一靜態的固定體,而是一個“動態的相續”,是一超越物質的精神存在,其本質特徵就是純粹的變化。而要認識這變動不居的宇宙,就必須首先認識作為萬物之原的“意欲”。但如何才能認識這個作為本體存在的“意欲”呢?只有通過非理性的直覺體悟。為此,他引入了柏格森的直覺主義認識論。並把它同佛家唯識理論探合起來。他認為,人類認識世界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理智的方法,一是直覺的方法。前者是一種純粹“靜觀”的方法,猶如在活動的電影中截取其中的一張膠片,它無法獲得運動實體的本質,而只能認識那靜止的物質世界,而只有直覺才能勘知那永恆流轉的宇宙本體。他說:“直黨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種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圓滿具足,無少無缺。”顯然,梁氏的這種直覺認識方法乃是一種超越實踐、超越感性乃至理性思維的一種內心體驗,表現為一種神秘的頓悟和飛躍。
正是基於這種“意欲”生成萬物的宇宙論和直覺主義認識論,梁氏建構了他的文化哲學。
梁氏對文化的界定是以他的“意欲”說為基礎。他認為,所謂文化,“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而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在他看來,人類各民族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樣法(或生活態度),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作為各民族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內在驅力的基礎“意欲” 有著截然不同的趨向之故。為此,他通過一直覺體悟的認知方法論定,儘管各民族的基礎意欲各有所向,千姿百態,但歸納言之,總不外以下三種路向,即“(一)向前面要求;(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他認為,人生意欲的這三個面向,正代表了人類三種迥然不同的人生態度,即:奮鬥欲求的態度、調和持中的態度和反身向後的禁欲態度。在他看來,這三種人生態度各自最充分地體現在西洋民族、中國民族和印度民族身上,並分別代表著三方文化的內在精神。三大民族正是各自秉持著自己文化的內在精神向前走去,遂成就了世界上三種不同類型、風格迥異的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而這三大文化系統正標誌著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截然不同而又次第演進的三大路向。“質而言之,我觀察的中國是走第二條路向;印度人是走第三路向”;而“西洋人則走的是第一條路向。”而這三大路向也代表著人類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
這就是梁氏獨特的文化類型理論,也是他的文化哲學的核心和理論基礎。他對人類文化的總體考察就是以此為邏輯起點來展開的。根據這一理論,梁氏又從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和道德哲學等方面對東西文化之差異作了全方位的比較,辨析。得出結論:西方文化自古相傳的是以理智型為主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西洋人處處追求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道德哲學;而中國文化自古相傳的是直覺型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不計物質利益”的超功利主義價值觀和“尚情而無我”的道德哲學。正是通過這種對東西文化哲學基礎差異的比較、辨析,基於其認知理論,梁氏提出了他的人類文化將三期次第重現的文化發展觀和中國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復興於世的大膽論斷。
他認為,不同類型文化的發展不是平列的、共時態的,而是歷時態的,有先後次序的,即:西洋文化:第一路向,第一期文化一中國文化:第二路向,第二期文化一印度文化:第三路向,第三期文化。這種文化演進的次序特徵決定了西中印三方文化在人類歷史上的時代地位。他認為,西洋文化是按順序發展的,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因“古初的天才太聰明了”,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便中途拐彎”,過早地走到第二和第三路向上去,“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而顯得“很不合時宜”。但他認為,中國文化雖然以前不合時宜,而“此刻卻機運到來”;因為走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發展到今天已出現了自身無法解決的嚴重危機,必須求助於走第二路向的中國文化。他因此斷言:在不遠的將來,第二條路向會被重新拿出來走,“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便是梁氏的結論——一個先知式的預言!
正是基於這一信念,梁氏進一步指出,處於轉折的關鍵時期的中國人,為迎接中國文化重光於世,應該做到:“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地把中國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而重點又在於第三條,這“中國原來的態度”就是孔子的人生態度,明白地說,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人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那只有如我現在所說可以當得起!”[注]
這,便是梁氏為中國文化開出的救治良方!
梁氏的這一套以先驗存在的“意欲”作為邏輯前提,並以一直覺體悟的認知方式將“意欲”的發用流行規範成三個方向。從而形成人生的三大路向及三種人生態度,繼而相應地形成三大文化體系的致思理路,其邏輯的不周延和簡單化是顯而易見的。他試圖以一簡約的概念去涵蓋那極為複雜而多樣化的歷史與文化,雖然能給人以宏觀清晰的印象,但卻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弊。但是,不管梁氏的文化理論是多麼的簡約與主觀片面,其中理論上’的貢獻卻是無法否認的:他徹底打破了以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文化一無論者的迷夢,並使國人眼界大開。而他從全新的理論視角對儒家傳統文化所賦予的深刻意涵,又使當時的任何一派文化論者都大為遜色,這種融深邃睿智與強烈主觀情感于一體的文化理論,打破了當時“徹底否定”與 “徹底保留”的雙重迷障,從而將中西文化的論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就梁氏一生為學而言,他並非為哲學而研究哲學。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的文化哲學的真正目的乃在於保存中國的文化本質,或更確切地說,保存儒家的倫理價值,並嘗試著去開創真真正正的中國文化復興之道。正如美國學者艾愷所說: “他將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不安,投射到中國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對人類的普遍性關懷結合到特殊的中國處境的當下問題上。”他和梁啟超、張君勱等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樣,“在實證論所隱含的決定論之外,共同致力於保存倫理道德,並且努力從傳統的外觀下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意義。”
梁漱溟和他之後的新儒家學者一樣,其終極關切是探求“意義”(這裏所謂探求意義乃指探求宇宙、人生的基本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探求過程中,他將自己置於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流中,並將自己同文化視為一體。因此,他在追問、探求自身的存在意義,同時也是追問、探求中國文化的意義。他探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同時也就是探求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的一生中,其終極關切的核心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何在?她在整個人類文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她未來的前途又如何?就在這一價值(或意義)的追問、探求過程中,一個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一生之使命的“現代聖人” 就應運而生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