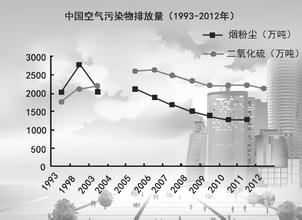海祭活动,罹难者家属在船上追思亲人
未停止的追寻
《太平轮1949》不仅是一本书,它像一道光,点燃了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最喜悦的过程就是在寻找过程中,好像串起来1949年很多的两岸的离散,同时也是华人共同的记忆,因为后来很多人就漂泊到全世界了。”在书的出版和海祭活动后,一个又一个的惊喜扑面而来。
第一个惊喜是又一位幸存者的发现,而且还是其中一位股东的女儿——张典婉告诉本刊记者,不过因为她还没有做好面对媒体的准备,姑且以“周老师”称呼。
“我和她谈了两个多小时,她讲了被救起来的细节,她的表哥、表妹当时都在船上,她的表妹当时也被救了起来,但是在医院里过世了。周老师本人被家里人安排到熟人开的医院里静养,治疗创伤。195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来校院调整并入北大,于是就在北大读书一直到毕业留校工作。”周老师的父亲周庆云是排名第六的船东,周庆云也因为“太平轮”的事情赔偿了两次,几乎倾家荡产。
“我的书出来之后,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据澳大利亚军舰记载,当时救起来四个女的,我在书里写了两个人物,加上这位北大教授和她过世的妹妹,正好就是四个人。澳大利亚的读者帮我在墨尔本找到一个当年救她们的澳大利亚军舰的水手,将来我们也希望请这些老水手回来做一些活动。”
另一个惊喜是在2011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读者见面会后。一位来自出版社的读者“飞奔”过来找到了张典婉,告之可以带她去见一位与“太平轮”有着重要关系的特殊人物——梅娘。
梅娘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当年有“南玲北梅”之誉。1949年以后,梅娘因在沦陷区创作的经历而被打为“汉奸”、“右派”,从此沉寂文坛。梅娘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不顾家庭反对,与柳龙光结为伴侣。
柳龙光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希望柳龙光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赴台湾动员伪“蒙疆政府”的参谋总长乌古廷率部起义。梅娘于是随柳龙光动身前往台湾。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事项的柳龙光不幸成为“太平轮”最后一班的乘客,遇难时年仅33岁……当时梅娘只有28岁,还怀有身孕。她后来在那边生活困顿,最后费尽周折地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大陆。

“当我知道梅娘后来隐姓埋名地活着,很长时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时,我又很难过,当年那么棒的一个作家,可是却一生困顿在两岸间游走,可以说她活着就是在见证历史。”2011年12月22日是梅娘生日,张典婉说,她专程带了束鲜花去看望梅娘。张典婉说,梅娘回到大陆后的境遇固然令人叹息,可是如若留在台湾又会怎样?“我觉得如果当时梅娘没回大陆,她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肯定也跑不了。”张典婉情不自禁联想起《台湾新生报》一位非常有名的女记者沈源璋,她当时恰好采访过“太平轮事件”及其幸存者。1966年,沈源璋与同为记者的丈夫姚勇来,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被逮捕,狱中受尽凌辱,不堪忍受而上吊自杀。
对张典婉来说,出版《太平轮1949》的另一个效应是,很多人找到她,希望她帮助找到1949年前后离散的亲人及其后人。所以,张典婉和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筹划着下一部作品,名字叫《寻人启事——我的爱》,专门讲述两岸在1949年离散的故事。张典婉和她的工作伙伴钻进图书馆和资料室,搜索到了台湾旧报纸上300多条寻人启事。她至今仍对这样一条印象犹深:“某某人夫,我已于民国三十八年几月几号辗转从青岛来台,父亲不堪旅途劳累已于半途病殁,带着大宝二宝三宝,目前孤苦无依,他人时来相欺,现已见报后到花莲某某地去寻。”这样一个小小的寻人启事里面诉说了多少欲哭无泪、愁肠百结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以前断裂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即便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其中筛选、查证、核实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困难重重,而且张典婉也知道,这300多寻人启事的主人,十之八九是找不到的,“但这个寻找的过程才是我们要记录的”。其工作伙伴谭端郑重地补充说:“如果要给这个事情扣一顶‘帽子’,那就是给这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的心灵做一次事后的安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