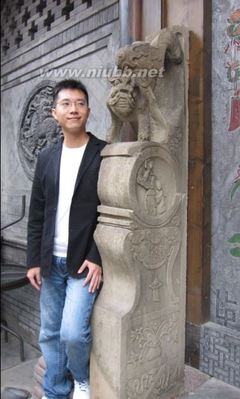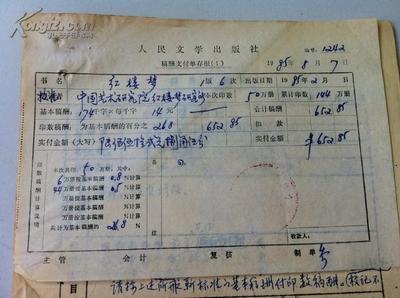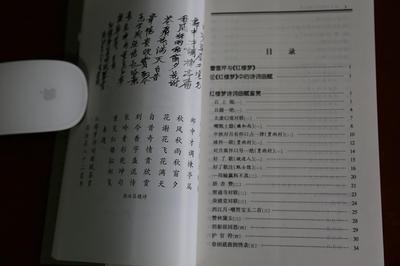聪明累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散 人亡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
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一场辛苦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名家点评:
这首曲是唱王熙凤的。
《聪明误》,是知进不知退,聪明反被聪明误之意。
凤姐是作者着力刻画、塑造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典型。她是荣府内实际上的第一号当权人物,各类人物都围绕着她活动着。对于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对她的看法。第六十五回里,贾琏的心腹小肠兴儿对着尤二姐议论凤姐说:“若提起我们奶奶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她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她。皆因她一时看的人都不及她,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人敢拦她。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她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她讨好儿。估着有好事,她就不等别人去说?她先抓尖儿;或有了不好事或她自己错了,她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她还在旁边拨火儿。”这些话是通过兴儿的嘴说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看法。她是封建阶级中最有才干,也是最贪得无磨的一个。在“弄权铁槛寺”一回里,她对老尼静虚说:“你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为了三千银子,她略施一点小手段,就害死了张金哥和长安守备的儿子。此外还有贾瑞、鲍二家的、尤二姐等人都先后死在她手里。兴儿还说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她是贾家这座大厦的顶梁柱,同时又是这座大厦的蛀虫;她照管着贾家的“长明灯”,又恨不得一口喝干灯里的油。、连她自己都承认“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实际上她一步也没退,当忽喇喇大厦倾倒时,第一个就要把她压死。脂砚斋批语透露,在贾家败落后,她要被关押在“狱神庙”,有一番“身微运蹇”、“回首惨痛”的经历,最后凄惨地死去。
留余庆
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
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
劝人生,济困扶穷。
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乘除加减, 上有苍穹。
名家点评:
这首曲是唱巧姐的。
《留余庆》的题名出自俗语“积善人家庆有余”;这句俗话又出自《易经·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意谓前人积德,后人沾惠。
巧姐在大观园十二钗中年龄最小,因她尚未长大成人,所以作者没有去刻画她的个性。她的命运取决于其母王熙凤。王熙凤英雄一世,最后惨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巧姐的命运就可以推知了。
刘姥姥在穷得过不去冬时,曾到贾府去求助。凤姐对这个“芥豆之微”的穷亲戚本来没看起,但在无意中也救济了她。曲中说的“积得阴功”,指的就是这件事。从此刘姥姥和贾家结下了缘分,先后三进荣国府,成为贾家兴衰的见证人。连巧姐的名字还是刘姥姥给起的,当时还恭维说:“她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随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从曲子内容看,在巧姐被其舅王仁等人推进火坑(很可能是卖给妓院)时,刘姥姥救她出来,使她“逢凶化吉”了。
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
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
只这带珠冠,披风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
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驾积儿孙。
气昂昂头戴管缨,光灿灿胸悬金印,
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
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
名家点评:
这首曲是唱李纨的。
《晚韶华》,意思是晚年要荣耀一番。
李纨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李守中为园子监祭酒(类似国立贵族子弟大学校长)。自幼其父就教她读《列女传》之类的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黛陶,成为一名典型的淑女。青春丧偶,她能安之若素,只知道孝敬公婆和抚养儿子,此外一概不闻不问。她果然就是“稿木死灰”吗?其实不然,她只不过是把苦痛和悲哀深深掩抑在内心里不流露罢了。这种无法渲泄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三十三回里,宝玉遭毒打,王夫人叫着贾珠的名字大哭: “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这话犹如一针扎在李纨心上,她禁不住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苦痛心情仅有的一次流露。
李纨苦了一辈子,尽管晚年母以子贵,还是抵消不了她的悲剧命运,接着就死了。作者以“气昂昂”、“光灿灿”、“威赫赫”之类的字眼形容贾兰升官,讽刺之意很明显,其实最多不过再来一次“苦枯”的小循环而已。
好事终
画梁春尽落香尘。
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
箕裘颓堕皆从敬。
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名家点评:
这首曲是唱秦可卿的。
《好事终》,指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丑事告一段落,曲名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
从曲子开头几句看,作者似乎是把贾家败落的责任归到秦可卿身上。其实细看书中情节,不过是通过秦可卿把宁府贾珍、贾蓉、贾敬等人牵出来,进行暴露和鞭苔。秦可卿的堕落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得而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贾珍都是主要责任者。秦可卿出身并不高贵,是其父秦业丛“养生堂”抱养的孤儿。贾珍这个无耻的酒色之徒垂涎其美,不顾伦理关系,勾引她堕落,导致她自杀,应该是合理的推测。由此再进一步,作者以为贾珍的堕落,责任又在其父贾敬。这个贾敬一心想当神仙,整年烧丹炼汞,“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完全放弃了家业和对子孙的教育。于是贾珍、贾蓉父子“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翻了过来”,也没人敢来管他们。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不败何待?
收尾-飞鸟各投林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
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名家点评:
这是《红楼梦曲》总收尾的曲子。
《飞鸟各投林》,是“家散人亡各奔腾”的另一种说法,与“树倒猢狲散”同义。
这首收尾的曲子是对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命运的概括,也可以说是一首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主题歌。
作者一生由“饮甘餍肥”的贵族子弟跌落成一个“举家食粥”的落拓文人。他看到封建社会处处充满矛盾斗争,一切都在运动,都在产生和消失。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印在作者头脑中,就形成了他朴素的辩证法观念。在第十三回中作者通过秦可卿之口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这就是说“物极必反”,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个客观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这首《飞鸟各投林》的曲子等于宣布:凡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拼命追求和维护的一切,都是注定要灭亡的。曹雪芹依据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忠实地描绘了大观园内外的社会生活,正像他自己宣称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蹬迹,不敢稍加穿凿”,因而《红楼梦》所反映的贵族家庭的兴衰始终,是符合历史的辩证法的。作者写他们的“极盛”,正是要反衬他们的“极衰”;写他们的“赫赫扬扬”,正是要反衬他们的“烟消火灭”。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写贾家最后又“沐天思”、“延世泽”、“兰桂齐芳”,安排一个不喜不悲的“团圆”结局,是违背曹雪芹原意的。曹雪芹设计的结局是“乐极悲生,人非物换”,“树倒猢狲散”。按照作者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荣国府并不永远“荣”,有荣必有枯,而且要枯得很惨;宁国府也不永远“宁”,有宁必有危,”终要有破家灭族的一天。从脂砚斋批语透露的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以后的部分情节看,贾家败落后,当年“金窗玉槛”、“珠宝乾坤”的大观园要变成“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一片凄凉颓败景象。被撵出大观园的宝玉和宝钗要有一段“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困苦生活;王熙风要有一个“身微远蹇”、“回首惨痛”的可悲下场;惜春要沿门托钵,“缁衣乞食”;贾赦、贾珍之流要被撤职罢官,扛上枷锁,或被杀头,或被流放充军。贾家如此,与他们有关联的其他史、王、薛三族也一样,得势时他们互相“扶持遮饰”,势败时也要一齐完蛋。他们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了去。这首《飞鸟各投林》的曲子,就是对他们下场的形象描绘。
曹雪芹毕竟是二百多年前封建贵族出身的一位作家,他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他出身的贵族阶级充满厌恶和愤慨,但又和这个阶级难解难分地联在一起;他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又不知道谁是历史的主人;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但又提不出超出封建主义范畴的政治思想。他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迁,但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如认为“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就是错误的“历史循环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曹雪芹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他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有一个论断,认为这首曲子是《红楼梦》全剧三大主线之一的“人散”。原文摘录如下:
……这第三条大线就是“人散”。人散虽与家亡相联,又自成体段,前文已经说过。秦可卿与风姐托梦的结语,说了两句七言诗——秦可卿也能诗!岂不甚奇?须知所谓“正邪两赋而来”之人,大抵皆属于诗人型.这是个专题,宜有专文讨论。如今只说可卿最后说道是:“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署名“梅溪”的,于此便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便欲堕泪。”可知这人散一线,是书中最后的一局——也就是结局,所以它独自构成一大经纬。
“三春去后诸芳尽”,有几层涵义。一即字面义;三春(孟、仲、季,即“九十春光”)过去了,百花凋谢.二是“三春”又指书中所叙三次重要的元宵佳节——第十八回省亲,第五十四回夜宴,与八十回后某回的一次元宵节(大约是巨变的发生)。三是“三春”又指贾氏姊妹,元、迎、探,特别是探春一去,方是人散的总溃之始。这两句诗总括地表述了大势.我们当然还是“欲知其详”。我以为这就要向雪芹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段曲文去参会——就是第五回《红楼梦曲子》正曲第末支,那首惊心动魄的《飞鸟各投林》: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单只这“飞鸟各投林”五个大字,已然道尽了“人散”的意味。这曲子笔大如椽,音调悲慨,总结了全书,我说是“结局”,全书的结局就是“人散’。大约不是我的一时的错觉吧!
这首极端重要的曲文,是探佚学和结构学的一把关键之启钥,纲领之提挈,把它研究透彻、的确了,将是“红学’的一大贡献。但就我个人来说,一时还未能做到。只有一些零碎的看法,姑且提供参考。
这首曲文应是每句暗切一入之?事。例如“有恩的,死里逃生”,是指巧姐,正谓“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者是矣。又如“欠泪的,泪已尽”,人人都能指为晴切黛玉。即此二例,其曲文体例确然可知,非我们穿凿可比。循此体例,就可以试作推寻了鄙意如下: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两句总括“家亡”
有恩的,死里逃生——巧姐
无情的,分明报应——宝钗、妙玉
欠命的,命已还——元春
欠泪的,泪已尽——黛玉
冤冤相报实非轻——迎春
分离聚合皆前定——探春、湘云
欲识命短问前生——凤姐
老来富贵也真侥幸——李纨
看破的,遁入空门——惜春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一秦可卿
以上十二句,本以为恰好分属十二钗,但首二句并非妇女之事,而脂批于此正有总括荣宁的语义(其实应是总括贾王史薛四门),那么可知此二句是先从“家亡”领起,以下才是每句分属。又由于只剩下了十句,而“分离、聚合”明明是两者的合词并詠,这又明白了还有一句应该也是合詠二人,于是我寻找这个可能性时,发现“看破的,遁入空门”也可能包括妙玉惜春二人而言。但细味其言,终以指惜春更为切合,盖妙玉之出家,固幼年多病,为父母所舍身,又因避权势仇家之难,方进京入园的,并非“看破”之故,因此我仍以本句只指惜春,而并妙姑于宝钗一起,理由全在不能忘记“报应”二字是眼目。宝钗属于“无情”,书中有明文点破(她抽的花名酒筹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是为力证。),这样是合榫的。
另需说明的则尚有元春、凤姐、迎春三人的分屑,以其容或招来争议,所以也是研讨的题目。我将凤姐隶于“命短”句下,理由也是书有明文暗示之处。元春原系死于非命,实因政治变故而致,受逼而亡(如书中暗示如杨贵妃),故为“欠命”。迎春为何隶于“冤冤相报”之下呢?这井非指此无辜少女本身,而是罪孽在她父亲贾赦,贾赦多行不良,贪货好色,害人性命,如姜亮夫教授所见旧抄本,贾氏之败实由贾赦之罪发而引起,他害了两条人命。我以为这两条命案皆是女子,其一即鸳鸯,说详后文。另一条女命当然也是因他好色图淫而致某女于死(疑是嫣红,说亦详后文)。所以冤冤相报是说他害人家的女儿,孙绍祖也害了他的女儿,是即曲文的本意。
以上的推断,不敢望条条妥贴,然而大局亦可概见。“人散”是“金陵十二钗”的主调与终曲。当然,“人散”的实际,所包远比十二钗丰富得多得多,举凡两府一园中的众少女,皆在此数,是全书一大收场关目。本节不及多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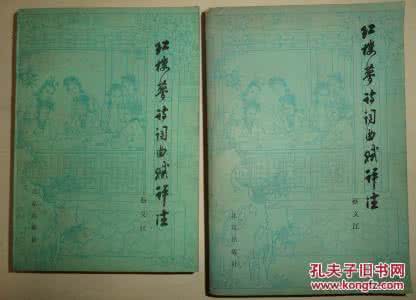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辩》中也有一段关于这首曲子的文字,摘录如下:
……“《十二钗曲》末折是总结;但宜注意的,是每句分结一人,不是泛指,不可不知。除掉‘好一似’以下两读是总结本折之词,以外恰恰十二句分配十二钗。我姑且列一表给你看看,你颇以为不谬否?(表之排列,依原文次序。)
为官的,家业凋零——湘云
富贵的,金银散尽——宝钗
有恩的,死里逃生——巧姐
无情的,分明报应——妙玉
欠命的,命已还——迎春
欠泪的,泪已尽——黛玉
冤冤相报实非轻——可卿
分离聚合皆前定——探春
欲识命短问前生——元春
老来富贵也真侥幸——李纨
看破的,遁入空门——惜春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凤姐
这个分配似乎也还确当。不过我很失望,因为我们很想知道宝钗和湘云底结局,但这里却给了她们不关痛痒这两句话,就算了事。但句句分指,文字却如此流利,真是不容易。我们平常读的时候总当他是一气呵成,那道这是‘百衲天衣’啊!”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嘲顽石诗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新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名家点评:
第八回写宝玉去探望宝钗,宝钗要看宝玉那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便笑着说:“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宝玉把玉解下来递给宝钗。就在此处,作者假托“后人曾有诗嘲云”写了这首诗。
女娲补天丢弃不用的那块石头,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人人世,变成了通灵宝玉,同时又是贾宝玉其人。这是作者凭空虚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所以说它荒唐而又荒唐。石头由自由自在的神物,变成一个被人百口诮谤的“臭皮囊”,表面上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其实是作者在发抒他对人生社会幻灭后的愤激情绪。“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是暗示宝钗、宝玉夫妇命运蹇涩,将由花柳繁花的顶峰,跌入贫困凄凉的底层。最后的“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两句显得很突兀,然而只有这样出入意料的有“分量”的句子才能把全诗结住。它告诉读者,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转眼即逝的过程,最终全告毁灭。书中这类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地方不少,毋庸讳言,其作用是消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要会读,会分析,作正确的弃取。
通灵宝玉与金锁铭文
通灵宝玉铭文: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金锁铭文: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名家点评:
这四句铭文分别铭刻在宝玉佩带的通灵玉和宝钗佩带的金锁之上,出现在第八回中。
这两句铭文恰好是对仗工整的一副联语,也是所谓“金玉良缘”的根据。从字面上看,这是两句好话,但用在“二宝”身上就带有明显的嘲讽意味。将来一个要出家当和尚,一个要守活寡,长寿又有什么用?说是“仙寿恒昌”,宝玉并没有成佛作主;说是“芳龄”永继,宝钗同样要衰老贫病。其实不过是表面吉利的两句空话而已。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赞会方园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
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
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
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
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
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
名家点评:
这段景物描写,在情节有它的反衬作用。王熙凤在观赏景致中,碰上了躲在假山后等她的贾端。接着作者就描写“毒设相思局”的丑事,对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糜烂、道德败坏作了无情的暴露。这些帏内幕后的丑恶与芳园的美好外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见,接天台之路,实际上只是通淫秽之径;涧流清溪,也只不过是臭水泥潭而已。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梦秦氏赠言
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名家点评:
秦可卿托梦赠言,预示着贾府“盛筵必散”。作者这样写是有深意的。小说写贾府中第一件对内外都有影响的大事是秦氏之死,而成为她致死的真正“病”因,即发生在宁国府的许多丑事(荣国府当然也如此),连家仆焦大都一清二楚了,要想瞒住旁人耳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秦氏丧生于丑事败露,贾府之败最终也就败在被敌对势力抓住把柄上。因此,作都特意让可以以自身教训为鉴的秦氏来提出必须对贾府将来的败亡早为后虑的警告。王熙凤掌握着贾府实权、作恶最多的人物,也是贾府的主要招祸者。让她来听秦氏这番话,用意思更为明显。就在听这个警告后没几天,她弄权铁槛寺,贪财害命,而且从此坏事干得更起劲了。这就显示了贾府之败的必然性,让我们从中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在腐化,在没落,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趋势。
王熙凤在梦中听秦氏念了这两句话后“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这描写是发人深醒的。为王熙凤和整个贾府叩云板、报丧音的下正是秦可卿吗?对于这样一个历时百年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作者及其亲友都是极为伤感的,一闻丧音,不免涕泪交流。比如小说的题名人之一,东鲁孔梅溪,他为了纪念曾替作者旧稿《风月宝鉴》作过序的作者亡弟棠村,仍给《石头记》新稿题上了这个旧名(见甲戌本第一回批)。可见他对作者家世十分了解,且有感情。他在这两句话上,就加批说:“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容易动感情的畸笏叟,当然更为之而“悲切感服”。他“感服”什么呢?就是秦氏为贾家后事作了周密的考虑。如在祖茔附近预先多置房产、田地,以备祭祀、供给,也为子孙将来留一条退路等等,总之都是为封建大家族长远利益打的算盘。他还因此原谅了秦氏生前的行为,嘱令曹雪芹把暴露她与公公贾珍之间丑事的“遗簪、更衣诸文”统统删去,以便将她从作者的“刀斧之笔”下“赦”出来。这些虽然只是批书人的立场观点,但从作者终于删改“淫丧天香楼”文字和描写这一段托梦的情节来看,对贾府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作者自己也同样是流露出悲惋心情的。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封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题大观园诸景对额
曲径通幽处(贾宝玉)
沁芳(贾宝玉)
绕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
有凤来仪(贾宝玉)
宝鼎茶闲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
杏帘在望--稻香村(贾宝玉)
新涨绿添浣葛处,
好云香护采芹人。
蓼汀花溆(贾宝玉)
兰风蕙露(清客)
麝兰芳霭斜阳院,
杜若香飘明月洲。
另
三径香风飘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兰。
蘅芷清芬(贾宝玉)
吟成豆蔻才犹艳,
睡足酴醿梦亦香。
红香绿玉(贾宝玉)
名家点评:
这些题园景的额对,内容上都是风月闲吟,但题额对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却是不可缺少的。
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种种活动都有大观园的背景上展开,作者通过贾政、清客和宝玉巡看新告竣的大观园,拟题匾对,一开始就把大观园的规模、方位、建筑布局、山水特色等等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重点的描绘。如果没有这一情节,我们很难设想用其他什么方法能使结构繁复、景物众多的大观园很快地就在我们读者心目中留下如此清晰、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安排,正是作者高出于一般的才能平庸的小说家的地方。
大观园中的几处房子,后来都分给宝玉和他的姐妹们居住,作者预先描绘这些各具不同特点的景色,以便用它作背景来烘托以后房主人的典型性格。如潇馆用竹睐烘托黛玉的性格,与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特点很相称。她容易伤感悲愁,所以又把竹子与潇湘的传说典故连在起。稻香村的环境,不但与守节寡欲的李纨性格调,就连楹联用“浣葛”等事,也与她家教素重封建妇德,认为女子“以纺绩井臼为要”,自己也“惟知待亲养子”等情况相称。蘅芜苑花木全无、幽冷软媚;怡红院蕉棠两植,红香绿玉,也都有意无意与房主人有关。
此外,作者还让题对额变与两类人在文才诗思方面的一次实的考核:一方面是被人称为“自幼酷读书”、当时在朝廷做官的贾政,以及他门下的一批附庸风雅的清客;一方面则是所谓“愚顽怕读文章”的封建逆子贾宝玉。考核的结果,谁优谁劣,谁智谁愚,谁被弄得窘态百出,这我们已从小说中看到了。在这里,作者对贾政及其门下清客相公们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赞省亲别墅
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
名家点评:
上一回描写要为正殿拟题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贾政道:‘此处书以何文?’众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贾政摇头不语。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象那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这里,脂评说,这是: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可见,“省亲别墅”原准备题“蓬莱仙境”、“天仙宝境”,都并非泛泛夸张。作者要通过这种描写暗示的是,贾府以大观园为代表的奢靡豪华生活和以贾元春为代表的尊贵显赫地位,只不来是幻梦一场,转眼就会破灭的。宝玉觉得似曾相识,又想不起来,这表面上说的是他对梦游太虚幻境中所经历的种种,尚留下依稀的印象,实质上则是他对逐渐弥漫有华林之中的悲凉之雾,能够比别人感受得更敏锐,而此时此刻又还不可能完全觉司的一种曲折的艺术反映。
上贾妃启
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行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帖眷爱如此之隆恩也。
名家点评:
如果要了解封建伦理纲常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曹雪芹所描写的贾政与元春之间畸形的父女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教材。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封建礼法渲扬男尊女卑、父尊子卑,最后都得服从于君尊臣卑。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中,有一种关系是最主要的,高于一切的,那就是阶级的统治关系、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它在种种关系中享有绝对的权威,不容许别的什么关系与之相抵触;如果有了矛盾,它就可以把别的关系踩在脚下。
省亲,表面上看,是让嫔妃回家看看父母亲人,叙天伦之乐,尽做女儿的孝道,倒确乎有点象贾府中人所颂扬的,“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第十六回)而实上如何呢?为了恭迎元春,贾府上下老小从五鼓起身直等到上灯,全都“跪止不迭”。做父亲的贾政更连见女儿一面都不可能,有话要说,也必须象臣子对皇帝那样奏启,而且一个只能在“帘外问安”,一个则只好“垂帘行参”。比起这样“隔帘”的“省亲”来,囚犯家属的探监倒可算是比较自由的了。为什么连父亲也不能见呢?因为元春首先是贵妃--皇帝的小老婆,而贵妃,除了太监,是不准与别的男人见面的,那怕你是父亲也罢。就连自己一手抚养的亲弟弟宝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元春没有传命,他也只能站在室外,所谓“无谕,外男不敢擅入”。同时,贵妃的身份、地位,又使元春成了皇帝的代表,所以,她的父母长辈,不但都要向她下跪,行“国礼”,而且说话必须称臣道名,用最恭肃卑顺的语言,就象一个下贱的奴才侍奉啊尊贵的主子一样。这一切都表明封建的伦理纲常,只不过是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工具而已。
贾政的奴才相,我们今天看来确是十分丑恶。明明是世家大族,偏说是什么“草莽寒门”;人家都说“上昭祖德”,他却偏要说“下昭祖德”。为了“颂圣”,当然不妨自卑自污,把贾家人说成是“鸠群鸦属”,或者比作别的什么也都无不可。只是这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元春难道不是贾家人,不是贾政的女儿?所谓“凤鸾”难道不是“鸠鸦”所生?曹雪芹抓住了这种矛盾的现象,深刻地表现了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如何轻易地抹煞和颠倒了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让我们看到封建专制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改变到何等程度,这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也并非贾政比别的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更善于阿谀奉承,更会挖空心思地想出“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一类话来。脂批就说:“此语犹在耳。”可见,此类语言,作者的前辈倒是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这种在我们的时代已难以想象的十分可笑的现象,在曹雪芹那个时代里、那种社会制度下、那个阶级之中,实在是被看成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顾恩思义匾额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
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
名家点评:
这类文字,就作品反映政治斗争的内容看,既是掩护,又是暴露。由天它“称功颂德,眷眷无穷”,所以是一种掩护;但由此看出贾府受皇帝特别宠幸的身份地位,让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个罪恶的封建大家族的政治靠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暴露。
大观园题咏(十一首)
题大观园(贾元春)
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
天上人间诸景备, 芳园应锡大观名。
旷性怡情(贾迎春)
园成景备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
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
万象争辉(贾探春)
名园筑出势巍巍,奉命何惭学浅微。
精妙一时言不出,果然万物生光辉。
文章造化(贾惜春)
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
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
文采风流(贾李纨)
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
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湘裙舞落梅。
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
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
凝晖钟瑞(薛宝钗)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世外仙源(林黛玉)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 宫车过往频。
有凤来仪(贾宝玉)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
迸砌妨阶水,穿帘碍鼎香。
莫摇清碎影,好梦昼初长。
蘅芷清芬(贾宝玉)
蘅芜满净苑,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
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怡红快绿(贾宝玉)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杏帘在望(贾宝玉)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 何须耕织忙
名家点评:
《大观园题咏》实际上是朝廷中皇帝命题叫臣僚们作的应制诗的一种变相形式。《红楼梦》这部以“言情”面目出现的小说,常常采用这种障眼法来描写它所不便于直接描写的内容,以免被加上“干涉朝廷”的罪名。所以,在这些诗中除了蔑视功名利禄的贾宝玉所作的几首以外,大都不脱“颂圣”的内容,这是并不奇怪的。
但同是“颂圣”,也因人而异。林黛玉所作就颇有应付的味道。如“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即是。命人赋诗者何尝不知其为了做诗而矫情地粉饰太平,但只要对方有这样的七领,能说得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就加以褒奖,真话假话倒无关紧要。宝钗的诗则可以看出从遣词用典到构章立意都是以盛唐时代那些有名的应制诗为楷模的。对她来说,歌功颂德,宣扬孝化文风,完全出于她的本心本意。她到称赞,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从匾到诗,还是个性化或暗合人物命运的。迎春为人懦弱,逆来顺受,所以自谓能“旷性怡情”;她缺乏想象能力,所以诗也写得空洞无物。探春为人精明,因知“难与薛、林争衡”,不如藏拙为是,故只作一绝以“塞责”;但“何惭学浅”之语,与迎春言“羞”,宝钗称“惭”,自不相犯,都表现各人的个性。也题“万象争辉”,写高楼崇阁气势巍巍,和惜春赞美造化神力,又都仿佛无意中与他们后来一个嫁得贵婿,一个皈依佛门等事有瓜葛。李纨,小说中虽说她自幼父亲“不十分令其读书”但毕竟出身名宦,“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非妇常家庭妇女可比;她后来被推为计社社长,除了因年长之处,也说明她还是懂一点诗的。她作的七律,也很符合这种虽乏才情,但尚有修养的情况:诗中或凑合前人旧句,或借用唐诗熟事,都还平妥稳当。所题“文采风流”四字,似能令人想到后来贾兰的荣贵,至于“未许凡人到此来”等语,又与她终生持操守节的生活态度相切合。如此等等,读《红楼梦》诗词时都是应该注意到的。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续《庄子·胠箧》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qu1) 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名家点评:
袭人不满宝玉与黛玉过分接近。她一边向宝钗说:“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边风。”一边对宝玉弄性气撒娇,故意不加理睬,冷淡他。宝玉恼恨之余,饮酒,读《南华经》,有所感角,趁着酒兴,提笔续了这一段文字。
题宝玉续子文后
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
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
名家点评:
与黛玉存在着矛盾的钗、袭,为了收伏宝玉,施展了撒娇含嗔,忽热忽冷的手法,使宝玉陷入苦恼之中。他从庄子思想中去寻求解脱,以为一论哪一方面都应弃绝不顾,才能怡然自悦。这虽是出于一时激、“趁着酒兴”所说的话,但毕竟还是皂白不分、是非不明之言。所以黛玉作诗相讥,说他“无见识”,不能知人,因为把黛玉混同钗、袭,都说成是“张其罗穴其隧”。说出这样“丑语”来的人,正应该知道“自悔”才是。作者让玉出来反驳,正是让黛玉为自己作必要的洗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