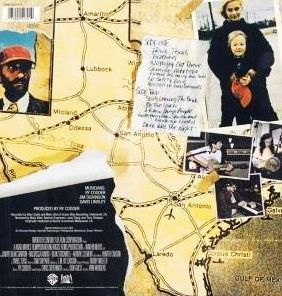【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本期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一个民族对某种东西感到荣耀,是因为这个民族因此有所得。所得有二,“内得于心,外得于人”,即内心心安理得,别人心悦诚服。一个民族,若在世界民族之林被认为毫无所得,它是不会觉得荣耀的。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荣耀心,与其所失,几乎没有联系。试想,一个民族,不论丧失了它珍惜的东西,抑或丧失了它轻视的东西,都会明显失落,岂有荣耀之理?
描述和分析中华民族的荣耀,怎么会从得和失两个视角来切入呢?将两个视角合一观,似乎是一个悖论。这一似乎是悖谬的合一视角,提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时,需要注意它的复杂面相。
邮票——四大发明
一个民族足感荣耀的事情,一定不是在生存的层次上。而且,一定不是只限于中华民族的有限范围。一个民族的存在,一定有其伟大人物的引领。不管引领者是宗教领袖、军事天才、政治人物、思想大家,他们为民族设计了足以保证其生存和发展的方案,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足以令人艳羡,倾力仿效。因此,民族荣耀一定呈现在发展层次,一定突破了国家界限。
民族荣耀不是自认的结果,需要民族间的公认。中华民族荣耀于世,不仅因为中华民族绵延了五千年之久,而且是因为我们民族在心灵上有所得,在世界的精神史上做出过独特贡献。换言之,世界历史曾经出现过和将要出现的中国时刻,才让中华民族感到荣耀。
近代以来,我们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民族荣耀问题被严严实实遮蔽起来。我们何曾设想过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我们满门心思在设想中国历史的自我时刻。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亢激昂的国歌,正表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何以有雅兴讨论中华民族何以荣耀于世的话题?原因很简单。我们民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集聚物质财富的公认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民族将有可能重临世界巅峰,在现代世界史上,以浓墨重彩书写属于中国人的新一页。
一、民族长期绵延的秘密
中华民族,历史绵长。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以“华夷之辨”,彰显文明与野蛮之别,凸显荣耀与羞耻界限。“华夷之辨”,今天被一些自命为阐释儒家理念的人认为是辨认民族政治边界的重要命题。这实在是太矮化“华夷之辨”的世界历史关怀和文明野蛮分野价值了。
我们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在精神上没有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华夷之辨”不应被理解为自命是华夏、别人是野蛮的二分命题。华夏乃是文明之谓,其范围一直在扩展之中。蛮夷,并不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而是对拒斥文明的族群的统称。“华入夷为夷,夷入华为华”,这是一种动态演进的文明族群的界定准则,而非固化认定某一族群文明特性的标准。
四夷表示图
可惜的是,“华夷之辨”后来演变为正统论,也就是将文明与野蛮界限的辨认,转变成谁居于政治正统的争执。这就突出了政治正当性资源的争夺,将文明与野蛮的重视程度严重降低了。历史学缕述的正统论,将汉民族自我绵延的政治史,视为是否居于正统的基本辨认标准。所谓“崖山之后无华夏,明朝之后无中国”,就是典型的断论。
对中华民族来讲,“华夷之辨”远比正统论更为重要。我们的远祖,开辟了德性政治传统,这是一种文明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是我们民族在精神上应该继承的正脉。一个朝代掌权者赋予的自我合法性辩护,如果依仗的是野蛮的权力奠基,那么,它就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既定文明轨道,就应当被谴责。这在正统论思维中,不是问题。因为正统论重视的是血缘性传承关系,重视的是具体族群的政治绵延。只要该族群掌握国家重器,其自我合法化似乎就应被无条件接受,这是不能肯定的强权思路,按照华夏文明的固有文明逻辑,必须追问掌权者在道德上是否正当,才能赋予其合法性资格。
天地有正气。中华民族之所以长期绵延的原因,就在于德性传统转化为天地正气。文天祥的诗《过零丁洋》,落地有声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片丹心,正是我们民族受人尊重的精神根柢,也是我们民族赢得历史荣耀和展现更大荣耀的心灵根柢。倘若缺乏这样的正气,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中华民族何以绵延至今,屡创辉煌。
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常常丧失理性、不夸示、持中道这些自我剖析的精神能力。我们常常陷入要么夸耀历史、要么指斥现实的两种悖谬状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自认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尽了荣耀和辉煌,那只能显现出这个民族在心灵上的极端幼稚和可笑;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对现实困境充满哀怨,总是抱怨历史没有传递下来丰裕物质、稳定制度和向上精神,那也只能显出这个民族对现实不负责任的状态。一个民族,之所以组成一个绵延长久的群体,就总是会有荣耀作为支撑。这一支撑民族绵延的荣耀,一方面有所得,得在它维系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另一方面则有所失,失在荣耀自身对民族尚未呈现荣耀的能力方面的遮蔽。民族荣耀自身,总是得失俱在、得失相伴的。
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吉普赛女郎艾丝美拉达
古希腊人的荣耀在宗教、艺术与哲学创造。古希腊人得在精神生活,但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个民族在政治治理能力上的孱弱。古罗马人的荣耀在军事征服、政治统治和私法创制。得在此失亦在此:古罗马人在宗教、艺术与哲学上的原创之功,远无法与古希腊人媲美。
曾经长期没有国家的犹太人,现在依然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以色列在二战以后,以对种族灭绝的道德审判为契机,与阿拉伯人强烈冲突,建立了旷古未有的新生国家。吉普赛人为什么浪迹天涯,却没有遭到灭顶之灾而至今生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族群依然有顽强生存的精神根基。尽管吉普赛人未能将其转化为政治建国尝试。
从存在的视角看,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一部荣耀史。存在的荣耀,都有自己的所得,亦有相应的所失。我们怎么平情地看待民族荣耀的得失相伴呢?中华民族的长期绵延与巨大成就,是我们的荣耀。华夏民族守正统、扬正气,成就了强大的人文政治世界,这是我们的所得。我们的人文精神、政治能力、治理传统非常深厚和悠久,常为其他民族和国家所艳羡。但我们缺乏追求精确知识的传统、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化限制不力,这是我们的所失。没有哪一个民族,荣耀仅仅呈现为光鲜的纯粹获得,而不存在被遮蔽的拙劣。
二、中国的信仰不能仅仅是中国
中华民族在人文世界足以确立其荣耀感。但所得亦是所失。发达的人文精神,分流了中华民族从事科学研究和限权努力所需要的资源,在这两方面的成就,中华民族远不如人文发展上取得的耀眼记录。就古代民族而言,科学方面,由希腊人登顶世界。法治方面,由罗马人登顶世界。就现代民族而言,立宪民主,由英国人登顶世界。后起发展,由美国人登顶世界。随着工业经济全面取代农业经济,中华民族陷入生产方式及其连带的诸种困境,由古代的典范性文明,转变为现代的学习文明。现代文明建构,是西方的优点,也是我们的缺点。
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特别强调,西方人在世界古代历史的书写上,并没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西方文明经过现代早期革命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工业文明的发育壮大,领先全球实现了现代化转变。这惊人的一跃,让人类从此开始进入第二个轴心期,超越了第一个轴心期的发展模式,启动了全人类寻求崭新发展模式的漫长征程。按照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西方的兴起,也是西方文明断裂的产物。西方登顶世界,远看,是从希波战争以后浮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历史变迁的结果;近看,是从12世纪一直到18世纪经数百年的坚忍努力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天下全舆总图》中,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
西方人做出的杰出现代贡献,伤不伤害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耀感?在特定意义上,当然会伤害。我们民族,在古代世界中,习惯于对周遭世界垂范。“天下体系”就是垂范于世的体系。但我们突然发现千年的学生毫不容情地跟我们说再见,并反过来给我们狠命一击的时候,我们民族的荣耀心岂不受到重创。
我们没有悠久的市场经济传统,缺乏工业革命的体制与机制,更没有行之有制的民主政治实践。如果说在人文社会世界的组织上,我们民族根据血缘关系建立了“家国同构”的精巧结构,根本不需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话,那么,在现代处境中,我们民族必须经过艰苦努力,补上这些落下的课程。
由于我们民族缺乏追求精确知识的传统,在现代科学与技术方面,也必须急起直追,以求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对今天的国人来讲,恐怕不能像一班科学学学者那样,动辄反思科学的局限。诚然,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不容否认,但需要借助科学建立精确知识体系,需要技术支撑现代生产方式的中华民族,绝对不能对之采取欲迎还拒的忸怩姿态。
我们确实遭遇到“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具有绵长的发展历史,但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临阵突破或临界突破。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我们绝对不能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在科学、艺术、宗教、哲学、政治诸领域都领先世界。如果不承认其他伟大民族为人类做出的突出贡献,我们就不能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多元状态、丰富景象,人类也就缺少了发展进步的多元动力。
李约瑟
我们民族由于发达的人文精神和政治治理能力,创造了世界的大国治理奇迹,这一荣耀的所得,恰与科学、民主的所失相伴随。今天的中华民族,自认为是一个现代民族,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中华民族确实健步迈进在现代大道上。问题是,中华民族真想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建构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就必须打开眼界,开放地吸收世界各个民族的优长智慧,这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重新登顶世界。
必须承认,今天中华民族对精确知识的兴趣还有待提高,对权力的约束行动还需要强化。迷信与科学的对决态势,还令人担忧;民主对专制的优势,还需要加强;世界对国家的超越,还需要理性认知;理性的自认对自负的感觉,还需要厘清;审慎的展望对骄纵的满足,还需要校正。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处在一个重回封闭状态,还是坚持开放选择的十字路口。审慎的决断,将对民族的未来发生决定性影响。
有学者在民族决断的关键时刻,强烈主张“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对之的具体阐释,需要人们耐心对待。但就这样的命题来讲,就有一种蒙蔽民族精神世界的嫌疑。中国的信仰,绝对不能囿限在狭小的国家的范围,应当以广阔的人类价值,展现我们民族的博大情怀。否则,我们民族就只能自限于孤芳自赏、不知今昔何年的尴尬状态。
三、荣耀的民族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
中华民族的所得与所失内在的勾连,意味着我们民族的荣耀感有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我们当然可以在历史记忆的深处,获得民族足以荣耀于世的资本。历史荣耀可以支撑我们民族的现实希望。但历史荣耀必定定格于历史,它并不能解除我们民族现实荣耀的匮乏。当下,只要举证中国人的荣耀证明,四大发明仍然是常列的证据。这样的言说自然不假。但问题在于,一说中国人的荣耀就举的是数百年前的论证,难道当下国人就做不出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情了?我们只有以现实取得的更大荣耀,才能真正让我们民族的荣耀之心不灭。
我们民族今天在物质财富积累上,已经成功突破,大致奠定了我们民族重回世界的物质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是特别雄厚,但已经作别了物质匮乏时代无暇想象民族复兴的窘迫。下一步,我们需要在制度和精神上的伟大突破,才能以现实取得的巨大成就,荣耀于世。
中华民族如何才能争取更大的荣耀呢?
第一,必须进行坦率的民族心理自我剖析。我们民族的荣耀是建立在得失相伴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民族因有所得而荣耀,因有所失而可能自卑。整个民族自觉意识到荣耀乃是得失相伴的事实,乃是一个心理挑战。将所得与所失切割开来审视,不是没有道理,但不能思及所得,便忘乎所以;思及所失,便陷入自卑。进而因自卑而自戕,“破罐子破摔”,完全丧失自我超越能力。由此可见,确立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对一个民族争取更大荣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倘若民族的自我心理剖析达到了理性认识自我的目的,这个民族就会扬长避短、查漏补缺、茁壮成长、追求卓越,尽显伟大。
苏联“国家英雄”——宇航员加加林
第二,必须建立理性而严格的比较文明思维。一个民族既希望自我超越,又希望兼得其他民族的优秀品质。希腊人兼容了东方波斯的优点,因而登顶西方世界的荣耀巅峰。汉唐综合了整个东方的优势,不仅对内整合了儒、道、法,而且对外整合了佛学,将东方思想熔冶于一炉,因此登顶东方世界的荣耀巅峰。一个拒斥外民族善性精神、适宜制度和生活新风的民族,一定会陷入自我封闭的泥潭,一定实现不了更大的荣耀。
这一文明间的理性比较路径,要求我们民族在心理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批判不惧激烈,辩护出于温情。不要以为,激烈批判我们的民族状态、批判我们文化传统的人,就是所谓“西奴”,就是民族的敌人,就要以绝不妥协的态度跟人家战斗到底。只是在我们民族自我进步、自我发展、重新光耀于世的基点上,再激烈的批判,都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精神动力。
辩护者也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些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中国传统做出的辩护,都是强词夺理。虽然,进行辩护,就不免强词夺理,但辩护者不能回避强词夺理所带来的心理阴影。辩护者可能因此无法揭示中国传统的真相,无法理性剖析我们民族荣耀的得失所在。这样就背离了为民族传统辩护的初衷。
为民族荣耀辩护,需要温情。温情与敬意相连,是我们民族在心理上能够成功地承接传统、自我超越的重要心理基础。如果我们在为自己的传统辩护的时候都缺少温情,就与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一样壮怀激烈,那就是心理不健康和不成熟的标志。我们需要区分清楚,批判不惧激烈,是因为我们要严格剖析自己的弱点;而辩护不乏温情,这是要多方呵护中华文明根基。两者的关系,是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
第三,中华民族要追求更大的荣耀,需要塑造强大的民族自我心理。大节不亏,小节不纵,对人而言是如此,对民族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民族一定要在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不懈积累民族重光于世的资本,我们绝对不能大而化之地讨论民族国家的前途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倘若我们把相关问题玄虚化、空洞化、抽象化,那我们在民族复兴的大节上肯定会有亏。因为大而化之的思路,一定会将我们引向记住历史荣耀、忘记现实艰辛的窘境,我们就会重回封闭的状态并且放肆地自我夸耀,以为这样的自我夸耀就足以呈现民族的更大荣耀。这是民族精神不成熟的显著表现,我们必须超越民族精神的自我囿限,坚忍而理性地积累民族复兴、重登巅峰的资本,并由此促成民族的涅槃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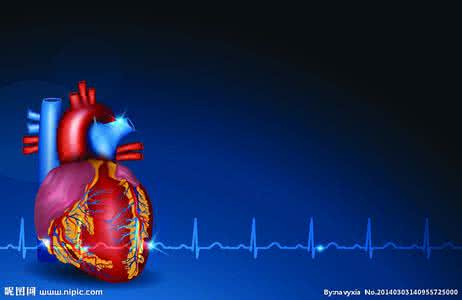
(作者:任剑涛;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