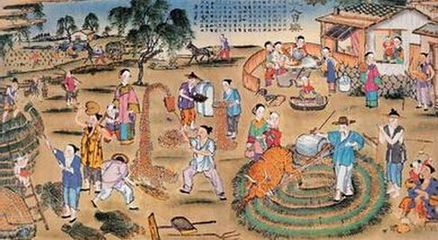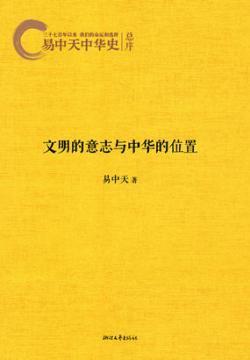世界文明的双螺旋发展
王春

前面,我们探讨了星旋态与现代科学的契合问题,即自然规律问题;接着探讨了星旋态与古代科学的传承问题,却不仅仅是自然规律问题,还涉及社会规律问题。下面要讨论的题目,则是世界文明的双螺旋发展。读者可能心存这样的理念: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规律。我们说,这句话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西方人从“天人二分”的视角,即主客二分的视角看世界,必然形成“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凯撒的还给凯撒”这样的理念。当然这并不为错,站在自然界的层面看,它有自身的规律;站在人类社会的层面看,它也有自身的规律。但您是否想到,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从整个宇宙的视角看问题,能否发现宇宙与人类的同一基本规律呢?
东方人正是从“天人合一”的视角看世界,发现了宇宙与生命的同一规律——反对称的双螺旋太极图像,并命名为“一阴一阳”之道。而《黄帝内经》有进一步的阐释:“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这就意味着,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尽管万象纷呈却能推理出若隐若现的相似形态。
这种若隐若现的相似形态,即太极图像并非是固化的绝对的存在形式,而是动态的形式流变的过程。诚如《易·系辞下》中所阐释:“为道也累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这就是说,道并非是固化的、静止的,而是不断迁移、运动、虚实流变的。因此太极图是对道的追踪,捕捉了道的一切形式流变之像,然太极图自身似道而非道,故“一阴一阳之谓道”。
由此可见,东方人对宇宙之道的思考、把握、表述,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截然不同。“道,可道,非常道。”如此深邃的表述,难道不令世人震撼么?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他考虑到:天籁之音,罕闻其声;天道之形,难觅踪影;宇宙之道隐隐约约,无从名状。如是说,虽可用语言来表述道,却要以自然之道的失真性为代价。这与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重点提示,相互呼应。
西方人难以理解孔子和老子的“道论”并不奇怪,而中国的某些知识精英却认为《周易》是“伪科学”,反倒令人惊讶。在我们看来,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珠联璧合关键的100年,世界文明的双螺旋发展,迟早会跨入星际文明。此言有何根据呢?这原本是星旋态宇宙层层嵌套的、分形与回归的流变法则——双螺旋结构、双螺旋运动、双螺旋发展。
宇宙乃是永恒振荡的电磁场,物质与力都是电磁场的振动起伏行为。宇宙的手性揭示了正、反物质世界膨胀与对流、收缩与穿越的运行轨道;一切分形结构都离不开电磁波的双螺旋圈环运动与演化,包括地球与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换句话说,星旋态宇宙一分为二地无限可分,使宇宙中充满了万有的结构——分形星旋态;星旋态无法可分原理,使宇宙中充满了万有的运动——双螺旋流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及所创造的世界文明,都体现了这一规律,而无出其外。万有结构、万有运动形成了星旋态宇宙的关系网络——万有辐射场态。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业已包容在这个网络之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起来的双螺旋历史圈环链。
回顾一下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双螺旋流变的历史轨迹显得格外清晰:轴心时代,东方(中国、印度)与西方(希腊、罗马)文化平行发展,呈现对流环行的统一图像;中世纪,出现了东方文化超越西方的景观;近现代,出现了西方文化领先于东方的奇迹;在当代,对流环行的东西方文化临近于一点,令世界文化面临新的历史转折点——第二轴心时代的来临。
第二轴心时代的主要特征,莫过于文化观念的更新。即世界多元文化统一于全球文化意识:全球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全盘东化,而是顺从人类文明自我构建的形态——东西方文化相交缠的双螺旋演化。当然,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在哲学、科学、政治、宗教、艺术等等问题上,所经历的思想沟通、智慧互补、道德融合之过程,则是观念更新的前提。
这一过程早有动向,并形成了当今世界思潮。1918年,李大钊(1888~1927)先生对西方“动的文明”和东方“静的文明”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以动补静”重构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提出:“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被誉之为“世纪智者”,1920至1921年他访问中国后,写《中国问题》一书声称:“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争斗、开发、无休无止的变化、冲突和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够从它所鄙视的东方文明学得一些智慧的话,它将走向毁灭的终极”。
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说:“现代物理学家与东方神秘主义者的方法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实际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它们对世界的描述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一旦承认这种相似性,就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难道现代科学及其所有的复杂仪器只是重新发现了几千年前便为东方圣贤所知道的古代智慧吗?……在科学和神秘主义之间能否相互影响,甚至合成在一起呢?”朱清时、姜岩合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指出,东西方的思想体系起源于不同文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其方法是公理化方法;源于中国的东方科学思想是整体论,其方法是实用化方法。西方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瓶颈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恰好需要东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补充。二者互有优劣,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1995年,姜岩博士参加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葬礼。在协助整理李约瑟的遗物时,一段遗言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作出伟大贡献”。
在我们看来,中国要想对世界文明再次作出伟大贡献,应尽快促成《周易》宇宙学现代化,让东西方科学文化再交流。然东西方文化交流,始于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有着2100多年的悠久历史。按照董光璧先生的话说,“世界之易学”时代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所开启。利玛窦是在1582年来中国的,距今也有400多年了。我们说,“世界之易学”仍然是二层嵌套的双螺旋结构。中国易学与印度佛学整合的东方易学双螺旋结构,是谓第一层次;东方易学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对立互补的双螺旋结构,是谓第二层次。
一般来说,“世界之易学”的实质也就是易学的世界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周易》宇宙学的现代化。可是,易学世界化走过了400余年尚未成功,但东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印证的态势已然呈现。如是说,易学世界化的初步实现,无疑是世界文明步入第二轴心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