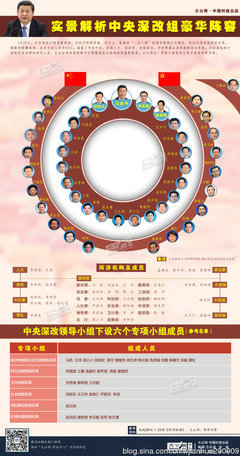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
李:您工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很奇特的机构,几乎所有的成员先后都被打倒。其中有些人文革后得到平反,比如陶铸、王任重。而另一些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打倒的,至今还是所谓“反面人物”,比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因此对他们的描述往往流于空泛和政治化,其中还有一些丑化,这对他们也是不公正的。希望您从近距离观察的角度,谈谈对他们的看法。比如康生,你跟康生有过接触吗?
俊:有过接触,但不多。他平时跟办事组工作人员话不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挺清高,对底下人挺漠视,根本不在意。我们对他也不害怕,因为他和别人不怎么接触,不像江青,还没来,就震唬住了,服务员也很紧张,哪怕万一房间里有个苍蝇、蚊子,那都不得了。
有一次康生通过戚本禹给我们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中办机要局受到一些单位造反派的冲击,挤得水泄不通。戚本禹让矫玉山和我去做工作,叫他们不要冲。我们去了也拦不住啊!造反派把矫玉山白汗衫上洒了好多墨水,矫玉山在那儿嚷嚷半天,他嚷完我接着嚷,也不行。后来,戚本禹告诉我们这是康老让去的,康老指示:谁也不能冲机要单位!机要局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让外边的人冲(那些所谓“外边的人”,都是中央下属的机要部门的)。我们出来的时候灰溜溜的,因为人家不欢迎你干预这事。对这件事我们写了个简要汇报送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也就无下文了。几年前,黄宗汉病逝了……
阎:他死了可惜啊,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了解很多情况。
俊:对,他经历全过程。文革前康生组织写《九评》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文革后,到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阎:康生去世后,黄宗汉当上了副军级的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俊:康生去世后他的几个秘书都安排相当好,黄宗汉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是正厅级干部。后来,我到黄宗汉家去过一趟,我说你的安排真不错!他说康生临终跟汪东兴说的,有遗嘱:一定安排好。
康生连他的服务员都安排得不错,钓鱼台服务员杨德田一直在八楼照顾康生夫妇,康生散步走到哪儿,他把躺椅搬到哪儿,后来康生把杨的老婆、孩子全给搞到北京来了,安排了工作,安排了房子。
阎:文革后我到黄宗汉家去,见他厅里挂着好几个条幅,都是高级干部和名人赞扬黄宗汉的。我问他这件事,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大权、宣传大权都归康生了,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他起草的,然后康生签上字,就生效了,有些人得到了解放或安排了工作,所以很感谢他。李鑫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生病去世了。现在写的抓“四人帮”,没提到李鑫,据汪东兴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是李鑫。前两年,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写的抓“四人帮”文章,谈到李鑫的建议,在一个刊物发表的时候给删掉了,他专门去问过:“为什么删掉?”刊物回答说是上边的意见。
郑: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现在中央对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的秘书李鑫就是坏人了,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对黄宗汉我非常奇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到各处做报告,说康生在粉碎“四人帮”当中的作用,说康生临死之前指出江青有问题,等等。
王:当然,康生这个人确实不好。就拿赵永夫事件说吧,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的司令员,在一次大会上抓赵永夫,我在场。总理找了几个老帅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逮捕赵永夫的事情。是王力起草的文件,我去京西宾馆亲自交给总理的,总理当时就签收——因为是绝密文件嘛!在会上就要抓赵永夫,康生在会上就审问赵永夫,问他三几年在华北参加过什么?当场就说他是特务、汉奸,就给戴上了帽子,在会场就铐上带走了。
阎:我见过中央文革的成员接见内蒙古的人。康生当着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的面就说:我看你面相就像个特务!
《王力反思录》还说过康生的好话,说他保护文物什么的。听广宇说,康生对砸孔庙不满意。
王:是,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好像有这么一条罪状,说康生大量地侵吞国家重要文物,而且罪行很大。
阎: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俊:后来,我从曾在康生办公室做生活管理员的杨德田那儿也听说,康生临终时嘱咐他将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此事是由杨德田具体承办的。
康生住的八楼,我去过好多次。他喜欢古董,他的房间里古董特别多,特别是文房四宝、字画特别多,有挂着的,另外有几个大盆插着一轴一轴的。陈伯达的房间古董也特多,有裱过的字画,有文房四宝。
康生经常看电影,就在他的楼底下大厅,同工作人员一块看。
李:听说江青跟康生关系不错?
俊:康生给我的印象是他跟江青的个人关系不错,江青看电影经常有他陪着,他再困再累也陪着江青。有时候康生陪着陪着就睡着了,江青说别打扰他,睡觉是最幸福的。等电影完了,康生还在那儿睡呢。平时江青打电话叫他干什么他都来,有时候她跟张春桥、康生单独商量些问题。康生有个特点,开会穿拖鞋。不过比较起来,他好像请假比较多,后来康生的身体就不行了,请假也就更多了。给我一种感觉,康生基本听江青的。江青对康生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她跟陈伯达常发脾气,对康生从没发过脾气,对张春桥、姚文元也没发过。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尊重康生,依靠康生(江青称呼他“康老”),而张、姚是她的得力助手。王:你对张春桥、姚文元怎么看?
俊:他们什么事都特别谨慎,不轻易表态。姚文元这个人有时神神道道的,记得有一次他从楼上突然下来到我们房间转一圈,走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又来了,他坐这儿,我在对面,他口述让我记录:“当前大批判的方向……”他嘴里念叨着,我就记录,念叨完了我记录完了,就交给他的秘书,时间不长清样印出来了,他稍加修改就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
李:社论都口述啊?
俊:字不多,也就两三千字。
王:他写完社论都要送给主席看吗?
俊:他是特别谨慎的,而且摸不出什么规律来,很少轻易表态,大的社论说要送主席审阅的。
李:姚文元平时跟你话多吗?
俊:话不多。张春桥话多一点,他有时候还下来到我这儿看一看,问问情况,张春桥好像城府很深,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张春桥的知识面宽,能力也比较强,写过九大政治报告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正好和姚文元相反,他胸有成竹,写的草稿干干净净的,几乎都不改什么,姚文元写得很快,但是很乱,涂改很多。张春桥写东西的时候,有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他在房间踱来踱去,酝酿文章,听完音乐再写。夜里有时候写到两三点钟。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我觉得这点还挺好,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点上确实很注意的。我接触他们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两性关系的事一点都没有。张春桥爱人文静在上海,姚文元爱人金英也在上海,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把家属带来,后来都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了,张春桥也没让文静过来。姚文元的爱人后来才给调过来。他们都是很不顾家的主儿!
张春桥跟工作人员相处比较平易近人,他从上海来,几次都是江青秘书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他,江青秘书杨银禄跟我说必须得说“代表江青”去接他,还有王良恩代表中央办公厅去接。
李: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一般你们两个人同时去接?
俊:同时去接。到机场以后张春桥下了飞机,握握手,车都准备好了。到那儿我给他敬个礼,说:“春桥同志你好!我代表江青同志来接你。”王良恩也给他敬礼。接了以后,当时也没有开道车,坐“大红旗”,我在前面,他跟我聊天,聊聊北京怎么样啊,社会发展情况。很自然,他没什么架子。
李:你一般都跟他说点什么呢?
俊:我不主动跟他说话,他问我就说。他问:你们现在工作忙不忙啊,累不累啊?因为他也没带秘书,所以他早晨起来在钓鱼台散步,有时我陪着他,他就跟我聊天,他说你要忙就不一定陪我了……
王:张春桥确实比较平易近人,在他手下工作和在江青手下工作不一样。姚文元那人就平时话语不多。
俊:姚文元学英语很刻苦,从广播事业局借来录音磁带听发音,晚上自学,后来杂志他都能看了,挺聪明的。他这人的脑子专走一根筋,感情不太丰富,不像张春桥。张春桥你要到他办公室去,还有点笑容。比如有时我去跟他说杨银禄又来电话了,江青请你看电影。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手头上的事还没完呢,半截思路打断了……我说要不就告诉杨银禄不去了?我刚要出门口,他说:“算了吧,我还是去吧,让司机备车!”许世友来北京要求见张春桥,因为当时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就把这个记录送给张春桥看,张春桥跟我们说“不见,就告诉他没时间”。
李:许世友见张春桥,要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
俊:当时张春桥还没有专门的秘书,他的秘书何秀文在上海,十大以后他在北京稳定了,才又给他安排了专职秘书。
李:在以往的传说中,总是说许世友不买张春桥的账,总给张春桥难堪,根本不理他!现在照您一说,事情是反着的:许世友要见张春桥,张春桥不见他!
俊:因为当时张春桥地位高啊,是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才是军区司令员。我记得许世友秘书两次电话说要求见,我亲自跟张春桥本人说的,张春桥说不见!
李:那您怎么回话,也跟许世友秘书说张春桥不见?
俊:说“没时间”就完了。
李:跟张春桥共事,您还记得还有点什么事吗?
俊:后来,他看我们清理文革小组的资料里有30年代的作品,有从韦君宜和杨述家抄的画册,他说你给我拿来看看。里面有关美学方面的,有人体美、裸体的摄影等等。他说,看完我会主动退给你的。果然,几天后就退给了我。
李:张春桥和姚文元平时看什么书啊?
俊:姚文元的书,连线装本都有,因为姚文元让我们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去买过好多书,一大摞。
李:都是抄家来的?
俊:对,但都作价了。那当然优惠了,大概一本也就一两毛钱吧,买了一摞。他看书特别快,线装本老书没多会儿就翻完了。他文学方面还是不错的。张春桥也爱看书,但张春桥很文雅,经常听听音乐。大部分都是施特劳斯的,他在房间地毯上漫步,哼着小调。
我记得有这么件事: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嘛,三老四帅对中央文革不满嘛,拍桌子了。当时叶剑英写一首词:“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这是忧国忧民,对文革不满,但套用的词牌是什么,出处在什么地方,当时谁都不回答,问郭老(郭沫若)也没音信。当时张春桥就说这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他对现实社会不满!这个出处就找到了。还有《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给张春桥写信,她说她现在很苦闷,她想再写《青春之歌》第二部,请求张春桥给一点指示。像这些文人,他都有交往,而且他这方面的修养不错。
李:他那房间里的书主要有什么呢?
俊:历史的比较多,文学的,哲学的。
李:有马列的书吗?
俊:当然有了,这是每个房间必备的。他读的比较多,古书看的也多。特别姚文元古书特别多,一有时间就看书,博览群书,绝不浪费什么时间。不愿意看电影,两人都不愿意陪江青看电影,但是也都没办法,也都跟着去。
李:他们有点生活情趣方面的享受、爱好没有?
俊:像姚文元基本看不出来,就喜欢看书,有点苦行僧的劲头。张春桥就是有时候自己吟诗,在房间里踱步,听听音乐,朗诵诗,有时在钓鱼台的湖边散步时哼两句。大部分是吟诗,背诵名人的,我觉得他挺有情趣。有时候跟孩子通电话,还有点父爱的亲情。书画也有,但没看见他自己写和画的。
他们吃饭也很简单,三菜一汤,当然做得比较细了,肉丝切的比头发丝粗点吧,就这么简单。包括碰头会,吃的也是家常菜。李: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好侍候吧?
俊:比较好侍候,没这么多事。衣服有钓鱼台的洗衣房,饮食有专门厨师,出行有专车。那时他们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
李:有人写文章说,张春桥是“摇羽毛扇的”,形容他有点阴险,您在日常相处当中有这种感觉吗?
俊:因为他们之间商量事的时候,我接触不了,张春桥的个人私事更无法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接触不到本质问题。
李:王、关、戚您都接触过?
俊:王、关、戚就接触多了,因为王力、戚本禹在我们楼上,关锋在十五楼。王力这个人很和气,我给他送文件很和蔼,从来也没有发过什么脾气。相反,戚本禹倒稍微牛点,年轻气盛,他是中央文革成员当中最小的,比姚文元还小一岁,一九三一年生,当时才三十五岁。他写那个《忠王不忠》评李秀成的文章,总理都夸他是青年历史学家嘛!他原来在中办秘书局信访处工作,有时候爱发脾气,我看跟他的秘书程里嘉瞪过眼,有时候对底下的人不是太客气。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傲气,个子高高的,也有点派头,人称“戚大帅”。
郑:关锋呢?
俊:关锋在十五楼,接触最多的是他的秘书瞿怀明,关锋也挺和蔼的。
李:其他的小组成员您还有没有深刻印象的?
俊:穆欣比较早就离开了钓鱼台。王任重、刘志坚是副组长,他们时间也比较短,当时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住在钓鱼台二楼,各带两个秘书。1967年1月,王任重、刘志坚都被打倒了。刘志坚对底下的人比较苛刻,刘志坚刚一倒,他本来腿不好,警卫员小黄还踢了他一脚。李: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您还观察到哪些外人不了解的现象?
俊:我看出来江青跟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整理者注)有矛盾。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一次批陈整风的华北工作会议上,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江青说陈伯达是你们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然后提到了关于河北磁县武斗是陈伯达搞的,挺厉害的。她说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挖碉堡,也可以设铁丝网,文攻武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江青说的是对付武斗升级的问题,吴法宪在旁边说:“江青同志你还懂军事啊?”江青大发雷霆,拍桌子说:“我跟随毛主席三十多年,怎么不懂军事啊!”把吴法宪给顶回去了,吴法宪挺尴尬的。这是华北工作会议上的一个小插曲。
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怎么样?
俊:当时我看出江青跟总理有矛盾。当然,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原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总理都带着秘书周家鼎或钱家栋,他们都是大秘书,后来还有赵茂峰、孙岳,这四人都带过。有一次周家鼎、赵茂峰在办公室跟我聊天,聊得还挺热乎,江青进来了,她挺生气的,那意思好像我们背后议论什么事,实际上我们就随便聊聊。不知江青跟总理说了一句什么,后来总理再也不带秘书到十六楼来了。只带警卫小高(高振普)、护士和医生张佐良或卞志强,他们这几个人轮流来。
1968年7月27日,就是中央派驻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那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已准备就绪,等待命令。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问题,碰头会商量好了,总理说请示主席去。总理就让秘书打电话问:“主席休息没有?”说可以来。总理就提着皮包要到主席那儿汇报。此时,江青匆匆出来了,连忙说她去。总理就说你去吧。总理在会议室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江青才回来,说主席同意马上派。这命令一下,当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就进驻清华、北大了。
平时我看见一散会都是江青第一个乘车,总理礼让,当时对江青这样做我们挺看不惯的!总觉得江青对总理尊重不够。中央文革办事组退出历史舞台
李:关于中央文革“散摊儿”的事,我想听您认真地说一下。文革这场暴风雨过后,文革办事机构最后负责打扫残局的就您一个人?
俊:背景是这样的。九大之前是真忙,好像有点代替中央办公厅工作了。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那文革办事组当时就相当于办公厅。办事组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通知开会、组织活动、会议记录,跟随领导到大会堂接见人,等等,确实是挺忙活的。记者站也是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基本是代替一部分新华社工作,办信组代替中办信访局,每天有几大麻袋群众来信。九大以后工作就逐渐少了,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在十六楼开,也由办事组通知,我记得一直到1970年,有一年多的过渡吧。
李:这个期间,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日常活动都做什么事情啊?
俊:九大开了以后,产生新的政治局了,会议刚开始还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但不叫文革碰头会了,叫政治局会议。
李:办事的还是办事组这些人?
俊:还是那些人。但工作陆续由中央办公厅接管了,像文件类的印发由办公厅秘书局来管,会议由秘书局会务处来通知,钓鱼台的管理人员负责会议室的清理。开会时接电话也不少,都是内部电话,比如说总理找谢富治,我们也得给他找,总理说请李雪峰(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来,由我们打电话去请。会议的服务工作像汪东兴说夜宵吃什么,通过我告诉服务人员,就这些事务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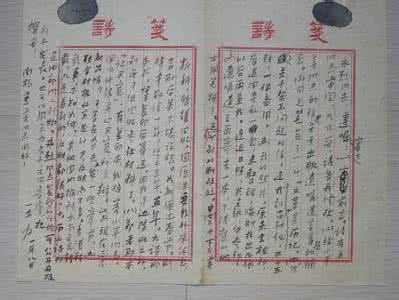
李:会议用的材料打印不在这儿?
俊:不在这儿。
李:那会议形成的纪要整理也不在这儿?
俊:不在这儿,我们谁也不参加会议做记录。汪东兴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事就找王良恩去办,王良恩是办公厅副主任。一切具体事情都由办公厅做了。
李:什么时候就进入了收尾工作了?
俊:1970年就开始收尾了,是汪东兴秘书高成堂通知说:“你们清理所有的文件,登记造册。”清理文件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因为文件太多了,到1972年春节后才完的。
王:戚本禹、王力、关锋的文件是不是也都要清理?
俊:对,所有的东西嘛,他们的房间始终都是关着的。我们清理的时候包括抄家的东西,都给清了。
李:当时有多少人负责清理?
俊:有五六个人吧,我负责。有二十三军一个叫赵明学的,中办信访局的魏登甲,中办机要局的郭亨乾,北京卫戍区的姜才熙。姜才熙后来也倒霉了,只因当时江青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出去,姜才熙老婆生孩子不能回去,他十分不满说不讲人性,“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结果有人写信报告了,王良恩报告了汪东兴和江青,让他立刻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并给他写一个鉴定说“在工作期间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讲了不应该讲的话”。姜才熙回卫戍区部队后不敢用他,第一批就转业到武汉了。
李:您的任务就是把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文件、资料、物品都登记上,还有其他活动吗?
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中办还通知我参加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军以上干部会议,听林彪事件的报告。这段时间让我们揭发、批判的事也不少。我们原来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后来又揭发批判林彪。
李:除此之外大概两年时间都是在清理文件?俊:对。
李:当时清理文件有哪些要求?
俊:一是分类。就是把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央文革的文件,包括文革《快报》《简报》,所有的文件都分类登记,按等级。另一类是所有的传阅件,也登记。这里还有主席亲自批的原件,《要事汇报》大都是主席亲自批的,我记得有山西陈永贵请示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七二七”进驻清华、北大的主席批示,我们就分类登记。
当时有规定:凡是主席的批件一定要用一个塑料套套上,便于档案馆保存。所有领导人都用铅笔写东西,铅笔才能留得住,保留时间最长的就是铅笔,比钢笔要长。
王:有烧的和毁的吗?
俊:不让,一片纸都不要落下,都要原封登记。包括矫玉山抽屉里工作人员交的党费,有一千多块钱哪,一分一分地点,注上“工作人员的党费”,还有矫玉山的笔记本。
王:我那个办公桌和卷柜里东西很多,毁没毁?
俊:毁是没毁,我们都登记上了,都交给中办了,而且中办来人一一核对,当时中办挺严格的。
李:除了您说的大量的文件、《快报》《简报》、传阅件等等,还有什么?
俊:还有电话记录和会议通知,各种抄家的物品。书比较多,还有画。古董好像就是印章、文房四宝这类的,我记得有油画,韦君宜的,当时挺有名的。这都是艺术珍品啊!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画报,展示东方的、非洲的、西方女性美的裸体照片、人物画。还有古书,都黄了,都是抄家来的东西。
李:登记的时候还登记是从谁家抄的吗?
俊:只要有来路的都登记上,不知道的就没办法了。比如画是韦君宜的,写着韦君宜的名字呢,韦君宜本人画的。还有杨述,他俩是两口子,这肯定是抄他家抄来的呗,好像是老王拿过来的。
还有大量送给中央文革的礼品,毛主席像章多得很。还有送给毛主席的茶叶,当时就打电话问这茶叶怎么办?回答说就放你们那儿吧。给毛主席送的东西挺多的,茶叶呀,各地的特产什么的,各地制作的工艺品,整整一大屋子毛主席像章,还有其他好多礼品。
李:这些东西都能登记上来路吗?
俊:咱们只能登记毛主席像章来自什么地方,有的写着呢,有的还附上一封信,信都打开过,送的礼品没什么保密的。
李:当时给毛主席送的礼也就这些?
俊:对,没有别的。
李:通过文革小组送上去的,就是纪念性或政治性比较强的?
俊:对。来了以后我们就请示,回答说就放在你们这儿吧!
郑:那些茶叶搁久了也不行啊?
俊:搁久就搁久了,那怎么办啊?那也不能动啊!谁也不敢动,谁也不会偷着分了喝了。连周恩来到十六楼喝杯茶还记账,一角钱呢!很廉洁啊,这是真事!让卫士高振普记账。
李:这么一大堆礼物,除了送给毛主席的,送给江青、陈伯达的有吗?
俊:送给中央文革的比较多,是写着“中央文革收”,我们收下。送给个人的我们就给他们的秘书打电话,一般就回答说“放你们这儿吧”。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都有,我们就放这儿。
李:他们本人知道不知道有人给送礼物啊?
俊:我估计大部分都不知道,因为到秘书那儿就打住了,太多了,这都是小事。
李:下边的“革命群众”捧着一副热心肠,到那儿连“中央首长”本人都不知道啊!
王:刚开始还有人给中央文革捐款呢。刚才你说矫玉山办公桌里存的钱,那里面是群众的捐款。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表示支持文革,给寄钱,都不多,几十块钱。所以你刚才说矫玉山抽屉里的钱应该不是党费,咱们党费都在原单位交。就是捐的,咱们不是没财务嘛,也没开支,所以收入都放在矫玉山的抽屉里。
俊:后来矫玉山还问我他的东西动了没有,我说没动,你的茶叶盒还在呢,一个一个、一件一件都登记上交啦!
王:我的抽屉和卷柜里有几部分东西比较重要,一个是陈伯达、康生接见时的记录,接见的这些人都是比较重要的干部,比如康生接见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还有监察部的人,都是用纸记的。再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记录,我参加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做记录,我把主席的讲话记录都整理起来了,就是经我手办的事我都没丢,全都在那儿呢!俊:你放心,丢不了,都给登记上了。
王:还一个重要材料就是张根成和周占凯收下的成立革委会和接见各地红卫兵的录音。
俊:录音还有,录音带都是大盘的。反正我们当时都登记上了,作为一类吧。
王:这个事赖不掉的。会上江青、陈伯达怎么讲,都录了,还有速记录,中央办公厅有个速记员,专门速记,我们拿来,没“翻译”过来。这都很重要,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史是有用的。
还有一本咱们中央文革办事组搞的刘少奇的材料,合订本将近寸厚,这是咱们自己出的。
俊:有,一大厚本!
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当时没时间看那些东西。
阎:审判的时候拿出录音让陈伯达听,让江青听,可能就是从那儿来的。
李:录音这是一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照片之类的?
俊:照片就很少了,有那么几盒是毛主席、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那照片是1967年12月照的。
李:在清理文件中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吗?
俊:比较深刻就是涉及总理那件事,这也是算大事。大概是1970年7、8月清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一张旧报纸报道关于“伍豪事件”那个事,因为这算是大事啊,我们把它密封着移交中央办公厅。不久王良恩把我叫到中南海,到一个挺深的院子里的办公室,他很严肃地说他“受汪东兴同志委托跟你谈一件事”。就是关于总理那件事,让我至死不要说,绝密!“这是给你的一条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说,这件事主席早已知道”。我说:明白,我按您的指示去做。谈完,他让我走了。对这次谈话我感到很紧张!
王:中央文革办事组何时结束工作的?
俊: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逐渐减少,大量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取代了。不久,汪东兴批示中央文革办事组清理文件,大约两年时间完成的。1972年4月文件清理完毕,全部移交中央办公厅并办理了正式手续,中央文革办事组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