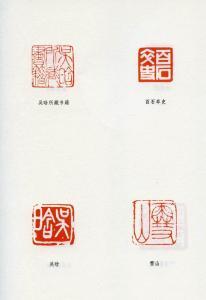二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七、八年前我到上海多次应聘,想找一所满意的学校继续我的中学教师工作。为此,我投寄了许多材料,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有至少三所学校表示可以接纳我,但不能接纳我的夫人,理由都是一个,她的身份是工人,“工人我们不要!”
上海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技术工人尤其是上海的骄傲。2010年世博会上,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期待着上海能拿出几件令人们眼睛一亮的发明创造和高新技术产品。然而,正是上海的教育部门,在科教兴国之际喊出了“工人我们不要”的规定。且不说这种规定是还违反人权标准,仅就其政治性质而言,也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属于“违宪”规定。因为新中国的宪法至今仍强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
文革时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月风暴”之后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红极全国,那时,“工人”成为中华大地上最闪光的一个词儿。当然,上海也成为极“左”错误的重灾区,我读到一篇文章回忆说,文革时期大约有一万多台钢琴被抄没,“钢琴”成了“文化毒瘤”。

我无意时至今日仍然故意撕裂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伤痕”。不过,历史是很容易被忘记的。文革时期还讨论过“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江泽民主席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当知识分子的“尾巴翘上天”的时候,喜不喜欢弹钢琴似乎就成为了“人才”的分界线,“工人我们不要”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理直气壮。
有人可能会从我的这篇文章里读出点“大字报”大批判的味儿,可能还会很不高兴。不过,当我听到儿子说他“绝不愿意当工人”的表示时,心里真的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儿。在儿子喜欢玩的电脑游戏里,“工人”的角色往往是最弱的,他们除了开矿、造飞机、坦克、盖房子、搭桥等等“做工”之外,几乎毫无抵抗力,很轻易地就会被对方“消灭”掉。儿子心目中的工人,无论是虚拟世界中的工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工人,与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已完全不同。老实说,作为文革时期成长的一代,虽然1978年我就以应届高中生资格考上了大学本科,但我从未认为工人低人一等。20多年来上班下班,我做的教书工作与工人做工并无太大区别,教师的收入也只是近几年才明显提高,很长时期与工人的工资差不多少。但是,如果说我现在支持儿子把当一辈子工人作为选择,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高考那年我填写入团申请书时,学校工宣队的一位师傅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说:“你隐瞒出身,应填写地主,而不是干部。”我的爷爷是地主成份,父亲毕业于南开大学,理应填干部身份。当时工宣队师傅的话,对我内心影响很大,因为地主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就是“周扒皮、黄世仁、胡汉三、南霸天”那样的人,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爷爷呢?有关这个话题,我在其他文章里还有提及,这里不愿多谈。今天,当我告诉学生,美国总统布什就是个地主,美国人叫“农场主”,学生们恍然大悟:“地主原来是这样的。”他们的羡慕之情与我们当年的憎恶之情,完全截然不同。
今天,作为一名教师我常常感到困惑:教育究竟起什么作用?是教育人们学会平等相待?还是教育人们分成三六九等?
其实,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好,还是“知识分子领导一切”好?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些今天已经不是真正令人关心的核心问题。也许,我们离共同富裕还很远,但是,重要的是人类的现代化社会必须找到一条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途径。
笔者与上海钢琴厂有一段不解之缘。去年,他们第四次上门,派两位工人技师为我家钢琴调换钢琴弦,他们一下火车,水不喝一口,烟不抽一支,立即动手投入工作。两天内我亲眼目睹了上海工人传统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很精湛的工作态度,内心十分感动,并以最大的诚意款待他们,他俩也表示满意。我很怀疑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们还有多少这种“工人阶级的感情”。
鲁迅先生批评某些中国人“脸一阔就变”。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最近,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放言说:“目前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大了,而是小了,应该扩大贫富距离,这样社会才能更和谐。”甚至还说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以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这些经济学家,有的标榜自己的钱包里“从来就不装人民币”,他们用美元看中国的房价,声称“中国的房价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未来五年内至少还应翻三翻。”……
历史上,纳粹主义者也说过诸如“牺牲犹太人的利益”之类的语言。当某些人言语偏激之时,人类的理性与良知就会面临挑战。当有些人不仅仅只是说说,而是打算动手实施的时候,人类面临的就会是“人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