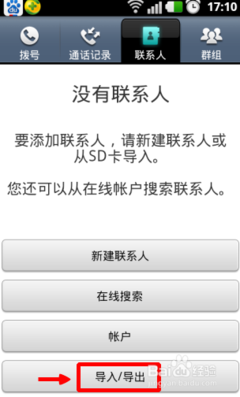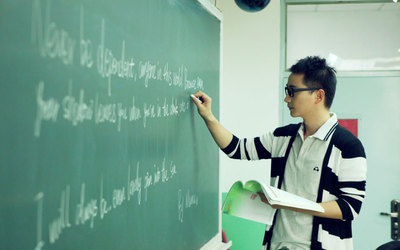20年前,一本《野火集》横空出世,直指台湾社会众多不公正、不光明的丑恶现象,也让人记住了作者的名字――龙应台。从此,这个瘦小的女子成为勇敢直面人生黑暗的猛士,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她仿佛钢筋铁骨,全身长满尖刺,让人不得近身。而从5年前开始,深情隽永的《孩子你慢慢来》和《亲爱的安德烈》,直到如今的《目送》,干脆直接地将另一个龙应台推到读者面前。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6/view-25958.htm
也许,所谓两个龙应台,原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完整组成了那个敢爱敢恨、坦率深刻而又柔情刻骨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怒目金刚
龙应台的硬气是骨子里的。她个子不高,眼睛不大,有雕刻感的脸庞线条坚毅,总是有点冷的感觉。出生于高雄眷村的她,遗传了曾做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的性格,坦率,直接,不平则鸣。
在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她赴美深造,直到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并在纽约市立大学和梅西大学任副教授。当1983年她回到台湾时,已经离开故乡10年了。这lO年里,龙应台从一个单纯快乐的少女成熟起来,懂得了思考、怀疑与质问的价值,而台湾岛正处于变革的前夜,热切希望突破现状,推翻权威。这种环境让这个有思想有胆气的知识青年感觉窒息。回来不到1年,她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女“立委”的谈话中涉及台湾社会,语气颇为自私自满,被触动了正义的神经,一口气写出了杂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当时并无太深关系的《中国时报》副刊。文章甫一刊登,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
广泛的支持。龙应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文章一连串写下去,凡是她看到的不公正不文明现象,都要付诸笔端讨伐一番。
到1985年底,几十篇文章集结出书,《野火集》真如燎原野火,上市后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四个月里卖出了10万本!诗人余光中形容当年龙应台掀起的风潮犹如“龙卷风”,几乎每个台湾家庭都有一本《野火集》,他家也不例外,“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买回来的”。《野火集》的风行其实很简单,那个焦灼的时代需要尖利的批判,撕破温情脉脉的窗户纸,给老百姓一盆凉水甚至是当头棒喝,让人们清醒一下,行动起来。
龙应台在序言里说:“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不戴面具,也许丑陋得让人不敢正眼面对,不裹糖衣,可能苦涩得让人无法下咽。她对社会的批判,对台湾人、中国人的批判犀利得触目惊心:“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龙应台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威胁。那时她父亲经常打电话给她,检查她是否在家,因为听说很多“不听话”的人晚上就那么被套上麻袋扔到河里去了。龙应台出门旅行两三天,父母也会紧张得不行。
温婉女人
1986年,龙应台再次离台,赴瑞士结婚。此后的两年,她安心做太太,并生下了大儿子安德烈。从1988年开始,她到海德堡大学教书,赴俄罗斯访问,在上海《文汇报》开专栏,依然做着她的老本行:教书匠和公共知识分子。1999年,她应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之邀,回台湾担任文化局长。当2003年卸任之际,她恢复学术之身,却悄然与丈夫离了婚。对于那段婚姻,她表现得如此低调,从来不曾让丈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即使离婚后,她也只是在《银色仙人掌》的自序里用第三人称淡淡地写了一笔:“作者出远门去了,背着一个人们看不见的行囊,行囊的轻重,只有自己知道……起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开始写,写自己的离婚书,写完传出。”
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是乐于谈论的。也许在龙应台心中,婚姻只是自己的私事,而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孩子的沟通和教育,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是全民族的事。所以,她欣然把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幸福与快乐,痛苦与担心都摊开来与人分享。安德烈14岁那年,龙应台离开德国回到台湾,下一次母子重逢时,安德烈已经是一个18岁的大学生,身高184厘米,可以出入酒吧,有了自己的驾照和母亲不知道的生活,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作为母亲,龙应台下意识地惊慌、焦虑,她决定不再连任,只在香港大学作一名客座教授,以重拾母子之间的生活。她问安德烈愿不愿意以书信的方式和她共写一个专栏,儿子竟然答应了。3年6个月的通信,无论是针锋相对,彼此嘲弄,还是午夜交心,知性辩论,再加上网上对谈,电子邮件和越洋电话,龙应台进入了一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她依然是那个担心儿子吸毒的母亲,却能更坦然、理性地理解年轻人那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十万字的篇幅不算长,但《亲爱的安德烈》的写作过程,却比《野火集》惊心动魄得多。
到了《目送》,她把三代人的情都写到了。往上看有逝去的父亲、老去的母亲,往下看有青春的儿子和自己的年少时光,身边审视的是自己即将迈入的老年。目送着去异地求学的儿子时,龙应台想起了当年,父亲这样目送着离家求学的自己,想起几年前目送着棺木中的父亲――这是她第一次目送至亲的死。五十多岁才经历生离死别,到底有点迟了。作为台湾的外省人,龙应台在台湾只有父母、兄弟,她从未目睹亲人离世,直到父亲逝世。在那之前,她极爱站在高处看世界,当最后一次目送完父亲,目送长大远行的儿子,才知道有太多无奈和失落必须放手。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如此简单洗练的文字,不再充斥问号和惊叹号,却只有经历了刻骨铭心之痛才能写得出。龙应台目送着父亲与儿子的背影,读者也始终目送着龙应台的背影,和她的一次次离开与回归。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