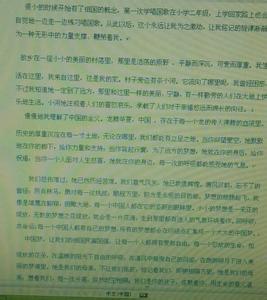传说在宫廷舞会上,巴赫的大提琴被做了手脚,除了G弦之外,所有的弦都断裂了。当大家准备看巴赫出糗的时候,巴赫,仅仅只用了一根G弦,就即兴演奏了一首《咏叹调》,该曲子就是今天所说的《G弦上的咏叹调》。

巴赫的晚年,他已经被当时的人们看成了保守派的代表。在启蒙思想传遍的欧洲大陆,音乐上,意大利风格的单纯明快的作品成了那个时代的新宠。巴赫的作品被人们公然攻击为是“太过技巧性,完全无法理解”的音乐。对于处于孤立之中的老年巴赫而言,继续创作“与自己的心做交谈的音乐”成了他最后的救赎。晚年的大作,“哥德堡变奏曲”,“平均律第二卷”,“赋格的艺术”等都是在这种心境下完成的。而就当巴赫在许多人的对立面上一一将这些作品颁布于世的时候,巴洛克时代的音乐也渐渐走向了完成,并在巴赫的集大成中实现了“终结”。一七五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巴赫因脑梗塞而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古典乐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地进入了新的时代,巴赫和他的作品也早早地就被人们所遗忘了。然而,正当人们在一个叫做古典乐派的新时代里欢呼雀跃,将新时代的音乐宠儿们一个个推到时代的最前线时,他们和他们的崇拜者们一个个都蓦然发现,古典乐派,甚至是后来的浪漫乐派中被认为是“新”的许多要素,式样以及音乐语法恰恰是来源于上一个时代的巴赫音乐。巴赫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同时,他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是过去,现在,也是未来。 在古典音乐史上,巴赫一直被认为是超凡脱俗的“圣人”。那是因为,他的音乐不仅确立了西洋古典乐发展的基础,还因为他在有生之年创作了大量的宗教音乐,以音乐向世界传播福音的圣徒地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然而我想,巴赫音乐哪怕被爵士化,或是摇滚化都依然被人们所热爱的奥秘就在这里。他是将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化成了音乐,并将它作为祷告而奉献给了上帝,他的音乐绝不是从天上飘落至人间的音乐,在他的音符中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威严,而是最最微不足道的平凡的生命。 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尔特曾这样对比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在上帝面前,天使们歌唱的毫无疑问一定是莫扎特的音乐,然而,是不是巴赫的音乐,那则未必。”
印象中的大提琴深沉,低沉,淡然,忧郁而不悲戚,欢乐又不张扬,又带着无限的似水柔情去缓缓讲述,很多很多都被融进大提琴舒缓的弦声中,复杂到让你一直沉下去忘记什么叫计较。当探戈碰到大提琴,当热情撞击舒柔,富有节奏的胶着,若即若离的缠绵在弦下更衬托出的柔美,然而探戈的热情的不失,宛如耳语呢喃。谁知道呢?就像老帕说的探戈是自由的,探戈中永远没有错误。 大提琴给了探戈灵魂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难以兼备的热烈。简单成就了探戈,融入低沉的复杂,滤出叹息中的杂质。如果可以,把生活当做一曲探戈,一场没有预演和草稿的狂欢里,抛开台词,在框好的拍子里,即使被绊倒,也请继续探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