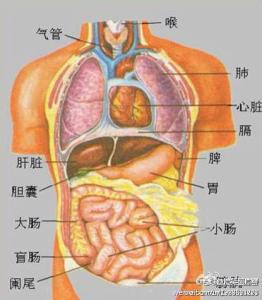“老人不想儿子走得不完整。”经历了5天的解释和劝说,家属仍然婉拒了捐献的提议,不得不说,这是吴平意料之中的答案。
吴平,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名游走于死亡与新生之间的说客。大多数时间,他反复承受着潜在捐献者家属的拒绝。
据了解,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2010年3月,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
劝捐故事“希望反复落空”成工作常态
7月17日上午,在广西出差的吴平接到信息员电话称,有一名脑干出血患者,大器官功能良好,已呈现临床脑死亡状态。吴平匆忙处理完工作,乘夜航航班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次日上午就赶到医院。
患者是一名男子,患高血压,饮酒时引发脑干出血。男子的父亲、爱人都在,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承受不小的打击。吴平出示协调员证件表明来意,“两人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好在没表现出反感。”
当天在医院的会议室,吴平与家属长谈近4小时。“他们对捐献本身没有疑虑,倒是对一些细节很在意。”例如,“不捐的器官是否会拿走?”“后事如何处理?”等等,他一一作出解答。两人同意捐献,但想等其他家属到院后进行。一切都看似很顺利。

19日,吴平再次致电两人,得知其他家属当晚抵达北京。20日下午,吴平再次来到医院,男子的病情已呈现不好的状态。他心里很着急,“捐献者离世后,在一般条件下,大器官要在10分钟内实现快速降温、灌注保存液,否则便无法使用。很多准备工作要提前进行。”
又谈了3小时,家属都表示同意。此时弟弟却说,“能否再等等,让母亲看一眼?”吴平有些蒙,“之前家属隐瞒了,可能怕母亲过于悲伤。”然而捐献须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在内的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缺一不可。患者母亲在老家,无奈之下,吴平让家属准备她的委托书。捐献被再次搁置。
21日早晨8点多,家属通知吴平称,男子病情恶化。他赶往医院时男子心跳已经停止,委托书仍然没有着落,他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很快,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也很痛苦,说只差一步就能捐。”
这场景陌生又熟悉,自成为协调员开始,希望落空反复上演,已成为工作的常态。
部分兼职协调员为医护工作者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为两种,专职协调员和兼职协调员。据介绍,专职协调员在红十字会工作,兼职协调员则在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工作,本身为在职或退休的医护人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