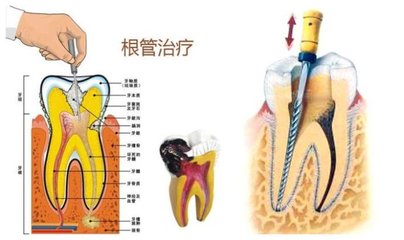正是管仲的“富国强兵”理念,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代代相传,才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内领先世界,这样的功德和基业应该可以超越“德才”的衡量标准了吧?
从布衣到卿相,管仲被人奉承为“春秋第一相”;清末的梁启超干脆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柏杨也说,在国史中,堪称为政治家的不过六七人,管仲是第一人。然而这个恢弘的政治家,当初却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
管仲是颍上( 今安徽颍上县) 人,祖上曾是贵族,很小父亲就死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管仲很幸运,和鲍叔牙是同乡,鲍叔牙大他2 岁。生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生在一起。从商,管仲多拿多占;从军,管仲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从政,管仲三次被罢免。这么一个各方面表现糟糕的人,鲍叔牙却不离不弃,都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而管鲍之交则超越这个天条。
管仲的才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未成年人成熟的力量。鲍叔牙是他的兄长、朋友,更像是老师。在鲍哥的正面引导之下,教学相长,两人都茁壮成长起来,只是各有所长,一人偏才,一人偏德。
两人结伴,德才兼备,他们来到工商立国的齐地,终于历练出了人样,齐僖公分别拜管 仲、鲍叔牙为二公子纠和三公子小白的师傅。两人既非大臣,也非贵族,僖公拜他们表面上是私塾先生,其实是帝王之师,此时,两人的见识才学名望已经为王室认可和倚重。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风暴。
齐国经过一系列残酷的高层洗牌之后,轮到避祸国外的二公子和三公子争夺王位了,昔日好友管仲和鲍叔牙随即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里。这场斗争,其实是两位智囊的决斗,有趣的是,它更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兄弟谁先回到国内,谁就是王,后到者是臣,而且是罪臣。
于是,管仲干脆带人去拦截老三小白。冲突中,管仲一箭射中小白衣钩,小白装死骗过管仲,抢先回国即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奇怪的是,当时管仲为何不去检查一下?或者补射一箭?是疏忽大意?还是故意放他?还是当时没有那个实力?难道并非真要他死,只是要他不要那么快地回到齐国? 后来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显然是避免了管仲这个难以原谅的错误。
公子纠一伙则慢悠悠回去,听到新君即位,如雷轰顶,只好退回鲁国。胜利后的鲍叔牙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说服桓公拜管仲为相,并设计把管仲从鲁国要了回去。他说,主公如果只想管理好齐国,有高傒和我就够了,如果还想王霸天下,那非用管仲不可。桓公志向高远,不计一箭之仇,在鲍叔牙的开导之下,化敌为臣。
桓公之所以如此,就是要用射他衣钩的人,替他射天下。两人之前的争斗,就当是干部任用之前的考察,这样另类的考察那是相当的准确、真实。管仲以商人的手腕做宰相,很有创意,先是相地而税,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又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思路都很精细。
以钱买罪的赎刑制度也是管仲首创的。即老百姓犯了法,可以赎身,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盾一戟,此一举,齐军的装备得以迅速升级换代。他又开设“女闾”七百,创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大半个世纪,越国的勾践就率先效仿。
对外,管仲更不客气。因为只有国盛产食盐,管仲便大大提高出口食盐的税率,相当于全天下人民都向齐桓公缴纳盐税。
为了制服鲁、梁,齐国不惜发动“粮食战争”。齐国人人穿丝制衣服,但只种粮食而不种桑树,导致丝价大涨;于是,鲁、梁二国都争相把丝运到齐国卖高价,没人种粮食,只一年,两国就出现了饥民,不得不屈服于齐国的霸权。
管仲又用同样的手法,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衡山的械器,制服了楚国、代国,吞并了衡山。
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周王室一次,这就是所谓的“九会诸侯,一匡天下”,这里面也有管仲赚钱的法门。
桓公与管仲预先秘密制造了大量石璧,然后串通周王,宣布诸侯朝先王之庙,礼物就是石璧。诸侯仓促之下,只好来齐国购买高价石璧,结果,齐桓公一下子聚敛了八年的财政收入。这等于是把尊王攘夷的成本转嫁给了没有搞尊王攘夷的国家,以邻为壑,把政治上的成功转化为经济上的好处。
孔子高度评价管仲攘夷的功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说,没有管仲,元朝和清朝就会提前出现了。但管仲认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个人富比王侯,虽然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孔子却批评他“不知礼”。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干脆把他两人合在一起写传。南宋的朱熹也说,管仲之德,不胜其才。
然而,正是管仲“富国强兵”的理念,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代代相传,才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内领先世界,这样的功德和基业应该可以超越“德才”的衡量标准了吧?
来源:真情家具TIME(微信号:jiajutime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