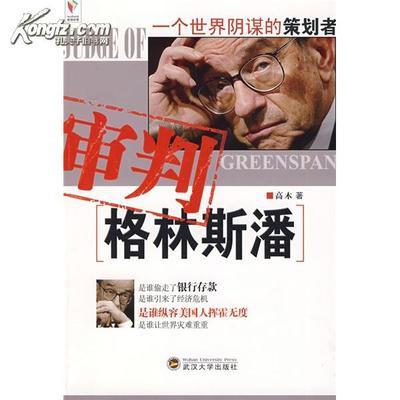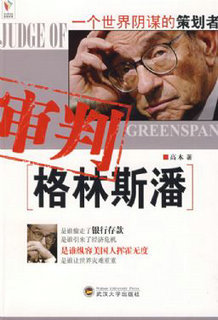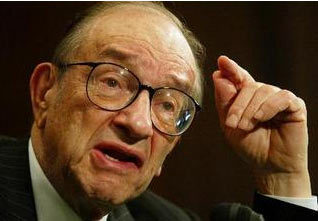原標題:作家格非談潘金蓮:是個惡人 但從不掩飾自己(圖)
格非,本名劉勇,生於1964年,江蘇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校任教。200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調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他的中篇小說《褐色鳥群》曾被視為當代中國最玄奧的一篇小說,是人們談論“先鋒文學”時必提的作品。其新作《雪隱鷺鷥》日前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文/關軍
作家格非曾說過,中國隻有《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三部好小說,它們雖然各具特色,卻又一脈相承。在寫完《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烏托邦三部曲”之后,格非於前不久推出了《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對《金瓶梅》一書進行分析和解讀。書名“雪隱鷺鷥”四字取自《金瓶梅》的詩句:“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意思是茫茫大雪下隱藏關於人性的幽微丑惡。“我覺得《金瓶梅》特別適合做敘事分析的文本實例,它比《紅樓夢》的視野更寬,內容更雜,而且和經濟史、社會史的關系更密切,它也有寫實主義和自然文學的痕跡。”格非如是說。他甚至認為,雖然已經過去了四五百年,但我們仍然沒能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視線。
十六世紀的人情世態
並不讓人感到陌生
《雪隱鷺鷥》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經濟與法律》,主要講述《金瓶梅》所表現出來的明代社會的法律與經濟的關系,熟悉明史的人可能會覺得講得不深﹔第二部分是《思想與道德》,主要講的是明代社會變革下思想史的發展變遷,《金瓶梅》與陽明心學的關系,《金瓶梅》與西方啟蒙思想的對照,從薩德一直寫到尼採,把《金瓶梅》放到全球舞台上去評判,這也是此書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第三部分是《修辭例話》,對《金瓶梅》的文本進行系統分析。在這方面前人已多有涉及,格非雖然沒有翻出太多的新意,但也不落俗套。
著名作家韓少功在評價《雪隱鷺鷥》時說,這本書“寫得飽滿、豐富,是一種驚人的釋放。深解、詳証、細品、透悟都做得十分出色。作家寫不出它的前半部,學者寫不了它的后半部,因此這本書注定是空前絕后。”
格非與《金瓶梅》相遇已近30年,在這期間他不斷地進行閱讀,不斷地做筆記。在反復閱讀的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於十六世紀前后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聯系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脈絡,《金瓶梅》中涉及到的許多重大問題,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釋。
“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刺激以及這種刺激帶給我的種種困惑,也是寫作此書的動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現的十六世紀的人情世態與今天中國現實之間的內在關聯,給我帶來了極不真實的恍惚之感。這種感覺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我甚至有些疑心,我們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視線。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或許正是四五百年前就開始發端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大轉折的一個組成部分。”
《金瓶梅》的大膽描寫
是對《水滸傳》等傳統小說的冒犯
格非認為,如果僅僅將《金瓶梅》歸類為“情色小說”,就把這本偉大的小說“讀薄”、“讀小”了,《金瓶梅》在西方的影響力要大於《紅樓夢》。
他說,《金瓶梅》中的情色部分是不容回避的,但他同時又認為,作者所想呈現的“色”不僅僅包括色情,還包括很多物質、欲望等方面的東西,更接近《心經》中所說的“色”的概念,或許這也是他要給書加個副標題“《金瓶梅》的情色與虛無”的原因所在。“因為是匿名,作者不需要為自己的創作承擔某種道德上的責任,所以他就更加自由一些。欲望每一個人都會面對,《金瓶梅》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拒絕說謊,這也是《金瓶梅》要思考的問題。”

在《金瓶梅》之前,中國的古典長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描寫的都是歷史故事或神話傳說,很少關注市井生活和日常生活,更不會用大量篇幅進行情色描寫。在格非看來,《金瓶梅》的大膽描寫是對包括《水滸傳》之類的傳統小說的一種冒犯,是一種全新的寫作﹔它對生活細節的描摹,對后來的《紅樓夢》又產生了很大影響。《金瓶梅》還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從此以后,文人創作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流。
《紅樓夢》對“高潔”的肯定
大大超越了《金瓶梅》
格非說,“《金瓶梅》中沒有賢人,隻有惡人、愚人、痴人、妄人,有的人更是將各種人性丑惡集於一身。”比如道德觀念中最“惡”的西門慶、潘金蓮,書中也呈現了性格中“真、趣”的一面。作者這種“無善無惡”、“既是又非”的相對主義價值立場,讓他們的形象無法簡單評判,增加了人物的復雜性。
格非在書中引用了大量原書中敘述的經濟來往,以此判定西門慶屬於情商低、財商高的“經濟型”人格,跳出了以往對西門慶“淫棍”、“惡霸”的定論,令人耳目一新。“潘金蓮、西門慶等等人物形象,與賈寶玉、林黛玉相比也毫不遜色,他們完全可以載入中國人的倫理史,成為建構我們自己文明身份的一部分。”
格非雖贊賞《金瓶梅》的寫作成就,但並不贊同它所傳達出來的思想,“我很贊同儒家的看法,欲望還是要有節制的。《紅樓夢》是對《金瓶梅》反動的再反動。從整個世界觀來看,《紅樓夢》比《金瓶梅》更豐富,層次更多。曹雪芹重新把君子的品格,把儒家作為最重要的思想再次放進去了。《紅樓夢》裡儒釋道都有,但儒家的思想是全書裡最感人的部分,他宣揚不要同流合污,所以林黛玉的高潔被他做了最重要的肯定。這是大大超越《金瓶梅》的地方。”
談人物
西門慶:
一個有欲望的普通人
對西門慶的評價,歷來有三種看法,第一種把他看成一個壞人,這是最普通的看法﹔第二種看法是他是一個有欲望的普通人﹔第三種就是有人為他翻案,覺得這個人其實還不錯,對朋友有信義,對親戚和佣人慷慨大方。我個人同意第二種看法,我覺得作者塑造西門慶的用意是想把他寫成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都受著欲望的困擾,隻不過作者把這種人在西門慶身上極端化了,因為他要批判欲望,必須要塑造一個典型。正因為這是一個被極端化的普通人,所以我們在看西門慶時,都能觀照到自己一部分的原型,所以西門慶這個人物塑造得實在是很了不起。
應伯爵:
靠嘴皮子生存的“掮客”
西門慶雖然在經濟事務上精明強干,但在人情交往上很天真,他那種“呆”,那種智商很低的“淺”是很幼稚的,你看的時候簡直想笑,這都說明這個人心裡還存留一些對人好的地方,可是這惟一的“善”在應伯爵身上卻是沒有的,他是一個心機隱藏太深的人。
西門慶的可愛在“淺”,而應伯爵的可愛在言辭漂亮圓滑,話語玲瓏,會裝愚做痴,這個人不得了啊!應伯爵的形象空前絕后,《金瓶梅》前后的文學世界裡你找不到一個類似的形象了,西門慶的形象你能在《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薛蟠身上“拼”出來,可是應伯爵的形象找不到,這是一個不斷依附於有錢人的“掮客”,他沒有原則,又隱藏得很深,他總能投其所好,鑽到你的心裡去。其實西門慶未見得沒發現應伯爵的“偽”,但他需要應伯爵,他升了官需要有人捧,尋歡作樂需要有人應景玩笑,所以這兩個人形影不離,彼此需要。我甚至判斷,作者有可能和應伯爵從事相同職業,都是靠嘴皮子生存的“掮客”,不然怎麼會描寫得這麼細致入微?
潘金蓮:
是個惡人但不掩飾自己
《金瓶梅》中對那群女人的描寫,取得的成就確實可以跟《紅樓夢》比。其實很容易把她們寫得很好色,但在《金瓶梅》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舉止、口吻、心裡的小九九等等。比如潘金蓮是個惡人,但她是真的,做事從不掩飾自己。李瓶兒膽小柔弱,通過退一步博得好感,但這種做事方式,不要說在明代,在現在也是行不通的。她就是一個可憐人,但她身上也不是說沒有心機。在《金瓶梅》裡,兩個偉大人物是西門慶和應伯爵,但我覺得,作者寫女人更為成功。
(柏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