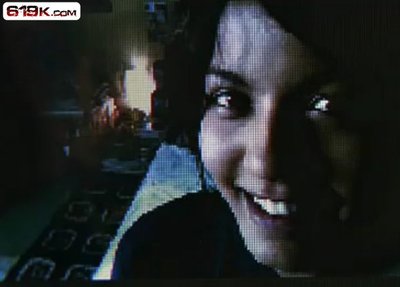如果说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到国内战争胜利这三年时间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站稳脚跟的时期,那么1920年代就是决定苏联今后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时期。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本是一条可能引导苏联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在党内斗争中随着布哈林的失败而被中断了,托洛茨基坚持的世界革命道路也随着他的失败而被抛弃。随着各个反对派的被击败,斯大林模式成了以后几十年苏联的唯一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促使苏联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导致苏联整个经济平衡失调,除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外,涉及国计民生的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滞后状态,1950年代的粮食产量甚至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而未果。苏联后来出现的各种弊病都与1920年代的斗争有关联。因此书写一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1920年代历史,为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寻根溯源就非常必要,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的政策方针不是在1930年代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早在1920年代,甚至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可以看到种种端倪。例如内战时期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斯大林模式的雏形,诸如计划经济、公社和集体农庄、书报检查、不容异见、打压知识分子、压制教会、集中营机制等等,在1920年代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当然斯大林对此种种均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且多数场合是变本加厉,推向极端。例如斯大林的大镇压无论从人数、规模和范围来说都是前所未见的。
《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有不少新东西,是俄国和中国出版的苏联史书中回避或很少涉及的。择其要点简介如下。
1921年初列宁说,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实际上国内战争后期,农民因对粮食征收制不满而纷纷举行暴动、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城市,广大工人也因为生活状况每况愈下而不满,举行罢工游行,民众的情绪也影响到军队,酿成喀琅施塔得兵变。农民暴动在官方的文件中是看不到的,在列宁著作只看到“盗匪活动”的说法。实际上,当时的农民暴动已经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所以本书在谈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用一定的篇幅描绘当时国内农民起义的情景。
兼并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这段历史是迄今为止俄国出版的史书都回避不写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允许波兰、芬兰以至乌克兰独立,列宁认为,实行民族自决权,允许民族自决直至分离,反而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他说过,可以允许乌克兰试试独立,也允许它加入俄联邦,或者再退出。但是自波兰和芬兰独立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不许国内任何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权口号只针对国外的国家,例如支持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苏维埃政权继承的是沙俄的地缘政治,恢复沙俄的版图是苏维埃政权所追求的目标。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宣告独立,成立民主共和国,由孟什维克领导。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格鲁吉亚共和国有双重不满,一是不能让它独立,要使之回归俄国;二是更不能容忍由政治对手孟什维克来领导这个国家,必欲灭之而后快。1920年5月,俄联邦同格鲁吉亚共和国曾正式签订相互承认的条约。但是过不多久,1921年2月,红军就入侵格鲁吉亚,占领梯弗利斯,把格鲁吉亚并入俄联邦。其实,布尔什维克如果大度一些,允许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继续执政,实施他们的理论方针,进行另一种社会主义实验,也许会为世界留下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未必不是好事。这段历史即使现在出版的苏联史书也是几乎不提的,然而这是一段确实存在的历史,应当写入史书。
新经济政策对农民做了让步,允许农民缴纳一定的粮食税之后自由支配余粮。这样就导致粮食的自由买卖,于是布尔什维克从禁止自由贸易转变为承认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实施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改革,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暴动基本上被消除了,财政币制改革尤为成功。然而在政治领域,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弥补对农民所做的让步,在政治领域反而加强控制。这在三个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1.打击宗教势力,特别是东正教。俄国居民80%以上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居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布尔什维克需要同东正教争夺社会影响。1921年俄国发生严重的饥荒,政府和各界开展了赈济灾民的工作。高尔基发起由一批名人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东正教也成立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不仅在信徒中间募捐,而且决定把教会所拥有的非宗教用品的金银珍宝捐献出来。但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非常担心这两股势力影响的扩大,取缔了这两个救灾组织。
2.驱逐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制造“哲学船事件”。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广大知识分子处境悲惨,他们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等领域不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经过一番准备,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了数百名文化领域的知名知识分子,把他们送上轮船,驱逐出境。被驱逐的知识分子一般并无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只是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或者措施。哲学船事件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丧失了一批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家,影响了苏联文化、科学的发展,但无意中也使这批人士逃过了1930年代的大镇压。驱逐知识分子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威慑措施,布尔什维克政权想借此迫使知识分子心服口服地归顺苏维埃政权。托洛茨基曾经为驱逐知识分子的措施辩护,但不幸的是,到1920年代末他自己也遭受了这种驱逐,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3.镇压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沙俄统治时期,俄国存在两大社会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前者后来分裂成两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孟什维克党(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者也分裂成两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政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都是第二国际成员党。他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是方法道路上存在分歧。十月革命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度同布尔什维克党紧密合作,后来因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分歧,中止了这种合作,社会革命党人曾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但1919年停止了这种武装斗争并获得苏维埃政权的大赦。虽然其多数领袖都已被投入监狱,但他们在居民中尤其是农村仍存在广泛的影响。为消除他们的影响,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审,把其中的某些领导人判处死刑。虽然由于国际上的强烈抗议以及畏惧社会革命党人的暗杀(他们有实施恐怖暗杀的传统和能力),不久对被判刑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实行减刑和赦免,但布尔什维克达到了打击和消灭社会革命党,同时打击孟什维克的目的,使苏联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以上三项措施充分说明,布尔什维克在对农民做了让步之后,再也不想在其他方面后退让步了,他们要把对农民让步的损失在其他领域找补回来,加强对其他领域的控制,当然其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暴力和专政。这种做法预示了1930 年代的镇压,是1930年代大规模镇压的先声。
党内斗争对苏联的前途有重大影响。关于党内斗争,我国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很少谈及,俄国出版的苏联史著作,谈得也不深入。联共党内的斗争事关苏联以后的命运,决定了苏联以后的发展方向,所以本书根据解密档案,尤其是当年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速记纪录以及一些人士的回忆录,尽量复原当年的斗争情景,展示出1920年代苏联复杂多变,各种派别集团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图景。在1920年代苏联有过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集团,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联合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斯大林多数派等派别集团,对他们的主张、他们的目标不应当回避。这里既有权力斗争,也有理论斗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世界革命方针之争,并不能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归结为一批反对派,一伙外国间谍内奸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斗争。
托洛茨基1923年秋发动的围绕“新方针”的争论,是一场规模甚大的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1928~1929年布哈林等反对“非常措施”的斗争,是反对在国内和党内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的斗争,可惜都遭到了失败。
1921年俄共十大曾经通过实行“工人民主”的决定,决定用选举制取代任命制,用工人民主制取代民主集中制。然而,与此同时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其第七条还规定中央委员会可以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连列宁也认为,这是一条反民主的决定,因为中央委员会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它自身无权开除中央委员。不过这一条后来成了斯大林在党内频繁使用的杀手锏。斯大林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把各种反对派逐个击败,获得最终的胜利,从而建立了他个人的一统天下,个人极权。本书对这一过程做了详细的描绘和评析。1920年代党内斗争的结局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发展:
1.党内不再有反对派,不再有不同的声音了。领袖由多人的集体变成一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了。从1929年底斯大林50大寿起,对他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减,斯大林完成了由人变神的过程。
2.党内的监督被消除了。斯大林借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之机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能够发挥客观公正的监督作用,在党内斗争中频繁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只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以多压少。到1930年代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取消,于是党的会议上只能听到清一色的欢呼声、万岁声。
3.斯大林模式的三个基本点: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重工业化,为大规模镇压制造根据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被堵死了,苏联经济走上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
关于苏联文化有两项以往的苏联史书很少涉及。一个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个文化领域的极左派别,它否定传统文化,要在“空白地”上制造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思潮在1920年代的苏联影响极大,对中国也有影响,其历史教训不应当被遗忘。二是书报检查制度。本书在苏联史的著作中首次详细记叙了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书报检查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极力予以谴责的制度,这种制度扼杀人的创造性,在文化领域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由于这是一个并不光彩的政策,所以长期以来苏联当局矢口否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宣称这一制度只存在于西方国家,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才公开承认其在苏联的存在,并予以废止。本世纪以来俄国公布了大量有关书报检查制度的档案文件,本书依据这些解密档案,对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做了详细的记叙。这样,在苏联1920年代的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由于主要领导人曾长期流亡西方,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也由于历史的惯性的作用以及青年作家的努力,1920年代的文化呈现各种流派林立、各种风格并存的生动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控制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消极现象,连当时的文化“总督”卢那察尔斯基也深受其害。书报检查制度的逐步加强为1930年代及以后年代对文化的全面控制,实施文化专制主义以及对文化人的镇压准备了条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存在70多年间的三次改革中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另两次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20年代的苏联处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按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走下去有可能走向市场经济,可惜到1920年代末这条路被打断了,走上了高度集中并且逐步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不归路。
从主观原因来说,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根本上说,那时的领导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经济,即使主张运用市场机制的布哈林也认为最终目标还是计划经济,利用价值规律是为了最后消灭价值规律,其他领导人就更不必说了。在苏联这样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人的认识往往决定国家发展的走向,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而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选择领导人的。
本书竭力揭示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它的运行机制和积极作用,同时探寻其不足之处,它夭折的原因。本书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揭示了1920 年代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政治体制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改革,使得经济体制得不到政治体制的有效保护,能够促使经济发展的措施处处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和阻碍,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蓬勃发展,这是新经济政策最后被打发去“见鬼”的根本原因。
实习编辑 阮 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