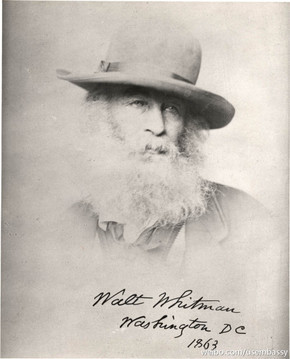夏日报道
不再穿越,这片百里香地毯
被迂回绕过。
一道空档线
从石南丛里透出。
在风的刈幅中,无物。
再一次,遇到一些
零散的词,如
防冲乱石,杂草,时间。
策兰的这首诗,收入他于1959年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中。如从风格而言,该诗在他的中后期诗中,属于“素描写生”一类。在1960年里为电台准备介绍曼德尔斯塔姆的节目时,策兰再一次表达了诗是“事实化的语言”的诗观,称“诗是存在的素描,诗人靠这些素描生存”。
当然,策兰所说的“素描”,并不那么简单,这体现了他在《死亡赋格》之后,在德国战后的语境中对诗的重新考量。在对巴黎福林科尔书店问卷的回答(1958)中他曾这样说:
德国诗歌当前的趋向和法国诗歌很不相同。尽管它的传统还存在,但它被记忆中的那些最不祥的事件和增长的问题所缠绕,它不再以那种许多人似乎都期待听到的语言讲话。它的语言已变得更清醒,更事实化了。它不信任“美丽”。它试图更为真实。如果我可以从视觉领域多色调的表象中找一个词来比拟其现状,它就是一种“更灰色”的语言;这种语言,甚至在它想以这种方式确立自己的“音乐性”的时候,也和那种处于恐怖的境地却还要多少继续弄出“悦耳的音调”的写作毫无共同之处。
这种语言,尽管有其不可剥夺的表达上的复杂性,它要达成的是精确。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它命名,它确认,它试图测度被给予的和可能的领域。①
《夏日报道》正是这样一首诗,“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它命名,它确认,它试图测度被给予的和可能的领域”。连它的题目,也是一种“更事实化的语言”。
策兰的这种诗学转变首先引起了巴赫曼的注意,在1960年2月法兰克福的讲座中,她这样谈到策兰近期的诗:“隐喻完全消失了,词句卸下了它的每一层伪饰和遮掩,不再有词要转向旁的词,不再有词使旁的词迷醉。在令人痛心的转变之后,在对词和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最严苛的考证之后,新的定义产生了”。②
的确,在诗歌对自身的拷问和修正中,“新的定义产生了”。不过,对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和理解。评论家君特·布吕克尔在1959年10月11日柏林的《每日镜报》上发表的对《语言栅栏》的评论文章《作为图像构成的诗歌》,就对策兰的诗包括这首《夏日报道》作了令策兰本人十分惊讶和愤怒的评价。在同月17日给巴赫曼的信中,策兰专门附上了这篇文章,并想听到巴赫曼的意见。以下为布吕克尔文章中与《夏日报道》有关的一段话:
即使在策兰将自然元素引入的时候,也不是自然诗意义上的抒情唤起。在《夏日报道》里,百里香草地也没有散发出醉人的气息,它是无味的——而这个词对这些诗歌都有效。策兰的诗歌大多都是由图像构成的。它们缺乏实体的可感性,即使通过音乐性来弥补也无济于事。虽然,这个作者喜欢用音乐的形式来写作:比如名噪一时的《罂粟与记忆》中的《死亡赋格》,或者在前面提到的诗集里的《紧缩》……在这些诗歌中,几乎没有什么乐音发展到可以承载意义的作用。③
在策兰后来给巴赫曼的信中,他没有提及布吕克尔对《夏日报道》的贬损,因为比起对《死亡赋格》的贬损,这已是次要的了(“《死亡赋格》对我来说至少也是:一篇墓志铭和一座坟墓”“布吕克尔这种人所写的,都是对坟墓的亵渎”“我的母亲也只有这座墓”——策兰1959年11月12日致巴赫曼)。但是,它会在策兰那里激起反响的。这类无视诗的进展、一味要求“散发醉人气息”的传统美学要求,也会使他自己更加坚决地在如他自己所说的“远艺术”的路上走下去。对此,我在《喉头爆破音》一文中也谈到了:“正是因为尼采所说的那种‘人性了,太人性了’,因而策兰在后来会朝向‘无人’”。④他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干脆就叫《无人玫瑰》。
策兰的这种努力,在很多意义上,也就是“去人性化”、摆脱西方人文美学传统、重返语言的源头的努力。这种诗学努力,体现在他后期的那些以“无机物的语言”、地质学、矿物学的语言写下的诗中(“以地质学的质料向灵魂发出探询”),也体现在他以风景和自然事物为“素描”对象的诗中。不过,在这些看上去是“风景素描”的诗中,也出现了“解体”的迹象,以下是收在1970年出版的诗集《逼迫之光》中的一首诗:
不再有半棵树,这里
在这斜坡的高处,
没有
发表见解的
百里香。
边界雪和它的
气味,那探听着
界桩和它的
路标的阴影,
宣告它们
死亡。
即使是风景,也被“死亡大师”所收割。它留下的,只是“视听的残余”,意义的虚无(“在风的刈幅中,无物”)。人类面对被他们自己的文化所强行索取的自然,已无所安慰,除了发明另一种语言——一种“去人性化”的、“无味”的语言。
我想,策兰后期诗歌的意义,也正在这里。这种努力,对他和我们来说,也几乎就是一种救赎。他的许多后期诗作,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以下是他的《逼迫之光》中的另一首诗:
什么也没有
只有孤单的孩子
在喉咙里带着
虚弱、荒凉的母亲气息,
如树——如漆黑的——
桤木——被选择,
无味。
这首短诗,看似很“简单”,或者说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单纯,但那却是一个“晚期”的诗人所能够看到的景象——“什么也没有/只有……”,诗人采用了这种句式,因为这就是世界留给他的一切。
而那孩子,也只能是“孤单的孩子”(策兰诗中常写到“孤儿”,他本人在父母惨死后就是一个孤儿)。这是被上帝抛弃的孩子,但也是一个一直被诗人携带到今天的孩子,不然他不会出现在这首诗里。 而那孩子,“什么也没有”,除了“在喉咙里带着/虚弱、荒凉的母亲气息”。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读过到如此感人、直达人性黑暗本源的诗句(这说明“去人性化”或许正是人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那涌上喉咙的母亲气息,是“虚弱、荒凉”的,但正是它在维系着我们生命的记忆。
耐人寻味的还在于后面:这个孤单的孩子“如树”,接着是更为确切的定位“如漆黑的桤木”。在长诗《港口》里,策兰曾歌咏过故乡的白桤木和蓝越桔,而在这首诗里,“桤木”的树干变黑了——“如漆黑的桤木”,这是全诗中色调最深的一笔。这才真正显现出生命的质感。
而他/它站出来,“被选择,/无味”。被谁选择?被大自然?被“奥斯维辛”?被一首诗?被那无形的、更高的意志?
这样的“被选择”,似乎总是带着一种献祭的意味。
而最后的“无味”(duftlos/scentless)更是“耐人寻味”。这不是一棵芳香的、“美丽的”、用来取悦于人类,或是用来“抒发悲情”的树。它“无味”。它在一切阐释之外。它认命于自身的“无味”,坚持自身的“无味”。它的“无味”,即是它的本性。它的“无味”,还包含了一种断然的拒绝!
“无味”,就这样成为这首诗最后的发音。
因为这个“无味”,这首诗还可视为对布吕克尔的一个正式的回答。(这里附带说一句,布吕克尔在后来出评论集时,没有将他的那篇文章收入。)
也正是以这样的诗,策兰顶住了“美的诗”、“抒情的诗”这类陈腐吁求,坚持实践一种“远艺术”的艺术。对此,还是阿多诺说得好:“在抛开有机生命的最后残余之际,策兰在完成波德莱尔的任务,按照本雅明的说法,那就是写诗无需一种韵味”。⑤
现在我们看清了,策兰的这些诗,是一种幸存之诗,也是一种清算之诗、还原之诗、朝向源头之诗。它清算被滥用的语言。它抛开一切装饰和文化上的因袭。它拒绝变得“有味”——这就像阿多诺在谈贝多芬的“晚期风格”时所说:“贝多芬禁止哭泣——既使是歌德也不行”。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次拥有了诗歌,就像乔治·斯坦纳在谈论最后“身首异处”的俄耳甫斯时所说:“伟大的嘴仍在歌唱”。
注释:
①Paul Celan:Collected Prose,Translated by Rosemarie Waldrop,Carcanet Press,2003.
②转引自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108页,梁晶晶译,倾向出版社,台北,2009。
③巴赫曼、策兰通信集《心的岁月》,芮虎、王家新译(其部分中译见《世界文学》2009年第5期、《中西诗歌》2012年第3期,全译将在年内出版)。
④“去人性化”(或“去人类性”)为西班牙著名艺术批评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艺术的去人性化》(1925)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后被运用到文学、诗歌批评的领域。其实,我们在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中,也都感到了某种类似于“去人性化”所呈现的境界。乔治·斯坦纳就认为在一切伟大艺术中都包含了某种“去人性化”的“奥秘”,“它引领我们回到我们未曾到过的家”(见《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⑤T·H·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slated by.C.Lenhardt,p444,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