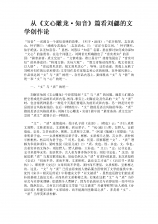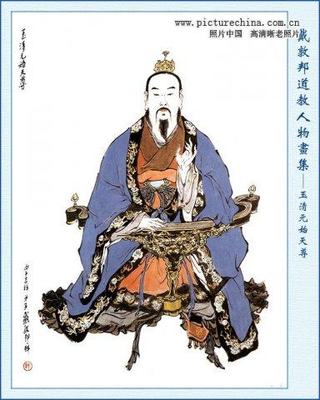古代有关孝道的论述极多,古人有关重视孝道的论述
与事例也极多。在早期的儒家经典小,对孝道的论述是比
较朴实而可行的,如孔子所说的:“父在,观其志;父投,
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①<论语。学而>“生,事之以 札,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孟子所说的: “世俗所谓不 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奔
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
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
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①《孟子。离娄下》就是在 两干多年之后的今天,孔子和孟子的这些言论,也仍然是
正确而应当加以提倡的。
可是,自汉代“使天下诵降经》”④以来,长期以来
国家对天下士民的要求都是“孝梯力田”,在不少人的心目
中,甚至认为“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
为”。 ④!从晋代的晋元帝、晋武帝亲注《孝经》以来,历代
帝王亲自注解、讲说《孝经》者比比皆是。懒lJ是在唐代,
科举制度是以明经科为首,明经科又以《孝经》为首。庸
玄宗更是两注《孝经》颁行天下,命令普天之下必须家藏
《孝经》而诵读之,还亲自书写《孝经序》立于国学,以至
于臣下李齐古等四十余人在上表中称:“《孝经》者,天经
地义之极,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经之上,为百行之本。”一
直到涪代,顺治、雍正二帝还在亲自主持注释《孝经》,颁
行天下。由于历代统治者是如此地重视,甚至可以说是过
度地加以重视.而和万事万物一样,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必
然出现错误,甚至于走向荒谬。最典型的例证,一类是见
于行动的.如东汉的向拥。据《后汉书·独行·向糊传》载,
当此公官居朝中侍中的重位时,张角军起,上下震动,纷
纷议论退兵之计,向初“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
兴兵,但遗格于河上北向读《孝经》,碱自当消灭。中常侍
张让谗颧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
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第二类是只有议论的,如元人陈
继儒,此公在为沈易的《孝经夯训》所作的《序》中说:
“余尝观六朝高人名士,祟信《孝经》,或以殉葬,或以荐
灵,病考诵之枫愈,斗考诵之辆解,火考诵之辆止,盖
《孝经》之不可思议如是。若使家诵户读,童而习之,白首
而不已焉,上非此无以举,下非此无以学,孝感所至,能
令酸泉出,异草生,大泵同乳,乌鹊同巢,盗贼驰,兵过
而不敢过孝于乡。”所以会有这类过度而出现的荒谬,除了
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出于对孝道的崇敬而出现的一些有明显
夸饰的故事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统治集团中一些人
别有用心地进行歪曲而加以利用,从而也就造成了在有关
孝道的论述之中出现了苦干的不实、不妥、不应当、不正
确的种种糟粕。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类:
将对父母的孝加以强化,纳入了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 族权,成为了著名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理论基 础和组成部分。
将原本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互敬互爱、相辅相成的互
动关系加以正面地强调,甚至走向极端。本来,在《左传· 隐公三年>中讲的著名的“六顺”是“君义、臣忠;父慈, 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在的L1己·礼运》中讲 的著名的“十义”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梯;夫义, 如听;长惠.劝顺;君仁,臣忠.十考谓之人义。”一直到 了南北朝时,著名学者额之推在《额氏家训》中还明确指 出: “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 顺*”可是后来的有关说教却愈来愈片面,只讲于孝而不讲 父慈,进一步就更是走向极端.出现了著名的“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父要于亡,子不得不亡”的一系列主张。
与上述情况相仿,就是不再强调晚辈对长辈的诤谏,
即我们在前面曾经引述过的《孝经·谅诤章第十五》中明确 地指出过的:“故当不义,了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 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厂而 是一味强调愚孝,不但不能诊谏,而且还要“子为父隐, 臣为君隐”。
片面强调宗法制度下的父传子继的重要件,以无儿子

传宗接代为大不孝,这就是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并由此而推衍为不娶要为大不孝、妻子无生 育为大不孝、生女儿不生儿子为大不孝,从而为歧视虐待 妇女、男子三妻四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将在孔孟学说和《孝经》论述中原本是比较朴实可行 的孝道言行逐渐加以复杂化和制度化,要求子孙要以极为 复杂的繁文绳节去尽章,甚至在父母死后要用一整套几乎 是不近情理、不顾人道地去尽孝,例如古时最常见的“三 年不丧”的那一整套规定,就是古代很多真心的孝子也是 很难做到的,在今天当然更是不值一提了。
应当指出,上述的这些东西严格说来都是有其政治目 的的,其主要目的就是将人皆有之的孝心都与忠君联系起 来,将原本是对于对孝道的要求更进一步地移于对封建帝 王的忠君意识上去。例如,宣扬“父要子亡,子不得不 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君要臣死p臣不得不死”;宣扬 “子为父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臣为君隐”。所以,对 于这一类糟粕,我们是很容易加以区别并加以唾弃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