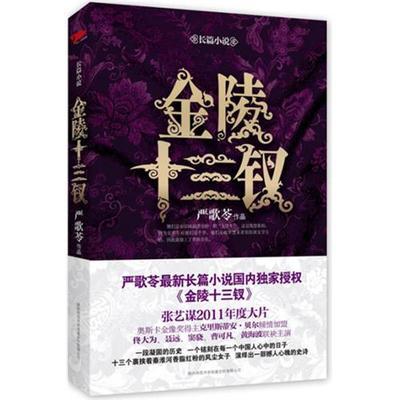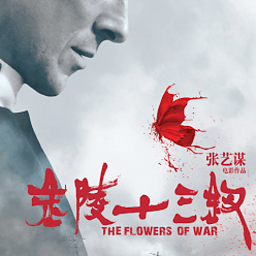13个风尘女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激发起侠义血性,主动代替女学生,直面兽性大发的日军……这是电影《金陵十三钗》讲述的凄绝故事。
历时五年、耗资六亿元打造的张艺谋新作《金陵十三钗》15日全球公映,适逢南京大屠杀74周年纪念日之际,影片和这段民族伤痕一同成为预料之中的焦点。
影片改编自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教会女学生和一群青楼女子以及几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兵的遭遇和命运。《金陵十三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当年犯下滔天罪行的侵略者,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一位美国人参与了营救被困女学生的行动,他的身影,折射着历史的痕迹———南京城陷之际,多位外国人为保护无辜难民、特别是女性的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时年51岁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和德国人约翰·拉贝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他们分别留下的《魏特林日记》和《拉贝日记》成为那段血腥历史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之一。《魏特林日记》中的记载不仅是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创作素材,更是字字见血的控诉。
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多年前的同名中篇小说扩写的作品,虽然二者一脉相承,但严歌苓表示,长篇版从头到尾都是重新创作的,与中篇版和张艺谋的电影剧本完全不同,“剧本的创意已经卖给了人家,不可以在小说中再使用。”严歌苓介绍,小说之所以叫《金陵十三钗》,是因为“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预示着主人公、南京城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我对南京大屠杀始终很关注,在海外每年都有纪念大屠杀的海外华人集会,我经常去参加。每次参加,我都有一种冲动,就是特别想写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但aIhUaU.cOM是真写大屠杀我可能也写不了,我必须创作一个凄美的故事,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后来,我查到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魏特琳日记的一段记录,南京陷落的时候,所有女人在金陵大学避难,日本人要求他们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中驻军,当时就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了,使女学生们没有遭到厄运,这就是故事的萌芽。”
明妮·魏特琳,彼时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南京沦陷期间,学校设立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那些血流成河的日子里,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留下了五十余万字的文字。那些文字里充满了道义和悲悯,记录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并入南京师范大学,现为该校的随园校区。当年按中式建筑风格建起的教室、宿舍,至今维护良好,粉刷如新,仍然发挥着各自作用。校园里的梧桐落尽叶子,铺下一地金黄,在冬日的萧瑟里显得格外斑斓耀眼。
在七十多年前那个血色漫天的冬季,这几栋建筑,以及学校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南京妇孺的救命安身之所。
严歌苓介绍《金陵十三钗》的电影剧本、中篇、长篇的故事主线基本相同,但长篇中加入了最近收集到的大量史实,“日本人当时怎样诱骗中国军队投降,怎样诱骗他们到一些容易被屠杀的地方屠杀他们,士兵们怎样死里逃生……后人研究发现,当时日本人是选了一些中国人处理尸首的,这些‘埋尸队’后来也发生了分裂,出现了汉奸,指认了许多那些被他们救回来的中国士兵。我爸爸的姨夫,当年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医官,负责撤离在南京的7、8个医院,绝大部分伤兵撤走后,他自己却留在了南京,当时只能化装成一个老百姓,藏在美国大使馆,和他同时留下的许多人遭到了汉奸的出卖被杀害,我觉得这个情节是非常重要的,于是都写进了长篇小说里面。”除此之外,长篇版中还加入了后人对13位女子下落寻访的部分。严歌苓说:“我希望借此,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那些为我们献身的人们,即使他们身份低贱,但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们曾作出最伟大的牺牲。”

“我没有自信写作当下的中国”
《金陵十三钗》承袭了严歌苓以往作品“以底层女性为主”的创作特性,对此,她表示,“写男性、写女性对我来说一样,只是相对来讲,我更喜欢写女性,因为女性在社会里较为边缘,较为边缘的人物身上一定有变数,变数大就容易产生戏剧性,而且女性的一生往往是以情感为主,小说、文学,都是情感越丰富的人越好作为主人公,比如,《安娜卡列琳娜》,这么厚一本书写的就是女性的情史,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原因。”而她的作品也大都是1990年以前的中国人,“《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都是写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离开了中国,我对之后中国人的语言、服装、状态都没把握了。人越成熟就越知道天高地厚,我和当代的年轻人完全是两代人,很多想法是两极的,如果不在中国住下来,我没有自信写好他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