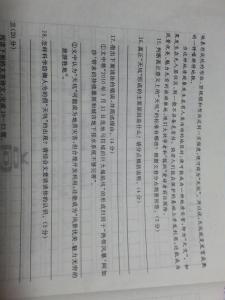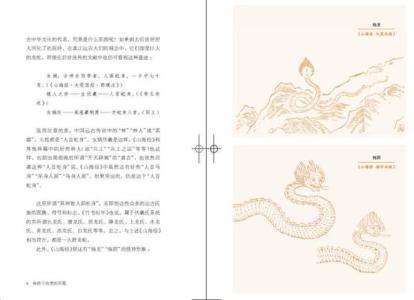我曾经、肯定是个乖女孩,因为十几年前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在《花城》首发的时候,还有引起巨大争议、震撼或者谩骂的时候,我对她一无所知。 我第一次知道林白和她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在王小波的杂文里。那是《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一文,说到北大戴锦华教授盛赞此书,有人反驳,理由是如果戴教授有女儿也不会让她看林白的小说;于是王小波又来反驳此人,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假如谢(晋)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王小波说得有趣,于是我就记住了林白和〈一个人的战争〉。 前几日,我在医院看这本小说,——医院搞体检,排的队太长,我穷极无聊,只有看小说,申明一下,不是我非要在那等嘈杂的环境下故做清高。——我的旁边坐着同龄的同事L,她告诉我她十年前就看了这本书,当时觉得简直难看死了,一是看不懂,二是H。我们就笑了,果然还是少女不宜。 不过现在我已经是个老女人了,所以再没有什么不宜。我喜欢此书,虽然我断不象多米——小说主角,“我”的原型——那么早慧,她在5岁时就做了我现在也不大做的事,对此我还是深表佩服和有一点怀疑。为什么性总成为对抗社会性的切入口?——比如《1984》里就是这样——其实很好理解,社会可以控制一切,总还有性,是最私人最原始也最本能的东西。 围绕《一个人的战争》的种种争议如今早已烟消云散,艺界已经公认此为中国女性自觉意识写作的发端之一和当代“女性小说”、“私人小说”的鼻祖。前几年流行过美女作家,看了附在书中林白的黑白玉照,我看林白还当得起“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绝不含贬义)的大师姐吧。 林白自己说女人写作总是不沿着主线走,想到哪里就游荡到哪里。这个小说有些象自传,也有些象散文,反正都是随性而走的。她写到好几个神神叨叨的女人,比如那个阴间河流边的美丽女人,要买多米29岁那一年的老女人,还有家里满是镜子的独身女人梅琚,和独居深山的可能早已死去的朱凉,甚至包括那些可能真的存在过的女人,北诺、琼、南丹,这些虚构出来的女性在小说中显得丰满独特,眉深目秀;而那些男性人物,包括一般意义上应该是生命中重要角色的男人,比如第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男人,大学时遇到的强暴者,30岁时爱慕过的电影导演,全都是面目模糊,无名无姓,他们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出现的意义只是多米的初夜、多米的偶遇、多米的爱恋,只是多米私人生活中的对应物。——就象俗话所说的,女人爱上的不是男人,而是爱着她自己的那份爱恋。 小说时而以“我”自称,时而以“多米”她称,但不管怎样,都是私人的、指向是向内的,感受是自我的。多米的经历,插队下乡、恢复高考、到电影厂当编剧,这些本来与时代洪流紧紧裹挟的事情,在这个小说里都虚化了,只是多米一切经历与感受的背景杂音。她不是时代的,不是社会的,只是自我的,内闭的。因而也是女性的、私人的。就象林白自己说的——“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我相信每个女人都可以在多米的自恋和自虐中找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