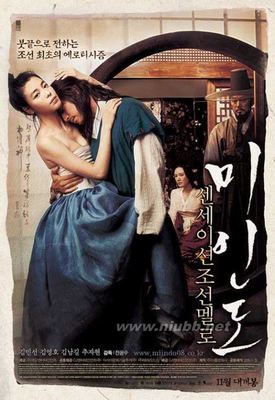[关键词]《桃姐》;音乐;银屏;桃姐;人物形象
纵观所有的艺术形式,音乐最容易传达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细微思绪变化,有助于丰富人物的形象。所谓艺术形式,我国的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在其著作《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论述:美的特点在“形式”、在“节奏”,指向的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全部的艺术都是趋向于音乐状态。[1]宗白华先生这番话就是音乐在传达剧中人物情感以及心理变化的先天优势上的最好证明。
在一部成功的影片中,音乐能够借助于画面,协助观众感受到那些影片所呈现之外的东西,正如《乐记》所言:“凡音已起,由人心生也。人心已动,物使已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2]这里所说的就是由内心感知到的思想。音乐之所以是美的,正是音符之间的变换与交错中迸发出的生命的律动,人的情感波动与这种源于律动的节律,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缕缕思绪随着音乐融入影片之中,在审美的过程中,自己的情感也就发生了迁移。
一、《桃姐》中音乐的清新自然的特质
许鞍华导演的影片《桃姐》荣获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并包揽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殊荣,是一部以剧中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电影。作为一部充满温情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剧中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是源自于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影片将镜头对准了香港的老人院,刘德华饰演的罗杰是一位从小长于大家庭的少爷,由叶德娴饰演家佣桃姐是侍候了李家数十年的老佣人。影片用极其细腻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主仆之间那种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的感人故事。纵观影片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表现的也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细节。
《桃姐》中的音乐看似平淡无奇,细细品味,却有一股清新自然的特质,在淡然的曲调中显示出人物真实的情感,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大文豪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鲍照比较谢灵运与颜延之的诗,认为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而颜诗则是“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两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如同谢灵运的诗一样。《桃姐》中的音乐也如刚出水芙蓉般清新自然可爱,从时下诸多的商业大片中脱颖而出。这种清新的音乐娓娓道来,成功塑造了家佣桃姐和少爷罗杰这两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也能品味出导演许鞍华寄托于其中的意味深远的美学思想。
二、“虚”与“实”
先秦哲学家荀子在其《乐论》中曰:“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1]”这是说艺术既要全面又要简约传达自然生活之美。一方面,所谓“全”,同理于孟子所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另一方面,所谓“粹”,就是要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即“洗尽尘滓,独存孤迥”之意,这样在艺术表现里就有“虚”。由此可见,只有将“虚”与“实”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辩证的统一,才能将影片的艺术完美地呈现出来。纵观影片《桃姐》中的音乐构思,许鞍华与影片音乐创作人借助于旋律的虚实变化,塑造出家佣桃姐和少爷罗杰这两位主人公的内心变化以及人物性格特征,并向观众传达出对于世界观以及艺术观的独到见解。
(一)桃姐的内心变化——折射音乐的“虚”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能将客观的真实通过乐符转化成主观的外在表现。清代画家方士庶曾在其著作《天慵庵随笔》里言:“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这句话的意思是,大抵诸如画家之列的艺术家们的创作,都是源自于大自然的,通过自己的主观创造形成的。音乐家们的创作也是如此,他们的灵感源自于生活,但是音乐旋律在对生活进行反映的同时,还可以勾勒出一种抽象的美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虚化的不确定感。[3]
在影片《桃姐》中,家佣桃姐在刚进入老人院的第一个夜晚,半夜的时候起来方便,却发现老人院的晚上热闹非凡——许多半夜失眠的老人们,要么在院子里溜达散步,要么在打太极拳,还有的老人吵闹着想要离开这里回家去。此时影片中的音乐伴随着桃姐迷茫暗淡的眼神缓缓响起,旋律经由钢琴的分解和弦之处起步,缓慢的旋律逐渐加快,让人听起来觉得仿若轻轻凉风般在耳边吹拂,让观众体味到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而随之融入其中的弦乐与管乐,变化起伏不定,忽强忽弱,很好呈现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虚无的听觉审美效果,响起的旋律忽而感觉近在眼前,近时清晰,远时模糊,虚化的不确定感通过音乐很好呈现出来,借此也将桃姐那种因生活境况的变迁而致使自我身心流离失所的不安感以及对于自己以后生活的忧虑传达给观众。
在老人院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桃姐逐渐适应了这里,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自己的心态也开始变得明朗阳光起来。她开始对老人院里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不再觉得生活是不安和忧虑了,同时,对于康复治疗也不再排斥,而是转为积极接受,一切似乎开始向美好发展,但是生活与戏剧冲突却又总是出人意料、变化无常的。当桃姐在某一天忽然得知老人院里的朋友梅姑去世的消息时,影片在这时响起了同样的旋律,变化起伏不定、忽强忽弱的旋律再次将桃姐内心的思想感情变化折射出来,桃姐的心情开始由开心变得低落,脾气也变得古怪,以致后来常常因为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和罗杰发生矛盾。影片正是通过抽象的旋律将桃姐这种老年人对于死亡的不安与恐惧,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观众。
影片中主人公内心思想感情的变化通过音乐的“虚”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来,看似无心插柳的运用,却能准确地将桃姐内心深处最细微的变化传达给读者。正如著名的美国电影作曲家赫尔曼所说过的,实际上影片中音乐的作用是为观众提供一系列无意识的支持,这种支持是隐性的,并非总是显露在外的,对于观众而言,也并非必要知晓,可是影片中的音乐却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3]恰恰是借助于这一系列无意识的支持,充分将影片中的音乐在塑造人物内心方面“虚”的妙用很好传达出来。(二)罗杰的性格特征——折射音乐的“实”
古人所云的“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与“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共同构成了融会贯通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两种审美的理想,“出水芙蓉”与“错彩镂金”为国人所推崇。《桃姐》中音乐的清新自然一面,体现出了“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学境界,这一类的美学境界倾向于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与人物性格特征传达给观众,华丽的外表并非其追求,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诸多的文人画家的作品也都体现出一种自然真实的审美境界,如东晋的文学家陶渊明、书圣王羲之以及画家顾恺之。
正如影片《桃姐》中的音乐,极好秉承了自然真实的审美美学理想,其创作的基础就是自然、真实,将罗杰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通过音乐的“实”折射出来,并很好传达给观众。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许鞍华导演借助于倒叙这一方式,向观众引出整个故事,影片的镜头定格于即将要远行的罗杰身上,此时响起的背景音乐是一段极为简单的旋律,仔细聆听之后便会发觉其中并无掺杂任何繁复的和弦,乐器的使用也并非是多样化的,但是整段旋律确实悦耳动听,很自然地引导观众思绪的展开,引发观众的深思。影片中的曲作家借用钢琴的独奏方式,将罗杰对桃姐一生的思念之情进行了一番感人至深的勾勒,一段简答之中流露着朴实的旋律,同样将罗杰善良而又不乏真实的性格特征很好传递给观众。虽然桃姐已经离开人世,不在罗杰的身边陪伴,但是她给罗杰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给罗杰传达的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命运,面对生活。[4]正如宋代大文豪苏轼借用奔流的泉水的意象来比喻诗文,所谓诗文的境界就是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所说的“平淡”并非平易浅俗,而是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内蕴,是一种由繁到简的艺术塑造过程。
在影片中当桃姐的身体开始逐渐好转的时候,少爷罗杰陪着她一起在家里翻看一些儿时的旧照片,每张照片都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回忆,两人对当年的故事都记忆犹新,桃姐看着一张张的旧照片陷入了深思,罗杰对于桃姐的爱也是满怀感恩之心。影片在这时缓缓响起了与前一段相同的旋律,还是一样熟悉的钢琴旋律,简约轻淡的音乐,再一次将罗杰真实的个性完美进行了诠释,那是一种常怀感恩之心……借助于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影片充分传达出了罗杰性格中的真与善的一面。[5]
三、诠释人物形象——音乐的“虚”与“实”相生
虚实相生,虚实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特有的命题,从接受美学的范畴来看,虚实相生对艺术家创作和观众欣赏接受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艺术形象塑造更是极其重要,无论是化实为虚、以虚代实,还是虚实相间、虚中见实,虚与实始终是辩证统一的,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要将虚实结合,进行正确的运用,才能进行总结和提升。[6]影片《桃姐》的中音乐,恰恰是利用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于主人公内在思想情感的诠释,成功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桃姐的内心变化所折射音乐的“虚”与罗杰的性格特征中所折射音乐的“实”,将《桃姐》这部影片中主仆之间那种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的形象进行了诠释,成功塑造出了家佣桃姐与少爷罗杰两位人物形象。从中也能够看出,导演许鞍华对中国传统美学有着深刻的体会。
四、结语
虽然音乐并不能像画面那样直接给观众以感官,用具象的方式传达人物的外在特征,但是,恰恰是音乐在其语音上的抽象性特点,令观众脱离画面,直接触动到内心深处,塑造一个属于自我感知的更为深层的人物形象。电影《桃姐》不仅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影片,更是一部完美的音乐盛宴,其中贯穿着美妙的乐声,将故事娓娓道来,借助于古典美学中虚与实的理念,影片中主人公的内心思想感情的变化通过音乐的“虚”与“实”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来,看似无心插柳的运用,却能准确地将桃姐与罗杰的内心深处最细微的变化传达给读者。犹如寒冷冬日里一杯温暖的清茶,淡然却又耐人寻味,深深地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最细微、最敏感的神经,指引了人们回归人性真情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26,34.
[2] 薛永武.中国文论经典流变:《礼记·乐记》的接受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 陈然,曹红波,魏晓兰.浅谈影视音乐的魅力[J].西藏艺术研究,2011(13).
[4] 沈萍萍.那些流水,那些花——电影《桃姐》叙事细节中的情感元素分析[J].大众文艺,2012(12).
[5] 列孚.《桃姐》:简单的深意[J].电影艺术,2012(03).
[6] 胡继华.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6.
[作者简介] 丁翔(1976—),男,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音乐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方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