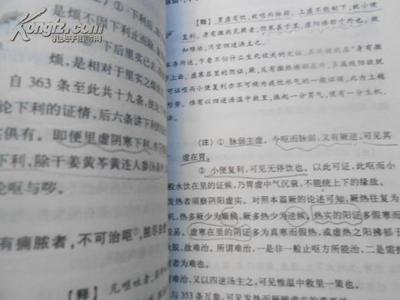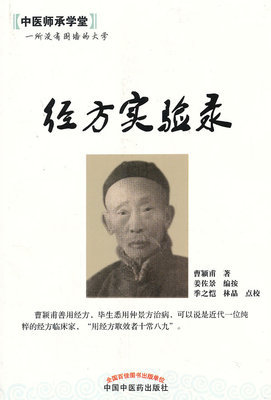经方之旋复代赭汤应用体会.
初识旋复代赭汤是在方剂学中,方歌中有两句是这样的:嗳气不除,心下痞.这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记得第一次用旋复代赭汤是我刚毕业时.一个男性病人,45岁,来诊时嗳气频作,诉:胃中胀痛,嗳气五天,有慢性胃炎病史五年.舌淡,苔白微腻,咯较多清痰.脉象已经记不清了.服旋复代赭汤原方一付,病人来诉已基本痊愈了.过了一个月后,病人因为劳累过度,又出现上述症状.那时因为刚毕业,看到别的医生开处方都开了十八九味药,所以我也试着,开了旋复代赭汤原方加四逆散加平胃散,当初以为开的药多,那治病的面就广,结果病人服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又开了一些西药阿莫西林、吗丁啉等,服了两天,也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第三诊继续服用旋复代赭汤原方一付,病人又好了。
二、一女性病人,38岁,确诊有胃下垂病史近十年,钡餐示:胃已经下垂到盆腔的位置了。诉:嗳气,胃中顶胀痛、隐痛不适,伴返酸,于夜间更明显,反复发作五年。我一听胃下垂,即认为是中气不足,遂用补中益气汤加乌贼骨制酸,两付后一点效果也没有。我遂仔细询问病情。诉:嗳气频作,有少量清痰,舌淡,苔薄白。遂用旋复代赭汤原方加乌贼骨一付明显好转,两付后基本痊愈。过约一周后,病人诉:尚有一点隐痛不适,我想应该扶助脾气了,遂用香砂六君汤加减,结果无效。又改用旋复代赭汤原方加乌贼骨一付,胃已不痛,不再返酸了,后又再服了两付以巩固疗效,至今三月未发。
三、一女性病人,55岁,初次给她看病是因为她头痛、身痛、咳嗽、气紧、吼喘、咯大量清稀泡沫痰14天,已经输了七天的液了,花了六七百块钱,一点效果也没有,经他人介绍到我处服中药。那是典型的外寒内饮,小青龙汤全方加附片50g(先煎30分钟)温阳化饮,结果一付药痊愈了。后来一次出现:头晕、口苦、咽干、心烦喜呕、纳差、头顶热痛,于是用小柴胡汤加丹皮、栀子、钩藤清肝热、祛肝风。二付药基本痊愈。过了约十天病人出现:头晕、前额头痛,嗳气,胃中顶胀痛,纳差,舌淡苔薄黄我用小柴胡汤加白芷治疗,三付后,病人诉:诸症均减,唯觉嗳气、胃顶胀痛未减.我仔细询问:病人平素体质较差,易感冒。嗳气后胃顶胀痛并未减轻,伴咯少量清痰,舌稍红,苔薄黄。并按胃脘部,按之并不痛。我遂断为:心下痞证。加之前有头顶热痛的情况。遂断为寒热互结心下痞证,用半夏泻心汤原方。病人诉:服一剂后,胃顶痛有所好转,但大便偏稀。心下痞证应无误,但出现了稀便,就是黄连、黄芩之故。此时以药测证,再加上最初是外寒内饮,用小表龙加附片治疗。我遂考虑舌稍红,苔薄黄为假热,况嗳气后胃顶胀痛并未减轻,遂排除肝气郁结。遂断为胃虚痰阻的虚痞,用旋复代赭汤原方一付病情减半,三付基本痊愈。
直到治好了这个病人,我才能较灵活的运用旋复代赭汤。
体会;应用旋复代赭汤注意事项:应注意旋复花与代赭石的用量之比,若是痰饮较重则用原方比例较好,若是肝气上逆较重的则加重代赭石的用量。用经方不要固守它的用药之间的比例,要因人、因病情的变化来做适当的调整。
经方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若能够准确的判断病情,不要在经方上做太多的加减,加减的药物多了,反而会影响经方的效果。中医的用药千万不要受西医的影响。
陶某,男,四十八岁,某粮管所副所长。1979年10月5日上午,与邻居因事争执,被木棍击伤头颅、腰背及眼部,当即晕仆。急送某区中心医院急诊。
在该院留观十二日,诊断为“脑挫伤”。出院时腰背及眼外伤渐愈。血压由入院时220/130(mmHg)下降为130/90(mmHg)。其时主症为头晕泛恶剧烈。于出院当日邀余往诊。自诉:击伤伊始,即晕不可支,旬余以来,虽针药迭进,而症无少减,只能静卧,不能稍动躯体,稍稍动作,即觉天旋地转而眩晕欲仆,随即泛恶频频,但不呕吐。一日三餐及饮水服药,均由家属喂饲。余诊得脉象弦滑,舌质舌苔无异常。迳予:
代赭石100g,加水两大碗,煎至一大碗,待温后,以汤匙缓缓喂饮,约四小时左右饮尽。
按:此案眩晕甚而无呕吐,《诊暇录稿》之案,则为呕吐剧烈,神识不清。该书原刊于1927年,以后未见再版,渐成凤毛麟角矣。今照录原文,以资读者印证:
“粤东范君之女,年五龄。自楼窗跌仆下坠,狂妄躁语。与饮饮吐,得食食吐。不能辨识父母,目不交睫。或云肝阳挟痰,或谓温邪痰滞。历五日夜,医药罔效。后经其友绍余往诊,切其脉错乱无定。外既不伤于风寒,内亦无病于痰滞,筋骨肌肉,亦无重伤,实以身躯颠倒重震,浊气反上,清气下陷,姑宗镇胃降浊法治之。
独味煅代赭石五两,煎汤三大碗,每隔十分钟用小匙饮五、六匙。饮未及半,神识大清,呕吐亦止,啜粥一盂,安卧而瘥。”
夫代赭石一物,《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其质重坠,又善镇逆气,降痰涎,止呕吐,通燥结,用之得当,能建奇效。”观此两案,可知其于“脑震荡”、脑挫伤症之眩晕、呕吐卓具殊效,无疑是治疗脑震荡、脑挫伤之首选特效中药。此症之病机,曹氏谓为“浊气在上、清气在下”,而治疗大法取“镇胃降浊”,与通常所用之平肝潜阳、化痰熄风之法不同,迥出意表,可谓匠心独运,实为脑震荡脑挫伤病机之研究开一门径。
《续名医类案》载“许宣治一儿,十岁,从戏台倒跌而下,呕吐苦水,以盆盛之,绿如菜汁。许曰:此胆倒也,胆汁倾尽则死。方为温胆汤加枣仁、代赭石正其胆腑,名为正胆汤,一服吐止。昔曾见此证,不知其治,遂不救。”此案标新立异,名曰“胆倒”,方以温胆为主。然若不加代赭,必无是效,是以此方所得力者,仍属代赭也。设单用代赭一味,不合温胆枣仁,效亦可期,而“胆倒”之论却含深意,盖人体受震之后,清阳下陷,浊阴上潜,胆中浊气循经上达巅顶则眩晕,横逆胃腑则呕恶。治疗后清升浊降,胆气敛藏则诸证自已。此症胆胃同病,用代赭一物而两利之,因而速效。是故岐黄家不当固步自封于套方疲药,自当开拓进取,而求验方达药也。
又按:古人治病每以小方,简药重投,取其纯而力专也,故取效既宏且速。《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一卷载:“唐初许胤宗谓:‘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许氏乃唐初名医,言虽寥寥,意则至深。余三复斯语,铭诸座右。
《30年临证探研实录》
《伤寒论》第161条说:“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汤主之。旋覆代赭汤方:旋覆花三两,人参二两,生姜五两,代赭一两,甘草三两(炙),半夏半升(洗),大枣十二枚(擘)”,从条文中看,旋覆代赭汤为治疗因吐下伤中所致的心下痞硬,噫气不除之证,病机为中阳虚寒,痰阻气逆,症见上腹部痞塞满闷不适,按之紧硬而不痛,频频嗳气,或见呃逆,呕吐,舌苔白腻或厚腻,脉缓或滑。方中代赭石为苦寒重镇之品,在方中的剂量是明显小于其它六味药的,仲景如此用法,意在既用其镇降逆气之功,而又不会伤及已经虚损之中阳。而笔者见不少医者在临证应用此方时,代赭石与其它药的用量比例与原方相去甚远,并多是大于其它药量,所以想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旋覆代赭汤方中旋覆花咸温,主下气消痰,降气行水;代赭石“味苦寒”(《本经》),能“镇逆气,降痰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除哕噫而泄郁烦;半夏、生姜辛温,和胃降逆化痰;人参、大枣、甘草甘温,补中益气,和而用之,扶脾胃之虚而止虚逆。全方标本兼治,虚实并调,镇降逆气而不伤胃,益气和中又不助痰,实乃“承领上下之圣方”(清?6?1罗东逸《古今名医方论》)。
旋覆代赭汤证为伤寒误治,病机关键在于中阳虚寒,痰饮内聚,胃气上逆。此证之“噫气”为胃虚气逆,属于虚证,正如清代医家邵仙根在评吴坤安《伤寒指掌卷三?6?1伤寒变症》中所谓:“中阳虚弱,寒气入胃,寒挟胃气上逆,升而不降,气从喉出有声,为噫气也”;此证之“心下痞硬”亦因胃气虚弱,邪气逆结所致,与此“心下痞硬”同病机者还可见于“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的桂枝人参汤证,和“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的生姜泻心汤证,以及“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热结,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的甘草泻心汤证等。
仲景经方,谨守病机,药量配比,法度谨严,所以,对于中焦脾胃虚寒所致之心下痞硬,噫气不除之证,方中代赭石的用量应当谨遵经方理法,不宜过大。这是因为,一则代赭石为苦寒之品,对于中阳虚寒,饮聚气逆之虚证,应用时不仅要配伍多味益脾和胃之药,而更重要的是用量要小,处处考虑顾护中气、宣化胃阳,降逆消痰而不伤正;二则旋覆代赭汤证病位在中焦,药物作用的靶点亦在中焦,应用代赭石也应考虑此药应在中焦取效,而赭石为重坠之品,如用量过大则会药过病所,直趋下焦,不能发挥其降脾胃之逆气以还归于中焦之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琦在《经方应用》中也强调:“仲景原方中赭石为剂量最小的一味药,是生姜的五分之一,是旋复花、甘草的三分之一,是参的二分之一”,并记载了一则医话:“刘渡舟老师带实习时,有一同学给病人开了一张‘旋覆代赭汤’,可是服后并不见效,仍是心下痞闷,打呃不止。复诊时刘老师把前方的生姜3片改为15克,代赭石30克减至6克,余无加减,增生姜剂量是欲散饮气之痞,减赭石剂量是令其镇逆于中焦,而不至偏走下焦,符合制方精神,所以服后顿效”,可见刘渡舟老师是深喑仲景用赭石之奥秘的。
笔者曾主用旋覆代赭汤治疗一患者赵某,女,71岁,上腹部满闷不舒伴嗳气频作2月余,2009-11-2初诊。患者素体虚弱,有糖尿病、高血压病、慢性胃炎病史。2个月前,因生气而初感脘腹胀满不适,继之嗳气连连,声音低沉,愈发加重,还伴咽喉部一阵阵憋阻难受,频清喉咙,在某医院诊为胃炎、神经官能症,多方治疗不效,几欲失去治疗信心。刻诊:精神差,脘腹胀满按之不痛,咽部不适伴梗塞感,乏力,焦虑不安,纳差,口不苦、不渴,二便调,舌质淡暗嫩,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白腻水滑,脉沉缓。辨证为太阴病兼气郁,痰饮。方拟旋覆代赭汤合半夏厚朴汤加味:旋覆花(包煎)、炙甘草各18g,代赭石10g,法半夏、厚朴各30g,茯苓、生姜各45g,人参、苏梗、苏叶各12g,大枣9枚(擘)。4剂,水煎,日3夜1服。上方服后,患者脘腹胀满不适明显减轻,嗳气次数逐渐减少,咽干不适伴梗塞感基本消失,已现难得的笑容,治疗信心大增,后守方加减又服8剂,诸症基本消失,还不时有上腹部轻度痞满,又用附子理中丸续服2周。该案中阳素虚,又加之情志郁结,木横侮土,致胃失和降,气逆痰阻,乃中阳虚损,气逆痰阻的虚实夹杂之证,病机重点在于中阳虚损,故在应用旋覆代赭汤时,代赭石的用量就不宜重,在降胃镇冲的同时不伤已经虚损的中阳,所以疗效很好。
旋覆代赭汤运用四例探讨 “旋覆代赭汤”这张方子我在临床上用的很少,所以缺乏体会。最近运用了三例,加上两年前的一例共为四例,现录医案如下,和大家一起探讨。
1、老年男性,82岁,食管癌。消瘦貌,营养不良,进食梗噎、呕吐,舌红无苔。如果现在的话我会用“炙甘草汤”增进营养,留人治病。那时我用了陈皮竹茹汤合沙参、麦冬之属滋阴益胃,伍剂后毫无寸效。又在此方上加旋覆花10克,代赭石30克,没用半夏,家属代述5剂后症状好转,能进食,可惜没有坚持诊治。
2、女性,51岁,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隐痛,稍胀,嗳气,恶心,咽中如有物阻,便秘。初用解郁汤,服用一月胃部症状消失,便秘好转,唯咽部症状无好转,且吞咽时感胸骨后隐隐作痛。原方加旋覆花10克,代赭石10克,党参10克,继服5剂,咽部症状及胸骨后疼痛明显好转。
3、女性,56岁,慢性浅表性胃炎。上腹胀 ,有气嗳不出,咽部有异物感,大便正常。初服解郁汤25剂,胀好转,气减少,但咽部症状无好转,颈部似缠绕了硬物,常不禁伸手去拉衣领。予旋覆代赭汤合半夏厚朴汤(旋覆花、代赭石各10克),五剂后症状明显缓解,仍在服用中。
4、女性,44岁,胆汁返流性胃炎。去年因双下肢不明性疼痛,闭经、便秘而在黄师处诊治,予温经汤后痛止、经来、便通。此次胃中灼痛不适,嗳气不畅,咽中不适,发出咕咕响声。初用小建中汤未效,后用解郁汤仍不效。再用四逆散合栀子豉汤,灼痛好转,仍有上腹部痞胀不适,嗳气,咽部症状无缓解。据其此次经来腹痛、面部泛出较多黑斑,更用当归芍药散,仍无效。最后用旋覆代赭汤原方(旋覆花、代赭石各10克)5剂,嘱患者若不效,仍请黄师处就诊。不料此方有效,自服20剂后好转停药。
旋覆代赭汤治疗“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故胃气虚弱,心下痞硬,噫气不除是应用本方的着眼点。原文“噫气”可视作嗳气,呃逆,呕吐,咳嗽等,即气机上冲的表现。《经方100首》把运用本方的指征拓展为“痰多而粘,两胁胀痛,咽间有异物感,咯之不易、吐之不尽,咳喘,腹中有气,自下上冲等”。其中载有“朱进忠治一女,呃逆频作20多天,吃饭时好转,咽喉不利……投以此方加陈皮,4剂愈”,以及用此方治疗梅核气的验案。
本案四例中三例有痞胀、嗳气、及咽部症状,一例食管梗阻症状。除第4例用原方外,其余3例都在原方的基础上合用了本方而取效。故临证见痞胀,嗳气,咽部主诉突出,这三种症状并存时,可能有运用本方的机会较多,特别是用了其他方法治疗效果不佳时。对于妇人“梅核气”,如半夏厚朴汤疗效不佳时,也应想到尝试应用本方。此方是否能缓解食管痉挛,促进胃肠蠕动,值得进一步探讨。
用旋复代赭汤的经验
仲景旋复代赭汤出于《伤寒论》,原治“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主治:胃气虚弱,痰浊内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功用:降气化痰,益气和胃。后世用治胃气虚寒之反胃,呕吐涎沫,以及中焦虚痞而善嗳气者。
晚清民初沪上名医金子久先生(公元1870~1921年),浙江桐乡(原德清)县大麻人。擅长调理脾胃,注重气机升降,对旋复代赭汤尤为推崇,将该方治疗范围有所扩充,娴熟运用于急、重、疑难诸症,经验独到,值得重视。
胸痹案:泻久累肾,肾为胃关,胃津肾液枯耗,脾升胃降失宣。中脘格拒,懊恼莫状,冲阳上冒,肢厥目瞑,浊阴中聚,二旬不纳谷矣。胃乏砥柱,木气上逆,时有嗳气频升。左关脉象细弦,右关脉至散弱。气分结郁,营液生竭,通阳不易,救阴亦难,姑仿仲景胃虚木乘例治,参入辛温扶阳,甘凉生津。
薤白、瓜蒌皮、仙半夏、麦冬、别直参、炙甘草、桂枝、白芍、旋复花(绢包)、代赭石、橘红、熟于术、炒黑干姜。
按:左脉细弦,右脉散弱,正如《金匮要略》“阳微阴弦”谓之胸痹的脉象。而此病见症,以“胃乏砥柱,木气上逆”为主,金氏十分强调脾胃的气机枢纽作用,故在“通阳不易,救阴亦难”之际,主张“仿仲景胃虚木乘例治”。徐灵胎曰:“古圣凡一病,必有一主方。”金氏认为胃虚木乘主方,即为旋复代赭汤。故药用旋复代赭降肺气,平肝逆,别直参、甘草扶中气,合姜半夏开痞,生姜易干姜,加强温中之力,并桂枝、白芍建中,冀升降复常,气化流通,胸阳痹阻自通,胃津肾阴渐充,辨标本缓急,察源流本末,组方至妙,可称深得仲师奥旨。
呕吐案:高年素耐烦劳,真元气液暗耗,近因挟食损中,胃失下行,脘满懊恼,莫可名状,呕吐频频,黑水带苦,大便六日始得更衣,所下式微,积垢尚留,脉象左弦右滑,重而按之,均见柔软。舌质根光,中带燥刺,腑阳不通,脏阴有亏,浊痰蟠聚,肝木偏旺,治当和肝养胃,通腑宣浊。
西洋参、仙半夏、白芍、橘红、川郁金、石决明、瓜蒌皮、茯苓、旋复花、芽谷、代赭石、代代花。
按:本案土虚在先,“肝木偏旺”,土虚木乘之势更甚,症见“脘满懊恼,莫可名状”,“呕吐频频,黑水带苦”,大便少行。所见诸症,均相似于现今胃肠动力功能障碍中的胃气应降而不降,气机上逆类型。治以旋复代赭相配,扭转“胃、食道”、“幽门、胃、十二指肠”返流的趋势,配合二陈、瓜蒌皮化痞降痰以泄浊,增白芍、决明、郁金、代代花柔肝泄肝以和肝,代赭石、瓜蒌兼有通腑功能。用药面面俱到,符合胃宜降、宜润、宜和、宜清、宜泄诸特征,深合叶天士“胃宜降则和”之旨。
反胃案:阳被阴噎,气不化湿。左脉弦大,右部滑紧,朝食暮吐,完谷不化,真阳孱弱,无以输运脾胃,当益火以消阴翳。
东洋参、枳壳炒冬术、广皮、代赭石、旋复花、丁香炒白芍、?桂、戍腹粮、黑干姜、制淡川附、吴萸、姜半夏。
按:本案朝食暮吐,完谷不化,当属反胃证。《圣济总录·呕吐门》说:“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故本案以附子理中汤合吴萸、丁香、肉桂之类,益火之源,以温运脾阳。李东垣说:“脾胃之寒热虚实,宜燥、宜润,应当详辨,至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本方以旋复花旋转逆气,由代赭石重镇,并领东洋参下行,安其逆气,配半夏消痞降逆,以白芍泄肝,戍腹粮取浊者下行之义,金氏每用于反胃、呕吐。调理升降,独具匠心,法似对证,药也中肯,对临诊应有参考意义。
肝胃阴虚案:血液虚少,肝失涵养,木气冲激,乘犯胃土,生机日钝,气津日耗,灌溉失资,经络空虚,遍体为之酸楚,步履为之欠利,而中焦气聚似痞,时或呕吐,舌质光绛,咽干口渴,脉象关弦尺软,左右皆然,叠进甘凉濡润之法,诸恙略觉见轻,届当草木黄落,气液安能振作,所以病样难期退舍,务使潜心,方能却病,否则恐多反复,调治之道,仍仿仲景胃虚木乘,旋复代赭汤主之,再参甘凉和胃生津之法。
西洋参、霍山石斛、旋复花、代赭石、化陈皮、丹参、江西术、戍腹粮、仙半夏、南枣。
按:旋复代赭汤以旋复花为君,代赭石为臣,人参、半夏、生姜、炙草四药合大枣为佐使,组方后性味偏温,后世用治胃气虚寒诸证。然金氏运用本方,并不囿于胃气虚寒证,胃阴不足导致胃虚木乘恒用之,本案即其例也。其间人参用法,颇具匠心,元气大虚者用别直参;气虚稍缓者投吉林参须(或党参);中虚寒甚者以东洋参替人参,肝胃阴虚火旺者,则以西洋参代人参,补气生津清火;阴虚液燥甚者,如本案则“仍仿仲景胃虚火乘,旋复代赭汤主之,再参甘凉和胃生津之法”,如霍山石斛,也可用麦冬、沙参之类。经过金氏变通发挥,旋复代赭汤已不仅适用于胃气虚寒诸症,并能在胃津不足时发挥作用,扩大了治疗范围。
中风脱绝案:左脉乍弦乍动,右脉忽散忽聚,目视直,鼻煽动,危险之形已见,脱绝之势在即,无限之假邪,蔓延不已;有限之真气,持守无多。入于阴则形寒,出于阳则形热,阴阳即是营卫,营卫附于经络,营卫既不循序,经络势必窒碍,身为之痛,骨为之楚,素有之痞攻于中,新积之滞夺于下,腑气益通,脏气益虚,升降更为窒碍,阴阳更难继续,设或寒热继续,便有呼吸垂危,法用龙牡救逆,藉以两固营卫,而胃被肝扰,仍以旋复代赭以镇之,气被浊蒙,当用郁金、菖蒲以开之。
橘红络、濂珠粉、吉林参、龙骨、牡蛎、石决明、旋复、代赭、桂枝、白芍、炙草、郁金、石菖蒲、姜夏。
按:本案为急危重证,“无限之假邪,蔓延不已;有限之真气,持守无多”,“脱绝之势在即”,如何处理这类危重急症?金氏强调升降阴阳四字,案称:“阴阳即是营卫”,“法以龙牡救逆,藉以两固营卫”,而升降窒碍,则因“胃被肝扰,仍以旋复代赭以镇之,气被浊蒙,当用郁金、菖蒲以开之。”该降不降的胃气,宜旋复代赭以镇之;该升不升的清气,用菖蒲、郁金以开之。运用药对调节升降,提纲挈领,切中病机。本案运用的旋复代赭汤,强调旋复代赭药对的重要性,尤宜深究原委,考旋复花咸温,行水下气,具有旋转之力,使上逆之气转为下行,故为君。代赭石味苦质重。经旋复花扭转的上升逆气,复归下降后,再由代赭石重镇,并领人参下行,安其逆气,补益中气,以抵御肝气的乘侮,二药配对,一转一镇,相得益彰,金氏运用旋复代赭药对经验,值得重视。
本文所举5例均为重证、难证、急证。旋复花、代赭石、人参(西洋参)、半夏每方俱用,而姜、枣、甘草则各有取舍,盖病不同,温热寒凉,各有相宜,纵观5方,看病的确,用药的当,议论明快,立方熨贴,洵属可存可师。姑录之,供同道细玩旨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