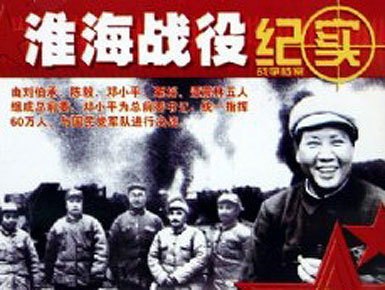蒋介石去收复徐州的时候,李宗仁始终在芜湖防备武汉的东征军。接到蒋介石的电召,他急忙赶到南京,看一看这位总司令现在是什么状态。
“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蒋介石一见面就对李宗仁说,“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李宗仁吃了一惊:“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介石回答:“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李宗仁依然劝他:“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
蒋介石仍旧坚持下野:“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一番谈话下来,李宗仁还是没能说服蒋介石,只得暂且离去。
其实蒋介石内心也不甘就这样离开。但此时北洋、武汉两面夹攻,如果不辞职,凭着那些从徐州惨败归来的部队,根本没把握击退敌手,必须有李宗仁的帮忙。
可是李宗仁这时候会不会真心帮忙?
他方才的话,更多是在试探李宗仁的态度。见他似乎无意让自己下台,看来可以指望这个人。
蒋介石于是正式向李宗仁提出:“出兵帮助御敌”。
他万万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却变了腔调:“对汉宜先礼后兵”。
武汉决意要赶走蒋介石的时候,还要跟他们讲“礼”,这分明是不想帮蒋介石解围。
在蒋介石提出下野的那一刻,身为下属的李宗仁,出于本能和礼节,都自然要竭力劝阻。可是当他能够独自冷静思索的时候,就不能不发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他可能借着武汉的压力,趁势推倒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

蒋介石可以无视武汉国民政府,在南京以下犯上,别的人为什么不能效仿,难道他李宗仁只能永远屈居蒋某人之下?
他按捺不住想要一试,毕竟冲天的雄心已经掩藏了太久。
在老家桂林的公馆大门两边,李宗仁用石刻书写了八个大字:“天下皆春,山河永固。”
那时的他,刚刚取得广西统治大权,根基未稳,却已经胸怀天下河山。
曾经的李宗仁也自甘平庸。幼年的时候,被母亲问长大想做什么,他还只能说要做个养鸭人,因为这个行当看上去比种田容易。
但是几经周折,他终归还是走进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大门,面前是军人生涯的不归路。
这时的他依然胸无大志。
小学堂的总办是日后的护国功臣蔡锷,年轻潇洒,意气飞扬。经常在学生面前故意让自己的坐骑先跑出十几步,然后他再疾步追赶,最后纵身跃马而上。引得众人惊羡,包括李宗仁。
可是羡慕归羡慕,少年李宗仁根本不敢想要做蔡锷那样的“飞将军”。他自己的志向也仍然不过是当一个中尉或上尉就可以了。
到后来他还参与了广西人掀起的学潮,把英姿勃发但不是本地人的蔡锷赶走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李宗仁跑回老家躲避。父亲告诉他:“学未成而空言救国,妄也”。所以他连革命军也不参加,老老实实读书直到毕业。
可是他终究有天生的军人禀赋,陆军小学时就成绩突出,加上训练不怕苦,身体强壮,人送绰号“李猛仔”。
因为太优秀,一遇到事情,同学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辛亥那年,桂林巡防营兵变反对革命,赞同革命的陆军小学学生不得不在深夜转移,敌情不明之下,大家齐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
尽管之后的他对革命不怎么积极,但到了讨伐袁世凯称帝时,连父亲也终于看出“国事若此,儿辈虽欲安居井里,岂可得乎,汝其速行。”
李宗仁这才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彻底投身军旅。
从1916到1926,十年之内,他作战身先士卒,两度负伤。绰号从“李猛仔”升级成“李铁牛”,官职也一路飙升。
还在他做营长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江湖先生。给他看相之后,立刻预言“鹏程万里,前途无疆”。
李宗仁也确实有领导者的气度。他平素在部属面前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让人觉得平庸。但是他为人宽厚,总是用心倾听别人的想法,很有容人的气量,恃才傲物的白崇禧也大半生在他的麾下效力。“刘备能使反对他的人为其所用,”他晚年的时候说道,“有这样的胸襟,才能用得了诸葛亮。”
他不止待人宽宏,做事也讲究公平,不问亲疏。军阀混战时期,枪支是最紧要的财富,但是为了让部队吃饱饭,他可以从自己亲信人马中拿出一百来条枪卖掉,给所有部下换来军饷。
他治理地方不搞苛捐杂税,统辖广西玉林的时候,除了定好的官税,百姓再不用多交一文。
李宗仁也很懂乱世的权谋,当初广西群雄并起,他以一支弱小的力量,在各路武装中间虚虚实实,左右逢源,直到羽翼丰满,时机成熟,才断然出手,给对手致命打击,使自己一举成名。
这些成功的阅历,还有北伐以后桂系部队一天天壮大,成为蒋介石不能不倚靠的力量,都让李宗仁感觉自己有机会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胜出。
其实在徐州战役之前,李宗仁就已经背着蒋介石,为自己能有更好的前程,偷偷开始活动。
还在4月的时候,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蒋介石劝他一起反共,汪精卫却并不情愿。其中缘故除了政见不同,很可能也有私人恩怨。毕竟在一年前,是蒋介石搞出的中山舰事件,让汪精卫离开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出走海外。
李宗仁自认为看出汪精卫的心思,他更知道汪精卫这次归国,就是要重新做国民党领袖。而且全党上下似乎人人赞成,连蒋介石也不表示反对。
如果汪精卫坐定了头把交椅,李宗仁这个时候走近他,总没什么坏处。
于是他主动告诉汪精卫,只要同意清除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可以请其下野。”
李宗仁等原本只不过是广西的地方“诸侯”,假如不是参加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桂系绝对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可是在功成名就的时刻,对蒋介石这位总司令,李宗仁却越来越不满意。
“我对他的印象一是过于严肃,”北伐还没开始的时候,李宗仁就对白崇禧讲了对蒋介石的看法,“二是劲气内敛,三是狠。”
那时中山舰事件刚刚过去不久,蒋介石正大权独揽,国民党内一时无人能与他争高下。
“‘共患难易,共安乐难’。”李宗仁接着说,“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从人格到能力,蒋介石的缺陷确实很多。
他为人暴躁,多疑,独断,偏袒自己的嫡系,对其他派系的部队不能同等对待。单单这些就足以让许多人都讨厌他。
就连指挥打仗,在李宗仁这样经历过不少战阵的人眼里,蒋介石也算不上多么出色。
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总司令,下野又何妨?
不过4月时的汪精卫势单力孤,不敢只依靠李宗仁一句许诺就冒险,他拒绝了吴稚晖的苦苦挽留,登船奔赴武汉去了。蒋介石只能空叹:“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到了武汉的汪精卫,反过来要征讨蒋介石。李宗仁这时倒还能顾全大局,赶紧派人去武汉,劝说汪精卫他们承认跟南京各占一方的事实,先分路北伐,等到会师北京之后,再在党内开会解决分歧。
武汉方面同意了,但是身在江西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却仍然不安分。他现在兼任江西省主席,曾写信拉拢何应钦反蒋。两个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一致对付北洋军阀的时候,朱培德对南京还是一付杀气腾腾的样子。
为了不让朱培德搅局,李宗仁亲自跑去江西湖口见他。
两个人在轮船上见面。朱培德开口就抨击蒋介石擅自在南京成立政府,为人更是“狭隘阴狠,专擅独断”。
“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李宗仁不去争辩蒋介石另立政权的对错,那样只怕不但说服不了对方,还可能把会谈闹僵。
“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辩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他对朱培德说。
实际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
怎样算“彻底解决”,李宗仁自己当时可能也心中无数。但如果需要牺牲蒋介石,他肯定不会在乎。
他的第七军那时正在安徽,如果朱培德动手,首先要打的就是桂系人马。
“如两败俱伤,”李宗仁接着问朱培德,“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
朱培德终于被说服了。李宗仁又答应帮他向蒋介石争取一个第四路军指挥的头衔,虽然那样恨蒋介石,朱培德却也不拒绝从对头那里讨官。
会面之后,朱培德立即去武汉汇报,汪精卫听他讲完李宗仁的态度,说了一句:“由此可见他与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
不来打武汉的主意,说明李宗仁与蒋介石并非铁杆同盟,南京政府也不那么稳固。汪精卫断定:“他们内部已经起了分化的趋势。”
他看得一点不错。从那时开始,经过几个月盘算得失,终于到了此时,李宗仁感觉可以挑战一次蒋介石的权威。
当然也不可太过急切,需要一步步稳妥进行,先不妨从与武汉讲和做起。
在这之前,汪精卫那边曾经致电冯玉祥,宣称准备召集各方国民党中央要员开会,南京方面只要能“尊敬中央”,“个人问题无关轻重”。
冯玉祥急忙响应,将汪精卫的意思转告南京,呼吁“各同志从此合而为一”,“诸兄务请速决”。
李宗仁也加紧动作,给电冯玉祥发去电报,同意南京、武汉尽快合作。
他又直接写信给唐生智,表明心迹说:“只欲武汉反共,予愿已足”。
他又放出话去:“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
这多半是说给蒋介石听的。
既然蒋介石已经是南京方面的最高领导者,如果武汉和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要合并,就不能不考虑他的位置。
中国自古讲一山不容二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蒋介石不会接受与汪精卫分享权力,汪精卫也不可能愿意跟蒋介石平起平坐。
但是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当年的亲信,在国民党内声望很高。与他相比,蒋介石在不少人眼里,仍不过是新崛起的一介武夫。
等到武汉、南京政府一统之后,汪精卫理所当然要做一号人物,蒋介石的地位就必须降级。
蒋介石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结局,不希望这么放弃到手的权力。
从武汉到南京,许多人都认为,两方现在重现联合的唯一阻碍,就是蒋介石本人。
李宗仁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敲打一下蒋介石,提醒他应该想一想退路。
蒋介石也自然清楚李宗仁的用心,被部下这样挑衅,生性孤傲的他无疑会非常忿忿。可是眼下刚刚经历徐州惨败,部队的实力还有他自己的威信都大不如以前。李宗仁那边却毫发未伤,意气扬扬,这个时候还不能得罪此人。
他只好努力忍下一口气,听凭李宗仁指手画脚。
李宗仁的主张也确实让人无法挑错。武汉、南京双方都是国民党内同志,和解天经地义,所以当他要跟汪精卫进一步接触的时候,不管是他自己的桂系,还是蒋介石、何应钦,谁也提不出反对的意见。
就这样在8月8日,南京大员们联名给冯玉祥、汪精卫分别发去电报。电文中极力柔和,竟称自己得知武汉“个人问题无关轻重”承诺之后“喜极而涕”,还承认之前“卤莽从事,过举极多”,实在比不上武汉“诸友”。今后只盼那些“我友”赶快“莅临南京”开会,执掌“大政”。蒋介石这边只求能随北伐大军直捣北方,统一国家。
两份电报的末尾署名中,蒋介石排在属下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之后,仅仅位列第四。
排名下降,权势也自然下滑。但蒋介石还有他能够主导的地方,那就是对徐州的失败追责。
他坚持认为,徐州城下功亏一篑,全因为王天培临战退逃,罪不可恕。
那一战只有蒋介石身临前线,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全在别的地方。追责的时候,他们只能听蒋介石一个人描述战情。
他们好像也没有想过要找王天培对质一下,就匆匆决定了这个将军的人生坠落。
8月8日,王天培接到总司令部电话通知:“来京面商机要”。
“又有什么要事面商,”他的弟弟王天锡表示怀疑,“恐怕是圈套哩!”
王天锡这样担心,倒不全是怕背徐州战败的黑锅。因为王天培还有更严重的背离蒋介石的行为。
眼看南京岌岌可危,王天培转过身偷偷向武汉政府表示归顺。
像他这样做的将领还有陈调元等十二人,这很可能只是他们为自己预留的退路。连汪精卫都怀疑他们“能否真正服从(武汉)中央”,“但他们既想来归,就要与人为善”。
“你真是小器皿”,王天培却全不在意。悄悄跟武汉联络,应该不会有外人知道。整个北伐,包括这次徐州之战,他无时无处不在浴血杀敌,哪里有可以整治的罪过?
他坦然上路,根本不怕南京那些人,他们“敢拿我怎样?”
9日他到了南京,马上就去拜见蒋介石,却被告知:“蒋总司令在总部与日本公使面谈外交要件,着明晨来见。”
他又在第二天10日走进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的会议室,上面要他在这里参加会议。
他刚走进会议室,就只见白崇禧在里面,板着面孔问道:“你知罪吗?”
王天培一下子呆住了,突如其来的的状况让他完全懵了,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崇禧倒是有一堆话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你的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饷等等……”
王天培完全晕头转向,更说不出话来。
“你知罪吗?”白崇禧再喝问一声,下令将王天培扣押。
第二天,总司令部发布公告:“王天培当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致前线无人指挥”,“昏聩至于此极,及至退却”,决定将他“暂在本部守法以观后效”。
处置了王天培,也不能解决蒋介石的难题,武汉那边仍然要把他拉下马来。
虽然8日那天南京高官一齐放低身段,请求武汉谅解。本来答应“个人问题无关轻重”的汪精卫方面,这时却又摆出严厉的架势。
就在王天培被拘押那天,武汉报纸赫然刊出《唐生智讨蒋讨共》的通电。
这份电报文辞严厉,唐生智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猥日反共,投降帝国主义及最后军阀”。
刚骂完蒋介石反共,唐生智却又转过头声称,蒋才是“共乱根源”,“共产党徒之作战,亦即中正之暗示”。
反正在他的言语中,蒋介石怎样都错。对这样的人,大家应该“共起而平乱”。
公开发表这样的声讨檄文,武汉那边对蒋介石的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汪精卫等也在10日这天致电南京,电报开头只提李宗仁的名字,要他“转诸先生”。这分明是将李宗仁视作南京领袖,把蒋介石晾在一边。
电报还宣称:此刻所争“不在个人意气,而在党国前途”,“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不能因为“个人之故”就否认。
这个“个人”当然还是在指蒋介石。
武汉打定主意不能容忍蒋介石存在,“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凉。”这是他们放出的风声。
到了这一步,蒋介石必须在走和留之间,做出出正式的抉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