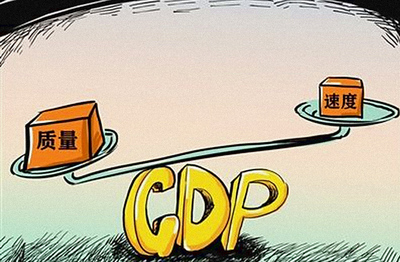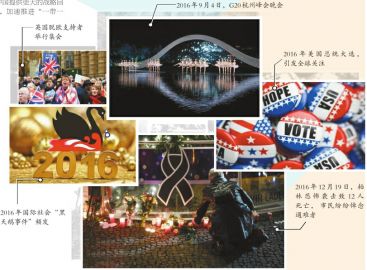公共政策案例5:
“异地高考”的阻碍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不适当地被夸大了。这与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时,对其定位过低,没有具体放到国家层面来做有关。
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2-12-13 浏览:1944
在无数人经历了苦苦等待以后,9月初,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出来了。
这是一个进步。但《意见》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离公众的普遍期待还有不少距离。同时,教育部让各地在今年年底前拿出办法,以及关于异地高考的“三个条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疑问:
各地会不会设置可能比想象中更高的门槛?异地高考会眷顾到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吗? 即使年底前,京、沪等地关于异地高考的办法出来,那么,随迁子女可以在当地高考、录取的那一天,是在什么时候?
在缺乏教育部统筹改革的情况下,异地高考迈出了象征性的第一步,但能走多远? 这些疑问,与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时,对其定位过低,没有具体地放到国家层面来做有关。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容之一,其重要性需进一步认识。
社会结构的重构
2012年中国经济放缓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催生了一个普遍的焦虑:在“崛起”而奔向富强、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如何避免被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问题绊倒?
这个问题,构成了对中国的巨大考验。而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正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从表象上看,异地高考是“随迁子女”在读书、高考上遇到了问题,因此要麻烦教育部、各地方政府来关心。但本质上,它是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为既定的制度设计,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公民权利、国民福利被剥离的后遗症。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这一制度设计隔离了两个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人群。也就是说,户籍制度在理论上,如果可以承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和国民福利,前提是一个社会没有流动性。
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召唤出了巨大的人口流动。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在理论上已经跟不上了,因为很多人已不在原籍,而且以他们的社会经济角色也回不去了,它无法再兑现对一个人分配公民权利和国民福利的承诺。
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种重构,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运动。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某种经济结构,自然地有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
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对各种资源,以及人口在整个社会中的重新划分。它必然改变原来和户籍捆绑在一起的人口分布。
如果要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或至少要维持某种经济水平的话,那么,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口分布的变化,应该反映在关于公民权利、国民福利分配的制度设计上,从而导致对原有户籍制度的改革。否则,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都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第一,在一个城市或已经城市化的地区里,很多非户籍人口在公民权利的行使和国民福利的获得上遭到体制排斥,而只为“市场”所庇护,意味着其在既定体制下难以体验到自己是一个被尊重的公民。
第二,以歧视性的国民不平等待遇,强化了“本地人”、“外地人”的心理对峙。这实际上为群体性的社会冲突埋下隐患。
第三,出于“降低成本”、发挥“比较优势”的考虑,30多年来,“异地务工人员”被视为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用完一批,马上又可以换一批年轻的,而没有在形成了某种规模的经济结构时,把他们也产业工人化、市民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因之整体上处于一个低端的水平,而且很脆弱。
反映改革决心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的描述,当前,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3亿的流动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7%,而他们在流入地生活、就业更加趋于稳定,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
这么一个庞大的人口数字,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而溢出了国家所承诺的公民权利、国民福利的保障体系,成为被排斥的一群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建构现代国家,以“权利”来调整、规范政府和公民关系的过程。现代国家承诺公民的迁徙自由,而中国的发展,恰恰在人口流动的基础上构造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就要求根据公民身份,而不是户籍来确立公民与国家彼此的权利义务。现代国家建构所要获取的政治认同,离不开这一点。
异地高考问题的产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已经严重滞后。
改革,意味着要冲破既得利益格局。异地高考背后是公民权利如何在国家层面兑现,其阻碍一是既定高考体制中的既得利益,二是户籍制度。因此,某种意义上,异地高考的推进是否艰难,反映出了改革的决心。
夸大的阻碍
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因为诉诸于公民的平等教育权,而这一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的义务,首先当然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因此,尽管现阶段解决的思路是由教育部推动各地来做,但由中央各部委来统筹规划,并改革高考体制、户籍制度等,这扇大门仍不应关闭。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仍可在未来某个时候取代现在的思路。
当然,即使异地高考的解决办法不幸地已经是这种样子,在现阶段,也并不意味着就作为不大。
从各地的反应看,到年底前制订办法背后最大的两个担心,第一是城市资源承载力有限,突然有那么多张嘴来“吃”,要在本地读初中、高中,得投入多少钱来建学校、聘请教师?而在以前,“随迁子女”更多地是在民办学校就读,而在高中阶段,大多数已经回原籍了。第二个担心,则是经典的说辞,非户籍人口在当地参加高考、录取,会影响本地学生的利益。 第一个担心,大致对应教育部所说的“城市条件”。作为对地方的一种妥协,《意见》把它表述为“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可能”。而在9月6日,更进一步解释为“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等于完全把要不要某些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而地方基于利益驱动,为随迁子女的教育承担成本,是要求有回报的。
但这是一个多余的担心。放开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并不意味着要当地拿出一堆钱来修学校、聘请教师。这类事情,只要放开教育管制,完全可以由市场解决。在现阶段,很多“异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就基本上是民办学校在解决。而放开异地高考,存在着很多人读高中的需求,一样会有民办学校来做。
第二个担心已经被《意见》考虑到。它的表述是:“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大的省份,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
那就很简单了,放开了异地高考,根据每省实际参加高考人数来招生、录取即可。而在此之前,教育部门还可以根据每省高中阶段的学生数量来预测并给各省分配招生指标。这样,高考人数多的省市,录取名额就多,高考人数少的省份,录取名额就少。这既解决了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录取问题,也没有影响本地利益。
很清楚,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不适当地被夸大了。但只要认识到它对于中国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意义,迈开的步子,就可以加快很多。
“异地高考”,谁的胜利?
201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全国各省市关于“异地高考”的方案或思路赶在“大限”之前出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排斥”、“限制”的思维,贯彻于各地“方案”始终。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3-01-18 浏览:4516
对很多随迁子女家长来说,这是一个经过无数日夜,辗转呼吁等来的结果—只不过,等来的,是沉重的一击。
新年的第一天,一位非京籍家长给《南风窗》记者发来短信:“被抛弃了,绝望之极,像行尸走肉,心被掏空,漫无目的。”
她说,这是随迁子女家长们的普遍感受。
这能体会到。
“特权”胜利了
随迁子女家长们注意到:北上广选择了同一天发布政策,在过渡期和门槛设置上也极为相似,就像约好了一样。
北京的方案规定从2013年开始,符合住所、职业、社保以及子女学籍条件的,可参加中职学校考试录取;2014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大学本科部分的录取则尚未公布放开的时间表。
虽然北京市教委一直在强调接下来的3年仅为“过渡期”,但仅就这份方案而言,其实质无疑是考试权与录取权的割裂,有限度的“开放”只不过是将原有的户籍栅栏异形移位—外来者只能在教育资源的末端寻找机会。
而上海与居住证挂钩的办法早在正式公布之前,就已经被多方预料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就曾向《南风窗》记者表达了担忧:“与居住证挂钩,则意味着异地高考最终会成为拼爹游戏。”最后的方案规定,从2014年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而A证的准入条件之高将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
广东则是“三步走”:2013年起,在广东积分入户的人,其子女“零门槛”参加高考;符合条件的2014年起可参加中高职的考试;2016年起,则可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与北京的未知状态相比,上海和广东看起来都为外来家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要享受平等,必须以跻身一个特定的阶层为前提,用财富和地位为子女的教育权缴纳 “保证金”。可以想见,2016年之后,完成过渡期的北京也会走向这一逻辑。
北京的随迁子女家长们反应很激烈。方案公布第二天,非京籍家长即在网络上发出了《致北京市教委的公开抗议信》,表达自己的愤怒:“教育公平不是考中职、高职的施舍,这是对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侮辱,是对国务院及四部委意见的亵渎。”
他们认为,“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状况相适应,要考虑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考虑的事,“有效平衡京籍学生和非京籍学生的升学利益”只是一句空话,毫无诚意。
同以往一样,非京籍家长对北京市教委和教育部的质询都没有得到回应。北京市教委仅在微博上回复了网友提问,重述了方案的部分内容。
与官方对社会情绪的漠然相比,网络世界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吵则更加激烈。方案的出台,让反对异地高考者似乎更有底气攻击对方,大有北京市教委总算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的阵势。
去年9月以来,非京籍家长到北京市教委约访姜沛民主任,一些本地人士便也加入了陈情队伍,只不过他们的诉求是反对放开,担心最终的政策会倒向另一方。而现在尘埃落定,他们“胜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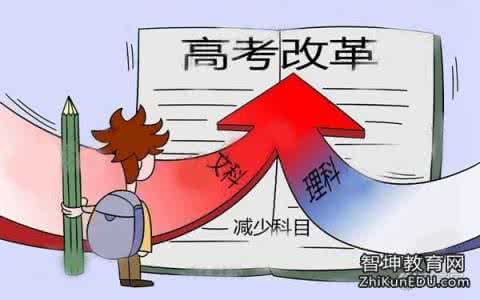
“乡愁”碰到“权利”
争吵仍在继续。
2013年1月3日下午,对方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异闹”代表终于见面了,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交锋,但是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谈还从未有过。某网站邀请了持续为异地高考发声的学者张千帆和自称阿庆的北京本地人进行对话。当天,《南风窗》记者旁听了他们的辩论。
尽管张千帆并不把这次访谈看作 “约辩”,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代表非京籍家长,因为他的孩子不仅有北京户口,而且在让本地人都羡慕嫉妒恨的北大附小读书。阿庆也一再申明从未使用过“异闹”这个歧视性词汇,并且也不完全反对异地高考。但是在各自所属的阵营看来,这就是一次“战斗”。
观点和主张已经没有什么新意。北京是不是高考特区、外来者有没有权利享受教育公平、一个城市的开放应不应该设置边界,在两年多的反复申述中,非京籍家长诉求的宪法依据早已被熟知。高考和户籍制度叠加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也不是新近产生的问题。
而本地人维护自身生存空间的立足点也是基于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在人口、资源和发展上的现实危机。当权利诉求遇到身份认同和城市定位,注定不可能在同一个概念和层面上对话。
张千帆对于这份方案相当失望:“这根本不是方案,只是一个标题。”他认为,“过渡方案”只解决中高职录取,不提异地高考。所谓的“借考”对两边的学生都不公平,名额占
用原籍,考分也无法折算。既然政府不拒绝纳税,为什么要等到他们子女高考的时候,就把他们拒之门外,似乎允许外地人在北京挣钱,成了北京人民的一种施舍。
同税同权、统一录取,实现平等的路径要超越障碍重重的地方性利益,不应该成为教育的国家责任区域化的理由。作为公民来说,这样的诉求再正当不过。而作为外地人,他们就会被贴上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标签。
“你不是以普通市民的心态来考虑这个问题。公平、民主、自由、人权都是非常好的,但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不应过于偏激,在理想状态下去追求这些,甚至妖魔化地追求这些,要在充分尊重他人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不能把问题都推到政府头上。”阿庆批评张千帆不接地气。
在她看来,异地高考之争,更多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政府需要严格地考量这些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和各方的接受度。
她的观点与主政者的政策逻辑如出一辙:城市的容量、大规模高考移民的可能性。“我被别人骂为既得利益代表,虽然我也不知道既得利益是谁给我的,我也没拿过。”阿庆否认存在所谓的北京特权,“如果说享受的话,那就是高企的房价、恶劣的交通、污染的空气、拥挤的生活空间、日益惨烈的职场竞争。”
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本地人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增强、舒适度下降,他们的怨气在异地高考这个现实问题下发泄了出来,把外来者当作对立面。既得利益者的“相对剥夺感”便无限放大。
“我今天斗胆代表京沪本土人,表达我们的心声。你想过北京人也有家乡吗,北京人也有乡愁吗?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着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 阿庆的悲情与慨叹显然不是外来者所能感同身受的。她的乡愁,和异地高考看上去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至少不是同一个问题的同一层面。当“外地人”应被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平等对待的权利,碰到了“本地人”旨在排斥这种权利的“乡愁”时,“对话”注定只是在自说自话。
对于那些被现实折磨的随迁子女家长来说,他们的愁只是:孩子明天要去哪里上学?回到家乡,无异于把孩子弃入一个完全陌生、无法保证正常成长的环境;留下来,则只能报考中高职——因为非京籍身份,他们天生就要比别人多承受苦难,或被迫作出一个不利于人生前景的选择。
未知的答案
在与官方的沟通已经完全失去可能的情况下,非京籍家长们将急切了解反对者真实想法的愿望投射在了阿庆身上。
与张千帆的正式辩论结束之后,几名家长围了上来。与网络上互送“菜刀”和“破鞋”的剑拔弩张相比,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情绪克制。面对语调凌厉而高亢的阿庆,非京籍家长的姿态甚至有些卑微。
当阿庆向众人剖白“骂急了总会有情绪化的发泄”时,一名家长起身向她鞠了一躬,替那些在网络上有过激言辞的家长道歉。也有家长给她端来一杯水,放在桌角,劝和中掺杂着小心的恭维:“网上那些骂的人是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很直率,也从来不骂人,已经做得够好了。”
仿佛政策制定部门的发言人一样,阿庆这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接受着家长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询问。面对无法接受的方案,他们太需要一个解释。
“解决问题要循序渐进,你们总在说2.6亿、2.6亿,谁听到了都会吓死。”阿庆说。一名家长急切地澄清:“2.6亿是全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再说也不是一下子都参加高考。” 阿庆还给家长们支招:“你们应该拿出一个数据,每一年参加高考的外地学生到底有多少。”“这个数据应该是北京市教委来做的,我们只是家长。”有人弱弱地反驳。
有家长请她谈谈对方案的看法以及怎么理解这个政策的合理性和依据,阿庆让他到自己的博客中去看以前写过的文章,并且规劝道:“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尽量少说歧视啊、公平啊,我们听了都很不舒服。”家长中有人附和:“说北京人多吃多占是没有道理的,这都是国家造成的。”
哪部分是最紧迫和容易解决的,“土著”到底在担心什么,1000万外来人口对这个城市的贡献应不应该得到回馈,家长们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抛向阿庆。答案让他们感到两个群体化干戈为玉帛的可能,但同时他们也深知,与本地人的和解不可能带来政策的转机。 在一个猝然而来的应景性政策打碎了憧憬和期待的现实下,这场对话,只是能够稍稍舒解他们心头的郁闷。除此之外,并不会有任何撬动利益格局的实际作用。
在北京,这部分人被称为“异闹”,在上海他们的名字是“蝗虫”。两地的群体冲突有着相同的模式,有“阵地”和“联盟”,也有网络论战和约辩。由高考设限所引发的族群割裂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因开放和包容完成了财富积累,但是当资源迅速集中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的时候,试图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将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
案例研讨
异地高考
研讨要求:
1.学员在认真阅读上述案例材料的基础之上,通过网络等形式,全面理清关于异地高考的背景和政策脉络。
2.请找出异地高考中的利益相关者,并论述他们的政策主张,是否在解决一个不公平的同时制造了另外一个不公平?
3. 地方政府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措施从提议到政策发布几经曲折,特别是高考“最坚硬的骨头”北上广从政策制定到实现不知道走过多少路途,请从公共政策角度评价地方政府先后出台方案措施背后的“辛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