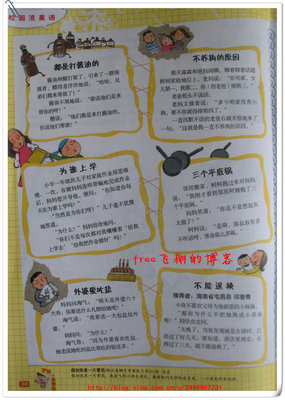现代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编,双月刊。现任主编李小林。1957年7月创刊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刊载长篇作品为主,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多幕话剧、电影文学剧本和长诗;同时,也以相当篇幅发表短篇小说、散文、特写,以及作家论、作品研究、作家创作谈等文章。每期50至60万字,是当代中国首创的大型文学期刊。
收获杂志_《收获》 -概述
《收获》
《收获》在1957年7月24日由巴金和靳以创刊,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杂志,属于中国作协主管。创刊之后,靳以负责具体事务,巴金侧重组稿。1960年5月,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收获》被迫停刊。1964年,《收获》复刊,由上海作协主管,仍为双月刊,由巴金担任主编。1966年5月,《收获》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979年1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收获》再次复刊。
《收获》“发刊词”提及刊载的作品,应符合6个“有利于”的政治标准及呼吁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提倡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今天读来,仍颇有现实意义。
《收获》创刊号上的作品掷地有声。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旗帜的鲁迅,于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记录稿,作为创刊号的开篇,颇有深意。“长篇小说”有作家艾芜的《百炼成钢》、康濯的《水滴石穿》;“剧本”有剧作家老舍的《茶馆》;“童话”有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诗”有著名诗人冰心的《我的秘密》、作家严辰的《苏联行》;“短篇小说”有作家沙汀的《开会》、刘白羽的《我们的早晨》;“电影文学剧本”有作家柯灵的《不夜城》,以及巴金的《和读者谈谈“家”》等大家力作,夺人眼球。
《收获》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纯文学杂志,其视点敏锐,注重观念的更新,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深邃的人文精神,能够传递丰富的文化感悟,深为人们喜爱。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均与《收获》有过亲密合作,如冯骥才的《啊!》《神鞭》、王蒙的《活动变形人》、柳青的《创业史》、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谌容的《人到中年》、陆文夫的《美食家》、叶辛的《磋砣岁月》、苏童的《妻妾成群》、路遥的《人生》、王朔的《动物凶猛》、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余华的《活着》等都在《收获》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收获》是几代人的文学图腾,《收获》是一根标杆,《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装本。
(wwW.aIhUaU.com]收获杂志_《收获》 -大事记
《收获》
1957,“老作家的新收获”
《收获》的创办是由时任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提议的。刘白羽曾回忆,“三十年代的《文学季刊》就卓然不群……我们为什么不恢复这样的刊物,由巴金、靳以来编……我说服了中宣部的领导,但是领导同志说:不一定都在北京,上海从前就是文化中心,可以在那里出,更何况巴金、靳以都在上海。”钟红明还补充说,当时许多老作家都创作了大量作品,发表的刊物却很有限,所以急需这样1个大型的载体;《收获》刊名的原意,即为“老作家的新收获”。
于是,《收获》成为1个独特的文学刊物:中国作协主办,编辑部却设在上海,有上海和北京2个编委会。肖元敏和钟红明介绍,1957年7月24日出版的创刊号由钱君匋先生设计,封面采用厚重的紫红色,字体则不是美术字体,创刊号厚达328页。
创刊号《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是:《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而第一期的带头文章,是未发表过的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和康濯的《水滴石穿》、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
此后,这个时期的《收获》刊发了如《大波》、《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创业史》、《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和《林则徐》、《蔡文姬》等剧本。
1959年11月,主编靳以先生因病去世。1960年5月,《收获》停刊,理由是“三年自然灾害”。不过,钟红明说,自然灾害是1个原因,当时还是《收获》读者的现任主编李小林回忆,她看到纸张都慢慢变黄了,因为纸的质量越来越差。但当时政治上也是很敏感的时期,后来人们评价说当时的《收获》是“统一战线的体现”,这也从另1个角度解释了停刊的原因。
1964,“大毒草”
1964年1月,在大家的呼吁和努力下,《收获》复刊,但换成了由上海作协主管。这个时期发表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大学春秋》等作品。
这段简短的历史却更加惊心动魄。在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巴金发言说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并且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谈话。当时主管上海市宣传的张春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但巴金和靳以开启了《收获》的追求:创建一股百花自由竞放的阵地,多出作品多出人才。即使在压力重重下,在“文革”中,战战兢兢,依然初衷不改。
“《收获》虽然只是一本文学期刊,但她的发展历史也是时代的晴雨表。”肖元敏说,看当时杂志的目录,很多都是直接转载的政论性文章,“杂志都排好了,上面就下一道命令,让你发社论。看目录即可知道当时办杂志的压力和发作品的无奈。没有办法。”
随着周而复在《收获》上发表的《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帮批为“大毒草”,一批在这一时期登上《收获》的作者被打倒,《收获》也没有逃离历史的厄运。1966年“文革”开始,5月,《收获》被迫停刊,编辑部成员都被下放。
1979,“新生”
第3个《收获》从1979年1月开始。但其复刊号的总期数为15期,和“文革”前的14期是首尾相连,而1957年《收获》的那18期《收获》,则不被纳入它的总期数内。
牛bb文章网欢迎您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