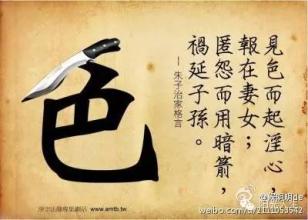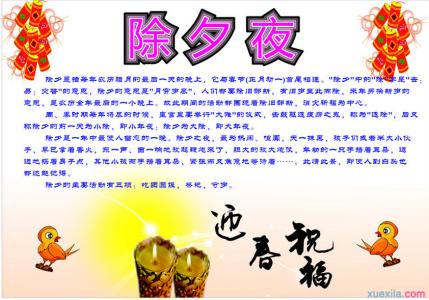难道一定要取一个长书名才行?
取一个夺人眼球的书名仿佛已经成为编辑殚精竭虑的头等大事,对此笔者深有体会。我曾经也出过一本书,当时编辑光取名字就绞尽脑汁想了好几天,在QQ上一会儿给我发一个“《你所抵达的永远是同一个地方》,你觉得怎么样?”一会儿又说:“这个肯定好——《明天我会从哪只鞋子里醒来》。”或者又说:“要不就叫《十七个远方和一个绝望的北京》吧,套用聂鲁达的诗集名《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最后,我坚持用了我原来的书名,只有五个字。结果,果不其然,我的书甫一上市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因此成了朋友们眼中的“过气作家”。
难道就一定要取一个长书名才行吗?书名自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拟定书名是一个作家创作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读者最先阅读到的部分。据说狄更斯在创作《艰难时世》一书前,先后取了《精打细算》《论证》《老顽固》《葛雷英先生的证据》《磨刀石》《二加二等于四》《冷酷的朋友》《锈与尘》《简单算术》《计算问题》《只是数字问题》《葛雷英的哲学》等十二个名字,足见狄更斯对书名的重视。
不过纵观外国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书名起的都显得比较随意,不少世界名著是以主人公的姓名作为书名的,像《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即使是一些离我们比较近的畅销书,书名也很平淡无奇:“哈利·波特”系列、“指环王”三部曲、“冰与火之歌”系列……反例自然是可以找到的,像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只是很少见到国内如此大面积的“标题党”现象。
书名越来越长的“喧哗与躁动”
如果我们继续顺藤摸瓜找下去的话,会发现欧洲人在十九世纪以前也很喜欢用长书名,比如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鲁滨孙漂流记》最初的书名是《在约克出生的海员鲁滨孙·克鲁梭有个不可思议的惊人生涯,他是海难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在俄罗挪克河河口的孤岛上奋勇求生,单独地过了二十八年,终于被海盗船救起的详情记,全文以第一人称叙述》,还有一本由英国人伊弗雷姆·钱伯斯编撰的百科全书,其法语版书名叫做《百科全书,或包含神学、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技术名词术语和事物解说,并对各种器物、制品品类和性状加以描述,以及对各种天然和人工产物的作用的说明,对神学、哲学、数学、医学、考古学等诸学科体系、学派、观点加以解说,并介绍古今学术名著、史籍、词典、报刊、回忆录等之综合词典》。
由此可见,用民族性似乎也解释不通。
取长标题似乎是世界各国的作家都喜闻乐见的一件事,但在别的国家,只是兴之所至偶有为之,而在国内已经欣欣然成为一门显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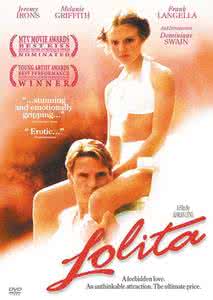
我曾问过一个出版社编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她回答说,长书名可以表达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读者读到这个标题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祝福和鼓励;《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读者会将自己代入进去从而获得共鸣;《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异性恋吗?》,这个问题会引发读者对自己性取向的思考,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这么讲好像也有道理,但是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书名可能没有编辑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一个理想中的读者不会仅仅因为一本书的标题很吸引人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不过问题在于,在高调鼓励冲动消费(买!买!买!)的今天,读者似乎也失去了理性。
如此说来,书名越取越长或许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傲慢与偏见”、“喧哗与躁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