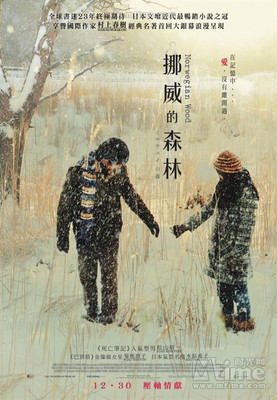我非常喜欢杜爱民的散文。
他对文字的感觉,不锐利但直接,不透明但干净,不游离但思索着,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从阅读他的《非此非彼》开始,我被他编织的一张无形的网左右着,率真而强大的思考,特立而独行的姿态,那种对生活的特有的敏感让我肃然起敬。杜爱民诗人写散文,天生丽质,他的散文散发着忧伤、悲悯的情怀,这是诗人的气质。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好散文是小的,这种小不是内心,也不是细节,更不是结构,它是作家对于生活的细微体察和思考。杜爱民的散文都是来自日常的记忆和经验,是与宏大的文化母体背道而驰的——他的散文几乎没有历史的背景,他的生活史就是他的个人史;几乎没有精神的指向,但他的个人思考足以把根须深植在泥和土里。今天,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与散文其实没有关系的廉价批评,像朴素、平实、唯美、思想、良知、文化、理性等。杜爱民散文好在与这些参照的词与物没有关系,如果要用若干词汇来打量他散文的话,我随手就会写下:身体、生活、人——性,这对于他的散文来说,是种贴心贴肉的疼痛感。
从他的《仁义村》到《刀疤》,这种疼痛是延续的,他始终在一种重力向下的状态。但绝不是回到现实主义,对于散文,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可耻的。散文应该回到生活的现场,它的实验不在书斋和实验室中。从这层意义上讲,杜爱民的散文又是原生的、自觉的,不需要过多的修辞和想像,直接出自生活最为深刻的部分。杜爱民说,他说了任何人都可能说的话,这就是全部的人性,是活着。这也是他文字的真谛所在。
我们习惯了平庸的文本阅读带来的经验,什么是好的——它的标准却建立在少数人规范的教科书上。然后,我再来阅读杜爱民的散文,我惊喜地发现,杜爱民散文的意义在于他没按你期待的那么写,这是他“一贯”的技法,就像他的诗歌《字典》那样是诗人的天真“有邪”,是在疑问中寻找迷宫里的答案,却又在你意想不到中颠覆很多人的日常经验。他散文的意义在于他正构建着属于他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庞杂且不拘一格。从他写的《半坡遗梦》、《藻露堂》、《枫园回忆》、《书院门》等,可见一斑,从中可以读到他整个散文创作的背景,这也是他生活和精神的故乡。杜爱民这样的写作是有野心的,借用他的书名叫做:非此非彼,就是说他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无论哪个方向,目的地都在那里向他问候。还有,最大限度的诚实是他散文写作的态度,而且一本正经。他经常问我,这样写,行吗?由此可见,谦虚和真诚是爱民为文为人之美德。向杜爱民同志学习,学习他的文章和为人,我总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真正强大起来。
日常低处和生活深处的写作
第广龙有一本诗集叫《祖国的高处》,我喜欢隔着这些文字去想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天我忽然见到第广龙,他是我以前在阅读他诗歌里想着的样子。我们握过手就心领神会。他喜欢大口大口地喝酒,喜欢客客气气地跟朋友说话,喜欢倾听另一个人在谈一些和他根本没有关系的事。他喜欢的方式有很多种,他是个真有耐心和认真的人,他有一种热情和宽阔的心境,他就是这样把事情做得好做得彻底的人,我很佩服他。
我的马桶背盖上有他的诗集,还有黑皮的《圣经》,都是我喜欢的书。我坐在马桶上就能把他的诗歌阅读到底,如完厕,洗了手,再读依然满是清新。那种意境让我内心得到平静,简单而从容地进入,好诗清澈见底。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后来我又读了他很多散文,他写工作、下雨、霜花、城市广场和空地;他写桑科草原、拉卜楞寺、七里镇、乌海等。他在日常的低处写生活深处的事情,他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人,给你带来的可能是生活的细处,你不必在乎他文字的完整,他放弃了整体——那些看似完美的东西。他的手、眼睛、耳朵和脚从另一个侧面触及心灵的纵面,可能是时间、色彩、声音、尘土、草木、市井,都是具体的事和物。他不喜欢那些大而无当小而不定的东西,他不光是呈现事物的本真和共性,他还回到散文写作的常识和诚实上来,这样的写作是值得我们信赖和期待的。对事物的发现,只是捕捉最细节处的精彩,这是写好散文最基本的要求。而感官不断将这些发现的东西挖掘下去,是需要审视、力量、判断力、勇气和才情的,需要手术刀一般灵活而准确的思考。这些第广龙都做到了。
他是个生活精细的人,他热爱那些细小的事物,他在自己的文字中体现个体生命应有的尊严,他写他那些石油兄弟的散文更具人性的悲悯情怀。人性——多么耀眼而光辉的词汇,对散文写作而言,它和自由一道构成散文的两翼。无论坐着,还是站着,爬着还是蹲着,他的写作呈现生命的姿态,他辨析来自自己身边一切可能的人和事——那些身份卑微的,毫不引人注意的,或者它细小得令你无法判断方向的声音——这些都是他对生命发自内心的敬畏。我们一起吃饭,我注意到他很少对荤菜动筷,他不是个素食主义者,他是个自然主义者,是个心怀美好理想的人。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让我内心不断地对自己犯疑,他纯粹得让我在世俗面前无地自容。这是他让人服气的地方,我随便就可以看见。我经常感到,他是贴着地面加速飞行的人,他的文字落到实处,就那么清洁透明。我们满世界地找,找啊找,然后我们又发现其实我们要找的东西还在原来的低处,在原来出发的地方。他的散文基本构成了我对“原散文”写作的最初理解。
毫无疑问,散文写作要有原创性和人性,要有独立的品格,要自觉,要有所为和不所为。我在一篇《散文的不完整性写作》中就谈到散文片断性的重要性,我认为只有回到常识中来,回到生活无处不在的现场中去,散文才会有骨头,有血肉,有精气,有身体,有我居于其中。
轻对散文来说是种境界,重对散文来说是种过程。第广龙的散文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他碎片一样的写作无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特别推崇他的散文《我在一个小城的记忆残片》,那是对生命下沉过程的一种逆向而行,它看似轻的部分蜻蜓点水般的掠过我的心灵,但由此带来的那种痛是深刻而切肤的。我忽然想到,贾平凹说散文“重在征服”读者,他谈到了散文的痛处。我的理解是任何形式、结构、修饰、技术等等可能对散文写作都是无效的,散文要做到简而有力,明则清晰,轻而无痕,重则混沌,是不是好方法,就看最终有没有征服读者。
第广龙的散文就是这样征服我们的。
我读吴克敬散文
吴克敬散文给我直接的印象是其思辨和理性,发乎情,又止乎理。他是一个力图摒弃修辞的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说的。我觉得他的散文有这种大东西,大境界,文字不拘一格,很少拘谨和内向,能把内心敞开给人看。我读过他的散文集《日常的智慧》、《真话的难度》等,这种印象尤为深刻。好散文有千百种所谓的标准,我先谈谈我个人的标准。我认为首先是个人气质,这决定作家作品的个性,这是好散文的根本的条件。其次是身体性,我们谈到作品的身体性,这是散文的骨骼,如果散文没有身体,它是软的,是空的,是浮在尘埃中的,即使有再高深的思想内涵,它也无法被支撑起来。身体性不光是肉欲,是吃喝拉撒这些具体的事,它更重要的是日常的,也可能是个人的体温,是活生生的现场和过程。再次,是作品的灵魂,作家作品的灵魂是贴着地面行走的,它不能是高蹈,尽管它应该有自己的千姿百态,但有一点它是不变的,那是作家内心的最大诚实。具备了这三点,我想它应该是好散文。
从我个人喜好来讲,我不太喜欢那些雕琢精致的文字,它光滑得没有棱角,读起来太腻,抹去了很多细小的东西,它虽然平整,但没了形象。吴克敬不是那种文字飞扬的人,他的文字在我看来有些敦实、朴实,不讲手法,这也许是优点,他可以随意地处理题材的多样性,但也从一定上削弱了作品的快感。节制对散文写作也是重要的。一篇文字洋洋洒洒,到头来却不知道它要说什么,这已成为许多散文作家的诟病,把散文越写越长,把散文越写越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到处是隐喻、象征、错位、嫁接、意识流等后现代写作手法,把读者弄得云里雾里,其实他是太低估了读者的阅读识别能力。散文在中国是个古老的体裁,它既需要旧颜换新貌,保持鲜活的东西,又要保留好的传统。从我的阅读经验看来,散文的传统是力求一切从简,去掉多余的脂肪,像《尚书》、《史记》和明清小品等,都是这样的格局。中国艺术讲究淡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写文字不能像注水肉。吴克敬散文没有这些东西。读他的散文像看乡村少女,清水芙蓉,是种健康的生活之美。他的散文多记叙生活感悟,身边事和日常事,在他手里游刃有余,仅仅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这是他与陕西乡土散文的区别。更为了不起的是他写出了《碑说》系列,《青铜器》系列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开阔和丰富起来。
枯燥而干瘦的写作之美
枯燥而干瘦的写作,是文章之美德。这也是我对文化散文的理解。
把历史写成没有目标的旅行,王潇然也算是有力的立言者。历史是人类怀念自己伤痛的口子,重新撕开这些疤痕可以成为重新发现和寻找为什么的过程,这是作家面对自己和大地的巨大诘问的选择。是还是否,大还是小,重还是轻,或者它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曾发生,这只是一个命题,不需要答案。答案对于我们来讲,不是总结,而是不断地延伸和更新。历史不以散文的形式还原真实,史记的可贵之处是它的不可靠性,或者说这就是文史不分的意义。那些士大夫们把忧乐写在纸上,历史就成了一本线装的散文。
作家对历史的思考是为了让它重新站立和鲜活起来。
我对王潇然散文写作的理解大体是他的自我性和旁观者姿态,自我性是作者对事物主观的看法,而旁观者姿态是要求他不加色彩地彰显历史原来的样子。对他来讲,一切是可疑的,一切又是那么清晰。他需要用平静的目光抵达现场的本质,他不是历史的审判者,他只是一个诗人和自己的王。我想他无论从哪个方向深入,拂开尘封的万物,每个人可能只是一个谛听者,但他却成了倾诉者。
这是一种勇气,也是王潇然散文的气度。
他的散文对过去的把握是在场的,那些无数被时间遗忘的细节在他的文字中得到重生,得到滋养,同时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轻,不是还原,不是零碎,不是松弛,而是对自己写作的自信。
他对时间的理解建立在历史的阴影部位,是在对立面的位置不断地树立某种具有个人气质的标杆,这个高度是站在废墟和瓦砾上的坐标。我想,文明的延伸不只是修补,更是重新的构建,无疑,他又是一位匠人,历史的泥瓦工、木工,或者雕刻匠和油漆工。
读他的文字,我又想到那些木雕,愈腐朽和丑陋的根愈是奇异,让人想入非非和记忆深刻。
寻找散文家张怀帆
张怀帆的写作有段时间彻底从我的视野消失了。
我不知道那段时间他具体忙些什么事。但我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叫做河庄坪的小镇,他在那里安静地写诗,工作和睡觉。下班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买菜,接孩子和讨老婆欢心。在没事的时候,他偶尔也给我打电话,客客气气地说些事情,我们谈的那些事竟然与写作没有一点关系。而在延河边的河庄坪上,夜色降临的时候,路灯下走动着清冷的人。深夜常亮的那个窗口,他就是那个守着灯盏写诗的人。他把诗歌蹲在那么小的地方,心境却寂静得像散落在天空的星星,凝固得一动不动。
我读过他写的一篇《病区》的长散文,洋洋洒洒,写得意气风发,不论是诘问还是议论,全是诗人之气。出手不凡,连我也嫉妒了他。果然有写散文的朋友问我,张怀帆是谁呢?我却一时语塞。他是个真诗人——他需要我这样去定义他的身份吗?即便他是无业者、手工业者、农民、知识分子、富翁或者游手好闲者,我觉得都不要紧。他的诗歌,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地理,他诗中体现的孤独感正袭向我们,他想在自己的诗里做个还乡者,在已经沦陷的故乡里,把每个交错的命运还给泥土。
在当下中国无数的乡村中,自然而凋敝的乡土被无数诗人复制为诗歌的时候,它注定会被时间无情地践踏。村庄是个什么样子?——它是人怎样生活的样子。它不只是满目牲畜、庄稼、大地、河流,它还有站立和劳动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的命运,我们理解吗?
这是最近我在《手稿》中读到张怀帆一组散文的感受。
他已经卸下问题的包袱,并开始把人的意义剖开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的散文向我们展示的不同的人命运的遭遇,他们的败落或者凋谢让我们暗自神伤。他要表达的是向生活不断妥协的过程,这是对生活无奈,更是人性的使然。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人根本无法战胜自己。这种残酷就是现实,不管你忧伤也好,悲痛也好,坚韧也好,降服也好,作品存在的意义是揭示最本质的心灵和世界。
这也是我要说的。
作为诗人的张怀帆他已经写出了好散文《活着的光》、《贫穷后来会成为一盏灯》,而读者寻找散文家张怀帆的信心还在加强。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要真的去干一件事情,他一下子会被我们记住。
棉花是另一种花
棉花是另一种花,这毫无疑问。
我与虎平认识,有几年了。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许多朋友,因为他是个让人放心的人。这几年,我读了他很多散文,我以前还给他的书《棉花》写过一个短文,现在读来有些惭愧。朋友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善良让你产生敬意的;另一种是他对你的敬意让你产生善良。虎平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聚在一块最多的地方是茶馆。我是个静不下心来的人,但遇到虎平兄,喝茶便成了和看美丽的服务员一样有耐心的事情,这是他教给我的生活哲理。我多数时候是个务虚者,当我在夸夸其谈地面对只有一个听众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倾听者,这多少对他有些残酷。
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的文字越来越好,让我和他坐在一起时很少谈到散文了。他是个有心之人,他有很多故事——关于自己和别人的,祝愿他把这些生活中最精彩的人生抒写出来。具体地讲,是从《棉花》开始的,他的散文写作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文字中有生命里柔软的部分,这种软对陕西当代散文的传统来讲是种叛离。他的文字有南方潮湿的阴气,少北方硬朗的成分,我认为是好气象。古之成大事者必是北人南相,南人北相之人——鲁迅说的是人。评价散文我想也加上这条标准——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都是好散文。贾平凹的散文是北人南相,于坚的散文是南人北相。他们的散文坚持了地理之中的特色,又拓宽了精神之上的疆域。
近又读了虎平写城市系列散文的片断,很是欣喜。他对自己的心灵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和诘问,他把触角伸展到了生活细密的部分,这是有重量的。题材对散文来讲只是形式,就像棉花一样,它是另一种花,但在虎平的手里便有了温度,有了生生不息的东西。
在我的老家,棉花是家产殷实的象征,意味的是丰收和饱满。我读他的《棉花》一书也有这种感受。我也希望自己像棉花一样成为另一种花。
回到故乡的写作
马召平是位谦谦君子。是我读到《聊斋》时,想像那些书生时的样子,有善良之心和心高之气,女生们肯定喜欢他。我记得多年前我们之间初次交往的情形,他话不多,略带细软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在不多的交谈中,都是谈具体的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那几年里,我或多或少地跟他联系了几次,我们都在繁冗的生活中平静地生活着,有时候还从朋友那里听到他的消息,没什么大事,每个人都这么过着。
时间过得真快,差不多五年吧,我们好像也见过几次面,但他从来没有被人遗忘过。有一天,我偶然在杂志上读到马召平的一组散文,让我着实吃惊,几年不见,文章大变样,满是意气风发了。我记得那时他写他的马家庄的事,他写村里的变迁史和生命的生息死亡,在沉静的叙述中那种力量一下子抓住了我,是如此的快意人心。接下来,我跟他打过一次电话,但我没有急于表达我对他散文的直接感受,我们只谈了些生活中那些零碎的东西。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时间渐渐冲淡了我那时的感受时,他忽然有一天带人转来他新写的一叠散文打印稿,我对他散文的认识又逐渐清晰起来,他是个心怀敬畏之人,还有颗敏感的心,故乡在他纸上层次分明,这在中国不多的个人故乡里有独特的意义。我有时想唐诗里李白的故乡是月亮,陶渊明的故乡是菊花,而他的故乡是什么呢?他没有告诉我。在他的写作里我读到的可能是一条河流,或者是一个大院、那些树和生命生生灭灭的人和牲畜。有的人写作是要回到他生活的故乡去,比如萧伯纳建构的小镇和卡夫卡虚拟的城堡。马召平的写作是要回到哪里的故乡呢?他是在重新返回童年记忆的背景里,是要回到他整个精神的故乡里,那是他个人命运交错的出发地。回到故乡的写作——这个“故乡”可能是你生活的地方,也可能是你的出生地,还可能是你精神的高处。这样有根的写作,不会有浮躁之气,是不断下潜的过程,也许是我们写作正在努力寻找的结果。马召平还喜欢惠特曼和博尔赫斯的作品。惠特曼是底层的草根写作,而博尔赫斯是典型的知识写作,但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的写作都是震撼人类灵魂的写作,它留给人的是生命的思考和疼痛。我拒绝任何给散文贴上标签的写作,但这不意味着个人的写作没有立场,恰恰是有立场的写作,独立于别人的写作,在这个时代更显得珍贵。读马召平的散文,让我想到他纸上孤独的故乡,一个人的影子,他把美好和理想沉浸在他的文字中,他把那些看起来极其平常的事,不加修饰地写出来,并写得开阔,有意味,还有大爱,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是值得我学习和期待的。
回到我跟他交往中,我觉得他在写作上是个有追求的人,有许多想法,他不说出来,但他认真地写出来;许多事情,他总在默默地去做,结果总是让我肃然起敬。我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加深着对他作品和人的认识。
一个人的故乡地理
李敬泽说,祁玉江在散文写作中是个回忆者。我的理解是,他的散文是在不断向后撤退的过程中,他要撤退到生命的出生地和居住地,撤退到他的故乡和童年,撤退到他内心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回忆往大里说,可能始于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救赎动机,而对于回忆者来说救赎的意义大于拯救。
“回”不光是回忆,回乡,回是回到原处和出发地,回可能是永远再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回到哪个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到的地方?这是所有作家要面对的问题,就像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一样。没有人能告诉我,作家就是要回到那个不可能的故乡。
祁玉江的“回乡”之路是艰难的,它的艰难之处在于那个深刻存在的灵魂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而地理意义的故乡已是陌生人的故乡。从这两点来说,“我”在文字中是个不归路上的游子,“我”对于故乡的理解是游离和模糊的,而这种不可靠性多年来一直支撑着他寻找我真正故乡的所在,他只能身体前倾地接近这个虚妄的事实。
这是心灵的一种无奈,但作为呈现于我们时代中心的一种精神立场却是根性的。
当知识分子试图去修补这种伪饰的乡土的时候,祁玉江却慢下来拷问愚昧和贫穷的责任,他的散文不掩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笨拙而善良的想法,他不掩饰自己的悲伤的情怀。当有人还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不能自拔时,他抒写的是一份自己内心的承担,我能做什么,或者说我要做什么。他是一个叙述者,他看到的大地是亲人、树木、杂草、黄土、牲畜,他能写到的就是亲人、树木、杂草、黄土、牲畜,他表达的方式是跟他们拉家常,他的这些美好的情愫弥漫在大地上,他构建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乡地理。
他是用心去写的。用心重新亲历、触摸,用心重新过滤也重新复原。
这个故乡的意义是他自己心灵的,他切片一样剥落下来,掷地有声。他像中国众多的农民一样是有根的,这个根一下子就扎下去,很深。从这个意义来讲,祁玉江的写作是向下的过程,他不是站在散文严格控制的自由中,他很多文字伸展出来的姿态是“有话要说”(李敬泽语),也是带着疑问而来——是为什么而为之。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似是而非的面孔是文人惯用的方式,祁玉江不靠这些手段“征服”读者,因为他为他的读者准备的是一颗坚强而善良的心。
真诚的表达或散文的自然法则
散文有没有自然的法则?我们从建筑学的概念去理解实用主义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建筑的审美作用。审美的功能与实用主义是矛盾的吗?散文写作需要实用主义吗?去其修饰是现代建筑走向自然法则的过程。同样散文的某种禁锢也是不断逃脱这些虚假的表象而走向自己内心和事物本质的过程。修辞的目的是让语言生动起来,而不是让语言模糊而似是而非。非此非彼的可疑在于作者对生活和事物缺少足够的深入和了解,对写作的态度缺乏真诚。
散文的实用主义不是单纯的文以载道,而是做到有话要说和有感而发,做到精确而独到的见解。《天工开物》和《昆虫记》都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但却闪烁着文学思想的光芒。今天的散文所缺乏的正是这些严谨而生动的表达,它一味地沉浸在修辞的表达中,那些陈年烂事,只不过是过江之鲫,鱼目混珠而已。
真诚地表达是作者写作的姿态。这种姿态应该是向下的,向着生活不断地低头,贴地贴身的潜行,而不是对日常事物的俯视和熟视无睹。李宗奇对待散文写作有一颗谦卑的心,他的抒写是掏空一切后,又把心灵袒露给别人看的人。一个向着自己内心奔跑的人,一个忠实于自己生活的人,他怀一种美好的情愫,他随遇而安式的表达从不会强加于他人,他还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倾听者,我想这样的写作是他写给好朋友之间的信札。
今年,他给《小品文选刊》杂志写的专栏文章,我觉得更是我们期待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文字少了很多束缚的东西,他几乎只用白描的手法接近生活的状态,他慢条斯理地记录内心生活的痛感,这种疼痛即使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还是保持节制的表达。我觉得旁观者不是对生活无动于衷,不是对悲情麻木不仁,而是积蓄力量,保持必要的客观和冷静。散文写作如果需要自然的法则,那么这个法则就是诚实的表达。万物在我心,我心属万物,朴素之面,中庸之道,或者自然之事,人文之心,都是散文的自然法则之一。那些假洋鬼子总是扯起所谓散文革命的旗帜躲在众人的后面喊——他们原来是在用汉语的方式学说英文。
我最近重读李宗奇的散文,我觉得他深得生活的精髓,向生活的深处淘得真金,他文字不生涩,不做作,不矫饰,不臃肿,能让人养眼。什么是为文之道?说人话——这是一个作家的素养和对作家的要求,这大概是散文最大的实用主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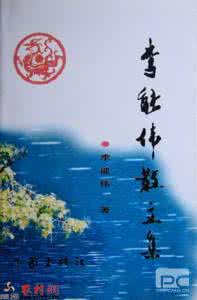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