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毛主席的心情很复杂
本文摘自《统一大业》(郭晨 著;天地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那时候毛泽东正在杭州刘庄检查和诊断病情,进行休养。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泽东内心的复杂感情。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将大陆接到邀请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挫折和损失。
另一种描述或者演绎却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说毛泽东私下为他一辈子的对手举行了一场个人的、别开生面而又十分含蓄的追悼仪式。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这是两位历史巨人难得一见的合影。他们虽是死敌,但某种程度上也惺惺相惜。(历史图片)
据说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幹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悲怆的古词录音只有几分钟长,反复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泽东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词的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个人恩怨、儿女私情的人。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泽东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的沉重告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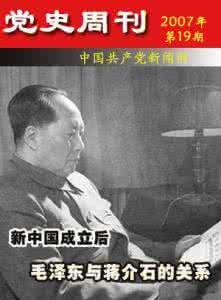
未能见到台湾和大陆统一,大概是毛泽东生平最遗憾的事情了。毛泽东自己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没有解放台湾,为他干的第一件大事留了个不短的尾巴,他的遗憾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从1953年起,毛泽东年年都要到海边,年年都要遥望大海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他愤怒“台独”分子远胜于愤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也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从进北京城之日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的便是台湾问题,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障碍也是台湾问题。他是很想跟老对手一起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在蒋介石先他而去了,他的伤感可想而知。
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前往老家溪口拜别母亲的坟墓。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历史图片)
应算是一代巨人的蒋介石走了,他的身后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评价。紧扣本书主题,我们引用他的毕生政敌毛泽东的独特评价:我和蒋介石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中国要统一,一个是中国要独立。
在不同的时期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1938年,中共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有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称呼蒋介石是“民族领袖”,是“最高统帅”。毛泽东说,国民党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第二个伟大领袖就是蒋介石先生。毛泽东这个评价,不是在公开场合讲的,是在中共中央的中央委员会上讲的,因此不是公开场合的吹捧,应该是比较真诚的。同样是毛泽东,到1945年以“新华社发言人”的身份宣布,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可见,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比较公允。在“第三次国共合作”呼之欲出的时期,蒋介石却撒手而去,以国事为重的毛泽东悼念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正确地评价蒋介石、国民党,对于建立和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至关重要。
蒋介石在1949年大陆失败后来到台湾,在1950年“复总统职”而为草山主人,如同宿命一般,他自黄埔建军至1949年共二十五年,以后统治台湾恰好又是二十五年。他统治全中国那二十五年的历史功绩,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的评价是:“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仍是在大陆创造的高层机构。这种成就不因内战失败而泯灭,假使没有他那段奋斗,中国可能仍是军阀割据,外强干涉。”
应客观地评价蒋介石的功和过。虽然他曾与人民为敌,但他在结束军阀混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方面的历史功绩,难以抹杀。他仍不失为一位影响深远的历史巨人。(历史图片)
蒋介石在统治台湾的几十年中,除了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最大的贡献是他从各个方面均突出一个中国的立场。当然,他所指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但是,海峡两岸在几个重要方面也存在基本共识,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省,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在国际社会只能有一个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台湾不具有“主权”;中国的分裂是暂时的,而统一则是必然的,这是历史潮流,不可违背。
蒋介石有功有过,这里无意对他作出全面评价,但就台湾问题而言,他虽然坚持中国统一,但却对中共提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长久冷漠以对,甚至一概斥之为“统战阴谋”“和平攻势”,认为海峡两岸是“汉贼不两立”,足见他的统一只是要他主宰下的统一,要恢复“中华民国”。
在70年代以后,中美走向和解,正是海峡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契机。因为一来人民要求国家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来美国已难以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重重设障,国共双方都握着这把和平统一的钥匙。但当和平统一的机会真正来临时,蒋介石反而提高了对“中共吞并台湾”的警惕,临死前虽有与中共和谈的愿望,但已经不能操作了,使两岸和平统一又失去一次良机。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缺陷,也给两岸人民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天方夜谭 毛主席支持蒋介石连任
打归打,谈归谈。金门炮战之后,北京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台工作,悄悄地下着和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对周恩来、张治中说:“打炮也好,不打炮也好,都是为了支持蒋介石。我们不能够让美国人把台湾拿去,不管它是单独拿,还是用联合国托管的方法,想把台湾拿去,都不行。”
张治中说:“在美国和台湾领导人的印象里,中国大陆炮击金门,是跟苏联人商量好了的。”
毛泽东摇手说:“没有的事。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和战从来交替无常,一阵猛烈炮击之后,毛泽东又悄悄打出一张和牌。
章士钊被请进中南海,他在毛泽东书房坐下后说:“主席、总理,我借‘避寒’为名,想飞去香港,再次与台湾方面人士接触。请你们告诉我最高与最低条件。”
毛泽东说:“行老,你去香港,给蒋委员长捎去高低两个礼物。低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最低的谈判条件嘛,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诸如互相访问,官方的、私人的、团体的都行,逐步实行通邮、通电、通航。”
周恩来接着说:“最高条件是我方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军队、政府、党组织,经费不足部分也可由中央政府支援,只要求台湾方面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说:“请行老写信与蒋介石联络,劝蒋顶住美国的压力,决不能从金门、马祖撤军。”
心里有底的章士钊高兴地说:“好,我胸中有数了,两张牌看火候灵活打。”
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章士钊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历史图片)
9月29日,显然是接到了章士钊老先生的信,愿意与北京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蒋介石公开表示:台湾将决心固守金门、马祖,“不容为了考虑盟部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急关头,台湾将独力作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知蒋介石这一讲话,即于10月1日发表讲话,声称:“金门、马祖并不是极为重要的,把很多军队驻在这里不是一件好事情。”再次重申:“美国赞成国民党军队从这里撤出。解决台湾海峡的危机应避免使用武力,停火可以提供一个谈判机会。”再次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同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发表讲话:“在中共继续炮击的情况下,根本不能放弃金门、马祖。我政府坚决反对减少外岛驻军,更没有接受停火的义务。”公开对抗艾森豪威尔。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确定对金门、马祖的新的战略,即“打而不登,封而不死”。
此时,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论的话题,已经是:现在我们不拿台湾,可能十年、二十年、四十年都不去拿台湾。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
10月11日夜,毛泽东伏案给周恩来写便信:“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这是给另一边(蒋介石)看的。”
第二天,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对周恩来说:“我还是想明天接见曹聚仁。”
周恩来说:“主席不是说冷他几天吗?我对他10月5日擅自将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的独家新闻卖给《南洋商报》也很生气,我曾要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转告他,我三年之内,不会见他了。”
毛泽东说:“我说冷他几天,也是对他此举不满。但他毕竟是个特殊人物,跟那边有直接关系,还得见他。”
周恩来说:“主席见他后,我要找他谈一次,告诫他,不能以新闻记者的自由态度,来做严肃的对台工作。”
10月13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被“冷”了两天的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一再会见曹聚仁是有背景的。50年代末,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
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持陈诚。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介石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的这一套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美国一直想扶植陈诚,以之取代蒋介石出任台湾“总统”。图为蒋介石与陈诚在会议上。(历史图片)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对曹聚仁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当总统,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
周恩来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看着忙于记录的曹聚仁,毛泽东又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
曹聚仁说:“蒋氏父子对此还是有顾虑的。”
毛泽东说:“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这样,蒋介石的美援会断绝的。”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因为身份的特殊,曹聚仁得以在两岸频繁出入,做国共双方的“代言人”。(历史图片)
曹聚仁关心地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还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过。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总理又两次接见曹聚仁,托他带话给蒋经国。
台北士林官邸,蒋经国进来向父亲请安,并问:“章士钊从香港捎来中共关于和谈的最高最低条件,父亲可曾考虑?”
蒋介石说:“我们不上中共统战诡计的当,管它什么最高最低条件,中常会要通过《粉碎中共和谈阴谋实施计划要点》,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答复!”
蒋经国说:“我看他们也自顾不暇,在跟苏联闹别扭呢。”
蒋介石敏感地问:“跟苏联闹什么别扭?有准确情报吗?”
蒋经国说:“据说赫鲁晓夫想跟中共搞什么联合舰队,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两人大吵了一架。”
蒋介石亢奋地说:“好!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
章士钊从香港回来,坐下后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说:“停止炮击金门,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又叫喊起反共复国,我是空手而归。”
毛泽东说:“我跟赫鲁晓夫吵架,蒋介石以为有什么空子钻,又翘尾巴了。不要紧,既然我们的对台方针已从‘武装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调整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就要有耐心。这壶不开就提那壶。”
章士钊惊讶:“毛先生还有一壶?”
毛泽东笑道:“我有好几壶呢!”
周恩来点破说,程思远先生就要来北京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