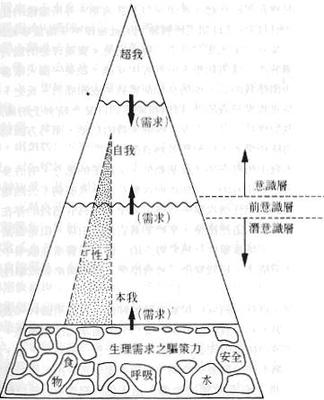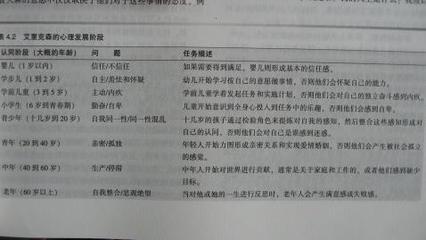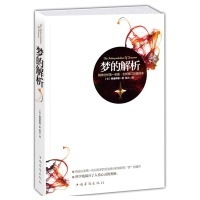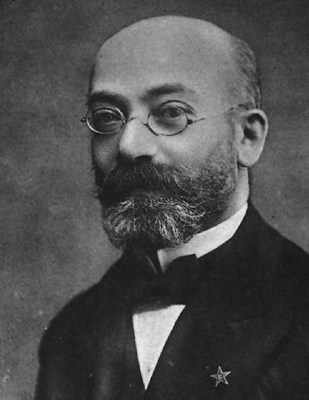和病夫鲁迅一样,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蠕动着的肠胃,可我们平常却不会专门花时间去理会它,真仿佛它从来都不存在。在从三间大学辗转回上海的船上,方鸿渐“博士”对他的未婚妻孙柔嘉女士说,尽管我们有那么多亲人,可我们把一生中用于想念他们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也很难超过数小时(钱钟书《围城》)。肠胃遇到的正是这种待遇。它正好也是我们的亲人。通常只有在它出现了问题时,我们才会在迫不得已之间发现它原来依然还在那里,像一只勤劳的工蜂,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为我们的所有动作,哪怕是吃、喝、嫖、赌、献媚、窃国、贪污、受贿等等提供有力的支撑。在《南腔北调集》里,鲁迅就曾经专门说到过肠胃的长期被忽略和偶尔的被重视,以及这中间合乎人性的原因。有趣的是,肠胃正是鲁迅经常用到的词汇之一,尤其是它的许多变种词汇,早已组成了鲁迅个人语境中的专门词汇;这些词汇在暗中支撑着鲁迅的思维、眼光、语调直到写作。
在此值得当做对比的是诗人海子,他在自杀前半个月以几乎凌乱的句式,天才般地写到了粮食、肠胃和农业。和鲁迅一样,他也给肠胃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
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南刮到北,无视黑暗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春天,十个海子》)
嘴、吃和胃一边联系着我们的人生动作,一边连接着土地和粮食。在海子那里,我们繁复的人生动作经由嘴、吃和胃最终掏空了粮食的五脏六腑,使大地变得虚无、荒凉。毫无疑问,在海子那里,嘴、吃和胃是大地的杀手,是罪恶的器官(或动作)。海子以他的敏感心灵,透见了肠胃和丰收、土地、粮食之间剥夺与被剥夺的残忍关系。很明显,在海子的语境中,肠胃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而在鲁迅那里,却更看重肠胃的原始功能,它表征的无疑是肠胃的现实主义: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容纳和消化食物(粮食)。因此,海子的肠胃中包纳的是土地,尤其是使土地变暗、变得空无荒凉的邪恶力量,是欲望;鲁迅的肠胃中容纳的,则是支撑我们做出各种人间动作的原始力量。如果海子语境的胃如其所愿地被摘除了,大地肯定就安宁了、美好了、纯洁了;如果鲁迅语境的胃不幸被消除了,大地就只有草木、野兽以及它们的自生自灭了,按照鲁迅一贯的话说就是:中国人肯定是要被挤出“世界人”之外了(《热风·杂感三六》)。
让我们先把海子和伦理学的肠胃抛在一边。实际上,从肠胃开始分析中国的现实境遇是鲁迅较常用到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同主义、小康主义曾经嚣然尘上,几千年来却又无不为嘴、吃和肠胃奔忙的国家,鲁迅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肠胃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孤零零的词,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词根出现在鲁迅的语境之中,并由这个词根演变出了许多专门性的派生词汇。在鲁迅那里。肠胃从功能上说,首先是一个基础:正是依靠它,才使人的身体得以生存下去。即使是圣子耶稣当年饿极了,也得不顾身份去偷人家的东西吃,当主人警告说这就是犯法时,他还煞有介事地为自己的肠胃寻找神学理由(《马太福音》)。这当然没有什么可笑,而是“基础”给了每一个凡夫俗子以宿命和大限。即使是圣子也不能例外,只要他还没有三位一体。鲁迅理解这中间的隐秘内涵。在肠胃问题上,如果不说鲁迅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起码也能说他首先就是一个肠胃的现实主义者。基于这一点,我们马上可以说,恰好是肠胃的现实主义给了肠胃这个词根最基本的含义:它指明了这个词根在自我推演、自我膨胀、自我完成过程中的方向和路径。
鲁迅多次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华盖集·忽然想到》)。这里容不得半点诗意,也和所有型号的伦理学暂时无干。它是现实的,也是功利的,带有太多保国保种的焦灼感。而“生存”、“温饱”、“发展”云云,正是肠胃作为词根经过自为运动获得的派生性词汇。它既表明了“基础”的意思,也把鲁迅的肠胃现实主义摆渡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这就是说。在鲁迅那里,肠胃一边连接着简单的保命术,另一边却连接着登龙术。可它又绝不是桥梁。和许多人的意见相反,基础就是基础,从来就不是别的什么!它是生存的必需品。
肠胃也不需要墓志铭,它是活体,始终处在时间的流动之中,它蠕动、收缩、扩张和吸附的节律,就是它自身的时间。更加准确地说,肠胃只有它自己的时间,也只听从它自身时问的号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在忘记它时,它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孜孜不倦地运转的原因。为肠胃虚构一种假想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肠胃的现实主义最内在的要求,也是“基础”最严厉的措辞。诚如保罗·德曼在《作为抹去的自传》里说的:“墓志铭或者自传话语之主要修辞法,是拟人化,是死后的声音之虚构。”鲁迅也说,梦是好的,否则金钱是重要的(《坟·娜拉走后怎样》)。肠胃反对梦想,特别是当肠胃还没有达到它自身的满足的时候——尽管肠胃确实能支撑起我们的梦想。也只有它才能支撑起我们的梦想。肠胃的现实主义最隐蔽的潜台词是:它是代表能量的阳光进入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中转站。而我们说,肠胃的现实主义和它所要求的特殊的时间,使肠胃坚决反对包括拟人在内的所有修辞法。肠胃是活体,鲁迅通过《阿Q正传》、《孤独者》、《伤逝》告诫我们说,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然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始终出现在鲁迅眼前:几千年来,尽管我们的肠胃从未缺席,尽管我们的肠胃一直都在暗中给我们提供力量,可它并没有得到善待,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尊重。种种肠胃的伦理学、政治学给了它过多的伤害,给了它超过它承受能力的众多教义。在极端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以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人肉去敷衍它滑腻的时空。这是肠胃的伦理学对肠胃的现实主义最大的犯罪。一般说来,在肠胃的现实主义肚量的弹性限度内,中国的肠胃以它菩萨般的胸怀原谅了肠胃伦理主义的敌意。它懂得,“肠胃”作为一个横跨亘古的巨大词根(而不仅仅是鲁迅的词根),它的自为运动毕竟还是给肠胃伦理主义的词汇之达成开启了后门,也预支了场地。是的,中国的肠胃现实主义一直有着宽广的襟怀。
时而当忙月,时而打短工的阿Q在生计出现问题时——鲁迅通过《阿Q正传》告诉我们,也告诉了他的时代——照样是要造反的。这是一个草民的肠胃在为自己的基础地位、现实主义寻找尊严。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但以瞪眼和斜视看到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化上的愚民、弱民政策,使得中国人的思想体格处于极度贫弱的状态,也看到了文化自身的机制在对肠胃实施愚民政策,在时时打破肠胃现实主义的内部平衡。“造反”是“肠胃”作为词根派生出的又一词汇。
鲁迅曾经提到了李自成的造反、张献忠的造反。他暗示说,他们造反的目的和阿Q准备革命的宗旨并没有根本差别。一旦李白成、张献忠等人(当然也包括阿Q)得势,他们的秉性使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造就新一轮肠胃现实主义内部的失衡。这都是些有来历的老例了。在这里,通过肠胃和肠胃的现实主义,鲁迅毋宁说出了这样一条真理:肠胃的尊严最终是冒犯不得的,肠胃最终是不可能被愚弄的。肠胃的现实主义有它的独门兵法。肠胃作为词根的派生词汇之一“造反”就是众多独门兵器中最厉害的一种。肠胃一边维系着我们的生存,一边维系着我们的尊严。当肠胃受到了类似于钱钟书所说的那种不公正的待遇时,它就会铤而走险,起义造反。是肠胃最终把人逼上了梁山。是肠胃最终给予了改朝换代的最大助力。毕竟海子那种过于诗意的肠胃伦理主义在庸众们那里,从来就不会有像样儿的市场。
鲁迅碰到的时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时代,人人都面带菜色;无论是肉体上的肠胃还是精神上的肠胃都没有得到善待。在一篇杂文里,鲁迅说到了北京城沿街乞讨的小孩儿。这是肠胃现实主义最动人的华章和最精彩的一幕。鲁迅保证说,从这里我知道了中国的未来。接下来的问题就顺理成章了——鲁迅的潜台词是:我们民族的肠胃早已出现了问题,这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凡智商不等于零的人都不难想见,因为按照某种貌似庄严的口吻,毕竟孩子还是人类和民族的未来。在另一处,鲁迅不无“恶意”地说,我的确是生得早了一些,康有为公车上书时我已经有好几岁了,这真是不幸。为什么会不幸呢?鲁迅却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但他知道终有人会明白这里边的深意。
2 肠胃的伦理主义……
孔夫子的弟子们记录了孔子说过的一句很有趣的话:“割不正不食。”他老人家的意思大概是,如果食物在刀法上显得凌乱、不守规矩、破坏了应有的美感,我们的至圣先师是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下箸的。联系到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说教,这自然可以理解。千百年来,我们的儒生、理学家、卫道士们在板着面孔之际,显然忘记了孔夫子在这么说话时包含着的更多的幽默感,也不愿意在孔夫子身上去寻找他之所以这么说话的原因。顺便说一句,孔夫子的话里边还隐含着一个肠胃上的美学问题,也被众多的孔家门徒给忽略掉了。是啊,在孔子那个年代,美学刚刚草创,割不正就不食,也未免显得太奢侈了。儒生们怎么愿意注意这些有可能给圣人脸上抹黑的鸡毛蒜皮呢?他们从那中间更愿意看到的是格物致知的心性功夫。我们都听说了,只有有病——不管是身体有病还是精神有病的人,才会过分重视吃食的面孔、成色和酸碱度是否与自己的肠胃相匹配。后起的儒生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活生生把孔子的话上升到了象征的高度,并由此开创了肠胃的伦理主义传统。听他们解释说,刀法不正,带出来的实际上是食物的非“礼”;而非礼的事情,我们都愿意相信,老夫子从来都是不会干的。
保罗·蒂利希在《文化神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象征的一般性来源:所谓象征,就是“出自我们今天所说的群体无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出自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一件事物、一个词语、一面旗帜或者不管别的什么东西中承认了自己的存在”。“礼”当然就是儒生们的“存在之家”,自然也是他们肠胃的“存在之家”。具体到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加上一个限定性条件:此处的集体无意识倒正好是儒生集团的有意识——是他们有意识地把意识强行处理成了无意识,最后把它弄成了象征,当做了禁忌,并给予了它伦理主义的板滞面孔。因为千百年来,鲁迅的肠胃现实主义暗示说,小老百姓梦想的从来都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至于割得“正”不“正”,大体上不会有什么讲究;到了民不聊生、易子而食的年头,就更是去他娘了。因此,任何号称无意识的东西几乎从来都是被迫成为的。这里不妨插一句,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失察,使得容格之流的伟大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了先天的残疾。
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已近乎变态;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似乎又在提前呼唤一种精致的新美学。他在吃食上的穷讲究,与其被门徒们上升到象征的高度、肠胃伦理主义的假想位置,不如先在肠胃的现实主义水平上进行一番思维游弋再说。正是在这里,历史谣言家鲁迅敢于断言:孔老二有胃病;而且他还指名道姓地说那是胃扩张,患病的时间大约是在周敬公十年以后(《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这不应该算是瞎把脉,毕竟鲁迅是学过医学的。除此之外,鲁迅还有着强大的理由,这里也一并罗列: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概就无须思索,直接承认那是吃的东西;只有患病的人才一再想到害胃、伤身,搞出了许多有关食物的禁忌(《坟·看镜有感》)。这当然是更加准确的诊断了,因为它建立在病理学和物质经验的双重基础之上。
肠胃的现实主义在这里拥有了足够的批判力量:它面对祖传的肠胃伦理主义时,有着鄙夷、蔑视和挥手之间就将它打发在一边的能力(这暗合了向上崛起的眼神)。在鲁迅看来,古老的、建立在“克己复礼”基石之上的肠胃伦理主义根本不值得再提倡了,它是糟粕,同样也是压在肠胃上的巨大重负之一。正是它,导致了整个民族都患上了广泛的胃下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肠胃的伦理主义一开始就给肠胃虚构了时间段落——王化的、由“礼”规定好了的四平八稳、低眉顺眼的时间。所谓君子不饮“盗泉之水”、不吃“嗟来之食”。这种柔顺的时间彻底摧毁了、取消了肠胃自身的时间。但它保证说,只有在王化的时间段落里,肠胃才能获得它需要的安宁、和平以及满足(大同?小康?)。肠胃现实主义在经过它自身的思辨、运作后,毫不犹豫地打翻了虚构的时间——我们早就知道了,肠胃的尊严最终是不能被冒犯的。
值得考虑的倒是,鲁迅不仅是一个肠胃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伦理主义者。但他不是祖传的伦理主义者,也不是海子那种诗意盎然的伦理主义者。在鲁迅这里,肠胃伦理主义反对诗意,它遵循它的主人对食物的理解方式,并由此去规定对食物的挑选,对食用方式的选择。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天然带出了他对个人、时代、历史、人生和文化的几乎全部理解。由于肠胃作为词根在鲁迅个人语境中的内在含义,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也有了它自己的独特性。简单说来,和鲁迅一贯关心的问题及其表情相一致,他的肠胃伦理主义也具备着痛苦的、口吃的质地。
在小说《孤独者》里,鲁迅描写了一个叫做魏连殳的知识分子。此人早年激进,抱着改造山河、富国强民的大志。残酷的现实生活却让他处处碰壁,几乎是经常性地食不果腹,及至无人理睬。最后他破罐破摔,当上了一个地方小军阀的幕僚,立时境遇大变,身边经常性地聚集了一大堆唯利是图、讨好卖乖之众和海吃大喝之人,其中也不乏那些先前对他的“不理睬”党。但魏连殳最终只是一个孤独者,因为他的真正目的、人生理想根本就不在这里。和孔子的伦理学一样,魏连殳的肠胃也自有它要排斥的“盗泉之水”和“嗟来之食”。不排除魏连殳身上有着被许多论者所标明出来的种种特质和象征意义,但他正好表明了鲁迅牌肠胃伦理主义的实质。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的真正含义毋宁是:在抛开祖传伦理主义对肠胃的时间虚构后,新的伦理主义必须要给肠胃一个全新的、有利于富国强民的,并且是健康的、可靠的时间段落。这个时间段落一定要征得肠胃自身的时间形式的同意。这就是说。肠胃的伦理主义既要尊重肠胃的本己需求,但又绝不为肠胃的原始现实主义牺牲自己的尊严(这在思路上倒有些近似于祖传的肠胃伦理主义了)。它同意《马太福音》说的话:“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也能在抽象的含义上同意《文子》的建议:“外与物化,内不失情。”但它决不同意“割不正不食”。
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的痛苦和口吃就在这里:尽管他特别想找到可靠的时间段落去框架肠胃,但现实境遇不答应;在肠胃现实主义的巨大压力下,他不得已牺牲了自己独有的伦理主义,但伦理主义却又为此痛苦不堪。并由魏连殳明知自己患了绝症也懒得去治疗最终吐血而死来了结痛苦。魏连殳是肠胃现实主义和伦理主义深刻冲突的牺牲品,是炮灰和齑粉。在矛盾双方之间,鲁迅牌肠胃伦理主义实在是很难对它们谁更有理作出准确的判断——这自然就是口吃了。魏连殳的痛苦归根结底是肠胃伦理主义的痛苦,魏连殳的孤独也是肠胃伦理主义的孤独。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鲁迅接受过国民政府一家学术机构的聘请,虽然他从未到场干事,却几乎是直到死都在领取它发放的薪水。联想到鲁迅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猛烈攻击,而他似乎对只领薪水不干事从来也不愿意提起,这中间不正充满着他的肠胃伦理主义的躲闪性吗?该躲闪性和鲁迅肠胃伦理主义的痛苦、口吃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呢?
建立在“礼”上的伦理主义造就了一个四平八稳的胃口、对食物进行广泛挑剔的胃口;建立在鲁迅私人词根之上的伦理主义造就了一个痛苦的胃口,它不断在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来往穿梭、居无定所。谁敢一口咬定哪一种更好,哪一种更糟?为了解决伦理主义本身的痛苦、口吃和它们带来的躲闪性,既然鲁迅早已枪毙了祖传的肠胃伦理主义,那么,他会听从海子的建议,捡起海子那种充满浓郁诗意的伦理主义即干脆把肠胃给摘除吗?对于海子的小儿之见,鲁迅当然会不屑一顾。因为肠胃的现实主义始终给鲁迅提供了这样一个发言的立场:活人只谈活人的肠胃。海子的肠胃在鲁迅那里显然指涉的是死人的肠胃。但鲁迅肯定不愿意知道(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会在他自己的肠胃伦理主义的指引下一条道走到黑的,比如海子,他用伦理学的胃口彻底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胃口。山海关铁轨上被火车砍成两截的身体表明了“彻底取代”带来的悲剧性,而不是躲闪性和口吃;比如伯夷、叔齐,他们同样是用伦理主义的胃口一步步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胃口。只不过他们的步伐更从容、更中庸。有趣的是,在《故事新编》里,鲁迅也写到了伯夷、叔齐。在鲁迅明显的调侃和讥讽的语气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肠胃现实主义和肠胃伦理主义之间忽而搏斗、忽而和平共处的真面孔(《故事新编·采薇》)。鲁迅把这中间的痛苦给掩盖了;联想到不为别人服务却又毫无愧色(?)地领取别人给出的薪水,鲁迅以那样的语调描写伯夷、叔齐,其目的和宗旨不是反而更加欲盖弥彰了吗?
3 肠胃的拿来主义……
肠胃作为词根,无论是在鲁迅那里,还是在传统文化那里,势必和饥饿联系在一起。饥饿是肠胃派生出的又一个值得大写的词汇。肠胃的现实主义正好是建立在饥饿的基础之上的:是饥饿让我们在迫不得已之际开始重视我们的肠胃,肠胃也是通过饥饿这个可怕的中介向人吁请对它的尊重。饥饿迫使肠胃伦理主义高扬的眼光向下看,把目光集中在早已坍塌的肚皮上;饥饿在呼唤建立肠胃自己的伦理学——关于尊重肠胃的伦理学。
饥饿使肠胃自身的时间终于从隐秘的地方浮现在我们眼前,从而和我们的公共时间打成一片。但它的方式却是特别的:它是金色的公共时间幕布上的黑色,是太阳中的黑子,是焦灼的时间。因此,两种不同的时间终于重合了,也迫使人们重视肠胃自身的时间。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最简单的法子把它重新打发回到囊中。但这种漫不经心的方武。往往是要遭到报应的。
肠胃的伦理学一直在为饥饿规定方向和解决的线路而奔忙:吃什么,不吃什么;这样吃,而不是都样吃。所有的肠胃伦理主义都在干着这样的事情。因此,在肠胃的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肠胃的现实主义倾向于马上解决饥饿,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怎样搞到这些东西,也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耗掉这种东西(比如“割”得“正”不“正”就不在考虑之列);伦理主义则倾向于对食物进行再三挑剔,反复研究,以确定下口的方式和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在通常情况下,伦理主义并不在乎饥饿痛苦的叫喊。肠胃伦理主义是天生的硬心肠,因为它本来就是由一群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的肠胃们发明的。
一般来说,肠胃的伦理主义在肠胃的现实主义面前没有不惨败的,无论是鲁迅牌伦理主义还是祖传的伦理主义——为了果腹而背叛自己理想的魏连殳,自然是前者的好例证,被逼良为娼的良家妇女更是后者的蜡制标本。因此,口吃(支吾、犹豫)就是各种肠胃伦理主义的天然特征。毕竟饥饿有着更大的力量,毕竟海子的伦理主义太完美了,以至于无法做到,毕竟祖传的伦理主义太高大了,凡人们注定无法攀缘到那个致命的高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有几个妇人能够终生奉为圭臬?为了解决伦理主义中暗含的口吃,祖传的伦理主义选择了“从权”:为了尊重肠胃。“嗟来之食”、“盗泉之水”也不妨一用。——毕竟像伯夷、叔齐那样彻底的人并不多见。鲁迅将会选择什么方法呢?
我们都知道了,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有着痛苦的一面,也有着强烈的躲闪性。这种痛苦来源于两个方面:从我们专事批发经营辫子、小脚的国粹当中,找不到除了“从权”之外更好的理论资源;时代境遇在造成了广泛的饥饿时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食物。总之,虽然中国地大物博,外国鬼子现有的一切东西我们都“古已有之”,但饥饿毕竟还普遍地存在着。它仍然是一种本地的、土生土长的饥饿。在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鲁迅牌肠胃的伦理主义迫于饥饿的巨大能量,也只有先靠躲闪性——以躲闪之后的痛苦为代价——度过眼前的劫难,然后再想办法。
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的意思是,这些祖传的法宝和今人的鬼把戏,其实都无法解决普遍的饥饿:既解决不了精神上的饥饿,因为它为精神的肠胃规定了一种残忍的、无视饥饿的伦理学。也解决不了肉体上的饥饿,因为它的教义往往使得土地里的粮食连年遭灾。当鲁迅通过躲闪性度过了最初的饥饿后,他马上开启了肠胃的拿来主义之门:他把求救的双手伸向了别人。伸向了域外。拿来主义是作为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冲突的调解者身份出现的。而调解意味着看到两边。拿来主义既不同意祖传伦理主义的迂腐、无聊,现实主义的完全丧失原则、有奶便是娘。也不忍心看到鲁迅牌伦理主义始终处在无能的痛苦状态和躲闪性的偷偷摸摸上。因此,拿来主义意味着它要给予肠胃自身的时间以更加广阔的解释。它要把肠胃自身的时间搬到更大的空间中去,洗掉它的腥味,除去它的潮湿。但鲁迅非常清楚。由于祖传伦理主义对肠胃现实主义的长期规范、定义、修改、奴役,已经使得肠胃极度虚弱,难以承受、接纳和消化有着强烈生猛性质的西餐。罗兰·巴尔特对使用筷子和使用叉子的现实境遇做过一次区分:“由于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成为和谐的被传送的物质;它们把先前分开来的质料变成细小的食物,把米饭变成一种奶质物;它们具有一种母性,不倦地这样一小口一小口地来回运送。这种摄食方式与我们那种食肉的摄食方式所配备的那些刀叉是截然不同的。”(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与其说巴尔特是在赞扬中国的食物,不如说是在讽刺:上述言论已经把中国肠胃的虚弱性的原因和结果给一锅端了——虽然整本《符号帝国》说的都是日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才说:
人+兽性=西洋人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排除这两个算式中包含着的其他含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做是中西肠胃比较学的纲领。鲁迅在许多文字中都曾经暗示道:我们必须要有一副野兽一样的好肠胃。拿来主义需要一副野蛮的胃口。从工具论的意义上说,拿来主义拿来的就是野蛮的肠胃。
遵循着这样的设想,鲁迅曾经塑造了一位手持长枪、大步行走在无物之阵上寻找敌人的“这样一个战士”(《野草·这样一个战士》)。我曾经指出过,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战士手中的长枪。尤其是要注意长枪上的原始性。在这里,原始性毋宁可以被看做是拿来主义所需要的那种肠胃的外部显现、物化形式。因为鲁迅说过,这个战士肌肉发达,有如非洲土人一样健康、野蛮。“这样一个战士”粗粝的肠胃,和他虽然无聊但堪称勇敢的斗争方式完全吻合。
让鲁迅非常生气的是,尽管肠胃的拿来主义早在他提出之前就已经被国人广泛地使用了。但被拿来的各种东西——无论是西方的最新教义,还是最新式的洋枪洋炮,中国的肠胃都没有能力很好地消化。出于中国肠胃的虚弱性,要么就是这些东西被完全腐蚀掉,要么就是中国的肠胃被它们搞得七零八落,肠胃自身的时间也被大卸八块,离开母体而单独转动。这种情况早已被鲁迅揭发出来了。在《拿来主义》一文里,他指出了中国的肠胃在面对外来食物时一贯采取了两种方法:要么按照祖传伦理主义的旨意拒绝拿来,甚至一把火烧掉一这就和善于放火烧房子的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了;要么就是专门在外来食物中寻找已经腐朽的部分,因为它正好配得上只适合消化“流质”的中国肠胃。可是,既能消化外来食物,又能拒绝祖传伦理主义的中国肠胃在哪里?
这是鲁迅碰上的又一个大问题。
4 肠胃的个人主义……
在锻炼中国胃口、强化中国胃口宣告彻底失败之后。鲁迅在无奈中只有选择并依靠自己的胃口这一条路了。只有自己的胃口强大起来才能自救;如果想去救人,当然也就因此拥有了前提。鲁迅穿行在无数胃囊之间,却没有找到拿来主义所需要的那种好胃口。而“锻炼”、“强化”云云,需要希望作为后盾。在此处的语境里,“希望”也是“肠胃”的派生词汇之一。它意味着在肠胃拿来主义的巨大废墟之后,有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那里的时间柔软、温和,正在等待肠胃自身的时间能自动与它合一。希望有着心态上的双重性:焦灼和从容。从容能让鲁迅坚信未来还是有的,也可以让他把目光投向将来。但焦灼却分明已经标识了,形势的急迫和希望本身的遥遥无期,使得鲁迅经常性地陷入了绝望的地雷阵,从而丧失了从容。很快,鲁迅弄明白了自己的尴尬处境,随之对希望做出了坚定的区分:希望——如果不是虚拟的话,也是别人的,与他无干;绝望——这肯定是再真实不过了,却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肠胃的拿来主义迫于希望在心态上天然就沾有的双重性的巨大压力,彻底失败了。拿来主义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蜕化为一个比喻,一句胡话。也正是由于希望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把拿来主义的成败的关键,最后一次寄托在自己的肠胃上。鲁迅的肠胃怎么样呢?我们早就从鲁迅的动作中(比如踹击、背叛、跋涉、挣扎、向白天施割礼、斜视、瞪眼等等)和生活中(比如领取国民政府的薪水),看见了鲁迅的肠胃的种种特点:他的肠胃现实主义教导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肠胃而战;他的肠胃伦理主义则唆使他,无论怎样的战斗都得有一定的规矩,要遵循一定的律令。在所有的饮食中,总会有一部分被定义为“盗泉之水”、“嗟来之食”以及和“失节”形成鲜明对照的“饿死”。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对鲁迅的交互作用,他的肠胃现实主义和伦理主义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和平共处,——只领他的敌人的薪水而不为敢人干事,已经把这种不一致给挑明了。因此。中国需要的肠胃拿来主义,鲁迅也需要。这直接构成了鲁迅的肠胃个人主义。
鲁迅本人的胃口并不是非常健康。但他的胃口的不健康却有着特殊的形式。和中国肠胃的普遍性、集体性虚弱最终导致在拿来主义催生下的拉稀不一样,鲁迅是呕吐。鲁迅的肠胃一生都在试图接纳希望、消化希望,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和他的肠胃有着先天的不合:希望在从容中预支的遥远的未来时间,始终在和鲁迅肠胃自身的时间打架、斗殴、刺刀见红。鲁迅呕吐了。呕吐出来的也不再是什么希望,而是黑色的绝望。是的。那个人早就说过了,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因此,绝望就是鲁迅肠胃个人主义形成的呕吐物。它们组成了鲁迅作品空间的一砖一瓦。
鲁迅说,他一直在拿着希望的盾,以抵挡绝望的矛(《野草·希望》等篇目)。这实际上已经把他肠胃个人主义的特点全部“点水”了:肠胃个人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导致呕吐(这和鲁迅习惯于呕吐的记录方式遥相对应)。在鲁迅完全否弃了祖传的伦理主义之后,随着集体的肠胃拿来主义的普遍失败,他发现,肠胃的个人主义也有失败的危险。顺便插一句,祖传的伦理主义、集体的拿来主义也一度充当过鲁迅的食物,但它们还是被呕吐出来了。鲁迅为了获得健康的身体,从生到死都在寻找可以食用的、非腐朽的食物。他本人的肠胃拿来主义使他很早就把嘴伸向了国门之外,他吞吃过大量的食品:个人主义、进化论、尼采主义、斗争哲学。让人揪心的是,他的胃口在祖传的伦理主义长期的熏陶下,一方面想反对祖传的伦理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早已被祖传的伦理主义弄得太过虚弱;再加上现实的残酷境遇,使得他个人的伦理主义与肠胃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并产生了强烈的躲闪性,共同导致了鲁迅最终对几乎所有外来食品的呕吐——对各种信仰的习惯性背叛早已昭示了这一点。
鲁迅干瘦的身体和肠胃个人主义的呕吐特征有着极大的内在关联。由于呕吐,吃下的东西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化做了营养以供他的动作所驱遣(比如鲁迅的本地语调最终和传统语调有了某种同一性就是显明证据)。但在他做出的所有动作中,呕吐本身却占据了绝大半比例。最终的结局是尴尬的:呕吐本身导致了新的饥饿,需要新的“拿来”——既然本土的食品已根本不可食用;呕吐导致了新一轮的呕吐。我不知道鲁迅在怎样忍受这一连串充满腥味的动作带来的痛苦;而详细描摹忍受和呕吐的过程,也不是本人的本事所能及。但鲁迅的文字作为呕吐物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却给了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呕吐的凝固形式。只要我们走进去,我们就能看见它、听见它。
鲁迅的呕吐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呕吐把他的痛苦、绝望、愤怒给全部捎带出来了,也将肠胃的拿来主义重新进行了论证。如果最初提出肠胃的拿来主义,只是作为对解决伦理主义的躲闪性和痛苦的可能方案的“大胆假设”,呕吐毋宁就是对它的“小心求证”了。小心求证的最终结果是:拿来主义是不可能的。不仅中国的肠胃已经集体性地虚弱到了不能承受外来食品的程度,肠胃的个人主义也不能成为通达它的道路。鲁迅的深刻就在这里,他为未来的中国从肠胃(不管它是一个词根还是物态意义上的东西)的角度算了一卦:时至今日,我们真的有拿来主义吗?我们真的已经拥有了一副野蛮的胃口?鲁迅肯定预见到了,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很好回答的问题。也是直到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巨大问题。可是,没有肠胃的拿来主义,我们的身体和思想肯定会过度虚弱,有了拿来主义就肯定不会虚弱了吗?
责任编辑 宁 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