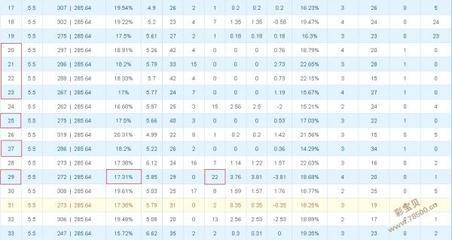本文所述全是事实,不过,由于她再三申明,她做的那件事在当时并不想为人所知,现在依旧如此。她以为只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小事,绝不愿在报刊上披露她的真实姓名。
作者尊重她的意愿,本文只用“她”来代替她的姓名。“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她,一个弱女子,在那风雨如磐的年月里,悄悄地而又勇敢地做了那件事,正是生动地说明了“民心不可侮”……
她,一个弱女子
1979年4月26日上午,银发如霜的作家柯灵走到话筒前,以异常庄重的语调,代表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宣布: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以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所蒙受的诬陷迫害,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柯灵是在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说这番话的。
傅雷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从英国赶来,出席了追悼会。阔别二十一载,他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回到故乡上海。望着追悼会上镶着黑框的双亲照片,望着那两只令人揪心的骨灰盒,他的视线模糊了。
追悼会后,傅雷的骨灰盒被郑重其事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聪感到不解的是,他父母是在1966年9月3日凌晨,双双愤然弃世。在那样的年月,他在国外,弟弟在北京被打入“牛棚”,双亲的骨灰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然而,他这次回到故里,亲友们却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他的双亲的骨灰俱在!
是谁把他的双亲骨灰保存下来的呢?傅聪几经打听,才知道是父亲的一个“干女儿”做的好事。
奇怪,父亲只认过钢琴家牛恩德作为干女儿,可是她远在美国。此外,父亲从未收过什么“干女儿”!亲属们也从未听说傅雷有过“干女儿”!
这个“干女儿”究竟是谁?
傅聪托亲友打听,颇费周折,才知道了她的姓名……
在上海一条狭窄的弄堂里,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她喜欢画画?”
“是的,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从小教她画画。”
如今,她的父亲已故去了,她跟母亲及妹妹住在这小小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拿出她的国画给我看,不论山水、花卉,都颇有功底,书法也有一手。她,画、字、文,三者皆娴熟。她所绘的彩蛋《贵妃醉酒》、《貂蝉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
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很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溯往事。有时,她中断了叙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风云突变的1966年
1966年9月,28岁的她酷爱音乐,正在她的钢琴老师家学习弹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什么?”她睁大了眼睛,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她跟傅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她是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这些译著中认识傅雷的。她非常敬佩这位翻译家流畅而老辣的译笔和深厚的文学根底。不过,她从未见过傅雷。
她倒见过傅聪一面。那是傅聪在获得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奖之后,1956年,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行钢琴独奏会。她当时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由于喜欢钢琴,买了票,听了傅聪那行云流水般的琴声……
“那是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老师的女儿继续说道,“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还有什么消息?”她异常关注傅雷夫妇的命运。
老师的女儿只听到一些传闻而已。
当时,她出于义愤,想给主持正义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她要向周恩来申明,傅雷临死还说自己是爱国的!
不过,她拿起笔来,又有点觉得不踏实,因为她听到的毕竟只是传闻。给周恩来写信是一件来不得马虎的事。于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细了解一下傅雷夫妇自杀的真实情况。
她打听到傅家的地址。她来到傅家,遇上傅家的保姆周菊娣。从保姆嘴里得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这些话,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这个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开始行动。她深知在那阴暗的年月。万一被人认出,将会意味着什么。
她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那儿工作人员的心。要留骨灰,就得买骨灰盒,她,只是里弄生产组的女工,菲薄的一点收入全都交父母,哪有多余的钱?
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便给他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与他约定见面时间。信末,只留一个“高”字(其实她并不姓高)。
她戴着大口罩,准时来到傅聪舅舅的家。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她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口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了。
死者入土为安。
她默默地,神秘地办完了那一切,她的心也感到宽慰。
她记起,在解放前,曾有四个亲友死后无钱买棺木。她的父亲慷慨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体同山阿”。她觉得,自己如同父亲一样,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不过,没多久,她的心中不安起来,傅雷夫妇惨死之事,时时搅乱她的思绪。
渐渐地,她觉得光是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还远远不够。她想,中共中央也许不知傅雷夫妇蒙冤的经过,她应当向中共中央反映!
苦苦思索多日,她终于写了一封信,寄给周恩来,如实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况。信中还提及了傅雷遗书中的话——他至死还申明自己是爱国的!
她担心这封信不一定会寄到周恩来手中,未在信后署名。
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封信落入了“四人帮”的爪牙手中,当成一桩大案,进行追查。她的字写得那么漂亮,看得出是颇有文化修养的。信中又谈到傅雷遗书,于是,那些爪牙们便怀疑写信者是傅雷亲属。他们从傅聪舅舅那里查到了那封只署有一个“高”字的信,笔迹相同,一下子又与“骨灰事件”联系起来了。
不过,当时就连傅聪舅舅,也不知道她是何许人。
“四人帮”的魔掌,紧紧地控制着上海。他们查问傅雷的其他亲属。她曾与傅家的一位姑母偶然说过一句,她的钢琴老师就住在姑母家附近。就凭这句话,他们追查到她的钢琴老师那儿,终于知道了她的地址……
墨染的夜
她刚从外边回来,踏进家门,看到屋里坐着三个陌生的男人,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她。
她一下子便意识到:出事了。
果然不错。来人用命令式的口气,要她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趁拿毛巾、牙刷之际,母亲压低声音对她说了一句:“他们说你是‘现行反革命’!”
她“有幸”坐上了轿车被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当时傅雷妻兄朱人秀在那里工作,也遭审查,所以由该厂造反派审讯她)。关在一个单间里。从窗口望出去,连对面屋顶上也有人监视着她!
第二天便开始审讯。窗外,围观的人好几层。审问时,并未过多地盘问她的经历——也许他们早已“调查”了。审问者反复追问她的动机。
“你为什么替‘右派分子’傅雷鸣冤叫屈?”审讯者问道。
“前几年,《解放日报》不是登过给傅雷摘帽的消息吗?他已经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等傅聪回来拜谢吗?”那人又问。
“照你看,现在这种样子,傅聪有可能回来吗?”她反问道。
那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问了一阵抓不到什么把柄,审讯不了了之。
大概是那些爪牙们查来查去,查不出这个青年女子有什么政治背景,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里,父母问她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她如实说了一切。父亲听罢,没有半句责难,反而说她做得对。
从那时起,直到1976年剿灭“四害”止,她在不安之中度过了九个春秋。有几次,户籍警来查户口,曾使她受惊不已。她的精神上,一直承受着无形的压力。“现行反革命”这帽子,仿佛随时都可能朝她头上飞来……
“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1979年4月她从《解放日报》上读到傅雷平反,隆重举行追悼会的消息。她心中的一块巨石落地了!多年的精神包袱彻底地抛掉了。
傅聪真的回来了!他四处打听才打听到她的地址,托亲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她却淡淡地说:“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傅聪一次次回国,总是托亲友给她送来音乐会的票子。出于礼貌,她只去听过一次,却没有去见傅聪。
傅聪的弟弟傅敏给她写来致谢信,寄来《博雷家书》及《傅雷译文集》。出于礼貌,她在1980年12月16日给傅敏写了一封回信。
后来,我在访问傅敏时,他给我看了这封信——
傅敏同志:
迟复为歉。素不相识,本不该以冗长的信打搅您,但有些情况又不得不细说,动笔几次,终于又搁下。感于你的至诚,但复信又觉为难,所以拖延至今。
首先应深谢您的关心;其次愧当“功劳”二字,并非我一人可成此事。至于谈到因您父亲而使工作问题受到影响,都属落实政策范围,那么,我完全不在此列。因当时我尚未踏上社会,若说为此事所受的“审查”,今天了解下来,亦未构成后遗症,因而没有什么可落实。看来当时办理我此事的工作人员并未食言:他们曾允诺我的要求——不向地区反映。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既得知,不留痕迹,则一了百了,更复何求!
今夏7月11日晚,您亲戚来敝舍相访。我回顾了与他们的谈话,我对自己的某些做法很不以为然。
朱佛恬同志(注:傅雷夫人的亲侄子)说,曾经去文联要求他们寻找我,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来寻找我的下落。因此,我希望我不至于到他们面前去申诉而谋得境遇的改善,当然也不希望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为我颇费口舌。这是公的一面。就私的一面,我全然理解您的心情,可是我认为您完全可以不必在精神上感到有某一种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事情与你们有关连,但在当时,完全是我个人的动机、想法。人与人相处,难免有“人情”往来,但任何事情一落到“人情”这一框框中。就失却了自然的真趣,凡属不自然的事,我希望不至于被我遇上。但,我和您从不相识,因此连人情两字都不适用。所以,作为子女的你们想了却这件事的迫切心情我是那么地理解。因此,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完全成了一种××(注:原文如此),这对我将是一种窘迫和难堪。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
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个女孩子(别管那女孩子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和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恕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质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得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不希望因人们巧妙的言辞、表情而流露对我的嘲弄致使我情绪上有波动,这种损伤我心神的波动绝非有价有值的东西所能补偿的。所以,我只能生活在不了解我一切的环境中。
所以,我希望少与人接触。不管认识与否,我一向力求别人能了解我。因此,敢以絮叨相烦。
傅同志来沪,如有便、顺路,不妨至敝舍一叙;若无暇,尽可不必以之为念,想能知我。
匆匆草此,搅时为憾。
这是一封何等真诚的信。一颗纯洁无瑕的灵魂,跃然纸上!
她以为,她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她说,如果她当时不写那封为傅雷鸣冤的信,也许她不会“暴露”,傅聪也就永远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她本来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所以做那件事只不过因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的翻译家——傅雷!
她还说,傅家的声望今非昔比,但是毫无必要把她的名字与傅家联系在一起。她仍是普普通通的她,一个平平常常的女读者而已。
我从她的母亲那里,知道了她的颇为坎坷的经历:她195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女中。当时,她与她的俄语女教师过从甚密。那位女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学校领导要她写“揭发材料”,她拒绝了。这样,尽管她成绩优异,却因“立场不稳,思想不好”。无法跨人大学的校门,只好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她常常说,如果那时她违心写了“揭发材料”,她可能早就跨人大学的校门了,但是她内心永远不会得到安宁的。十年浩劫中,父亲因政治问题,受到猛烈的冲击,在1971年离世。她体弱多病,迄今未婚。1979年,她已41岁,竞下决心人业余大学学古典文学专业,成为班上的“老学生”。她坚持学了4年,以总平均超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红色金字的大专毕业证书。自1984年下半年起,她调到上海一家编辑部编副刊,兼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于一身。工作是那样的忙碌,每天还要花3个多小时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她爱文学,爱书法,爱绘画,爱音乐,爱生活。然而她是一个恬淡的人,自洁的人,于人无所求,于己无所欲。
临别,她用这样的话,诚挚地对我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恪守诺言,不要透露我的姓名,我淡于虚荣!”
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通篇只用一个“她”字——因为我们有约在先!
1988年,她荣获全国书法“庐山杯”一等奖。大名被收入《中国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经她同意。披露她的姓名,她——江小燕。
这是后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