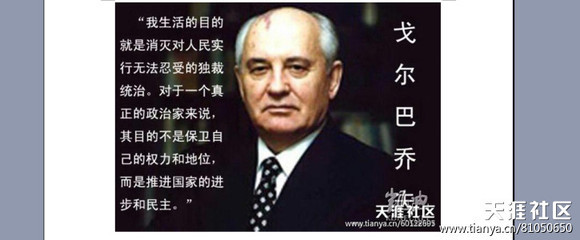????
1945年8月20日,日本关东军士兵在哈尔滨向苏军缴械
文丨李夏恩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8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这群人步履蹒跚、饥肠辘辘、疲惫的脸上挂满了沮丧的情绪,他们垂头丧气地慢慢行进着,“有的手里拿着半拉倭瓜,有的兜里装着从路边地里抠出来的土豆,有的手里拿着胡萝卜,有的啃着发青的苞米棒子”,这是这群人一路上唯一的食物。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敞着军服上衣,有的歪戴着帽子,很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这支杂乱无章的队伍还曾在战场上拼斗厮杀。只有几名军官,端正地坐在马拉的铁轮战车上,风纪整肃,目光严峻,“竭力保持着他们武士道的风度”。
崔凤成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支狼狈不堪的队伍从面前经过,他们是一群日本战俘,尽管落魄,却并不值得同情。即使是在三合村这个位于绥芬河畔边境小村庄里,日本士兵也已恶名昭著。像绝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在这片土生土长的土地上,崔凤成只能算是三等臣民,高踞头顶的不仅有占领东北的日本人,还有在东北沦陷的22年前就被日本吞并的朝鲜人,日本人称之为“半岛人”,东北人见了前两者都要鞠躬问安,否则拳头和枪托就会如雨捣下。尽管日本关东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在过去的14年里侥幸被战火遗忘,但在“日满亲善”的和平幻象下,亡国奴的耻辱无时无刻抽打在每一名东北人的身上。
但这一切都戛然告终,跟随在日本战俘两侧的苏联士兵就是证明,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背着圆盘式冲锋枪,每隔一、二百米一人一骑,跟随在队伍两侧”,负责押解这群俘虏。昔日不可一世的占领者就这样沦为低三下四的俘虏,但在这部剧情反转的历史大戏中,崔凤成扮演的只是冷眼旁观者,苏联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两个月前的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屯驻边境的160万大军突然大举入境,这场被日本人称为“一星期战争”的闹剧,很快就在8月15日广播里播放的投降诏书声中告一段落。到9月2日,全体关东军向苏军投降。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中苏友好”的红色标语很快取代了“中日亲善”的黄色宣传画。在铺天盖地的苏联红色海洋中,昔日傲视东北大地的日本人已无立锥之地,能在这个新世界里苟延残喘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按照“天皇玉音”里所说的那样:“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
向苏联红军集体缴械投降的日本汽车部队
通向地狱之路
在过去的几天里,元宗鹤感到自己正在演出一场“可怖的闹剧”。这个日本人所谓的“半岛人”在8天前才被强征入伍,主要任务是往信封里装沙子,好用来“打眯苏联坦克驾驶员的眼睛”。而现在,他和其他几名朝鲜同胞的计划是,当眼前这些狂性大作的日本官兵集体“玉碎”后,用炸弹清理现场,然后再借机逃跑。
但“玉碎”的场景却没有展现在元宗鹤眼前,他只看到了前戏——当军营中队长抱着炸雷跪倒在野战炮前的高潮终于来临时,一纸大队长发布的自杀禁令及时送达,阻止了这场闹剧的继续。这并非是因为大队长轸念生命慈悲为怀,而是出于担心,根据与苏军签订的和约,他要将这批军队如数送交苏军手中——这群侥幸逃脱“玉碎”命运的残兵很快将面对新的命运:战俘。这天深夜,在“朦胧的月光”下,元宗鹤将伍长交给他的一把手枪藏在准备逃跑用的苦力服里,打成一个包袱,打算一有机会就逃跑。
第二天,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躲过了苏军的空袭误炸后,元宗鹤和他的小队终于来到了苏军受降处。
还没到达入口处,元就听到一声枪响,一名被搜身的日军军官抽出手枪试图顽抗,但还没来得及放枪,就被在旁警戒的苏军枪杀了。元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自己打开行李表示合作,在提起那件苦力服时,他顺手把藏在里面的手枪抓牢再抖,终于顺利通关,和其他人一样被关进铁丝网里。进了收容所的元宗鹤迅速把手枪埋进了厕所里,直到此时,他才预感到“逃回家乡已经无望”。
元宗鹤的遭遇是成千上万缴械投降的关东军战俘之一。到底有多少日本士兵放下武器后被关进苏军收容所仍然是个未知数,苏联方面公布的战俘数字是59.4万人,远远超过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向苏军报告的45万这个数字。但实际上,这两个数字都同样水分不少。秦彦三郎试图将停战前被强征的16万新兵刨除在外,在他看来,这些毫无军事经验的新兵不应对战争负有任何责任。8月17日,就在苏军正式受降之前,关东军司令部暗中下令,示意各地驻军赶在苏军进城之前,迅速解散应征而来的士兵。但苏联人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身着军装的人,哪怕是出现在军事设施中人,都应当被看作战利品。
户村幸一就是这些苏军抓获的战利品之一。他本来是满洲建国大学第七期的学生,苏军突然进攻使他在8月12日被临时征召为“第二国民兵”。这些士兵刚刚学会用电影胶卷捆炸弹,就迎来了终战广播。但因为相信留在部队,可以作为战俘被苏军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早日送回日本,所以户村没有脱下军装,这最终将证明是个巨大的错误。
斋藤邦雄和其他战俘们一同被押上一列火车。车厢都是用很粗糙的木头钉成的,外面被涂成暗红色,东北当地人称之为“苏联瓦罐”。车厢的门鼻都用粗铁丝拧着,只有在上部开着一个车窗当通气孔,厕所则是地板上的一个30厘米见方的小孔。斋藤和一百多名战俘就一同被挤在这样一个狭小、腥臭的车厢里。9月初,元宗鹤被苏军驱赶着跟随关东军野战炮兵大队千余名战俘一起上路时,脑海里只剩下铁丝网里漫长而无聊的俘虏生活。他甚至没有斋藤邦雄挤在逼仄车厢里的运气,前进的每一公里都需要用自己的脚来丈量。
就像那个12岁的中国孩子崔凤成所看到的,每一列长达数百米的狼狈的日俘队伍,都由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骑马押解。这些苏联士兵背上的冲锋枪绝非摆设,老弱病残的战俘使它们胃口大开。“我们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已经倒伏路旁”,一位战俘回忆道:“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四周林间,我们沉默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死一个’”。
9月10日,元宗鹤的这队日俘终于来到一个叫黑河的边境小城,本来以为可以暂时休息,却看到一艘汽船从对岸驶来。直到这群战俘踏上汽船的那一刻,他们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不是回国,而是前往苏联。“当汽船驶到江中时,有个日本人纵身跳进江里,转眼之间被滔滔巨浪卷走了”。
对元宗鹤这些侥幸活下来的战俘来说,他们很快会发现那个投江自尽的家伙是多么明智,就像那些在8月15日集体自杀的人们一样——死亡同样也是一种逃避,用来逃避活着见证地狱的命运。

1945年8月,关东军部分将官在沈阳投降后被运往苏军后方
极寒地狱
事实上,在这群日俘被苏军的押解下一路北上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地是苏联。很多人听说过《波茨坦公告》,相信苏联会履行其中“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的条款,一些负责押解的苏联士兵也是这样告诉这些战俘的。
穗苅甲子男同样也沉浸在这种返乡的幻想之中,尤其是当押送战俘的列车抵达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时,这种幻想就变得更加真切,人们开始相信列车会把他们送到海参崴,然后在那里登船返回日本。但当列车再次开动时,幻想带来的喜悦开始逐渐被忧虑的揣测所取代,因为列车的方向不是海参崴所在的南边,而是一直向北,到了伯力又一路向西,到最后,这些无凭无据的揣测也渐渐失去了活力,沉寂下来。当火车驶过一大片水面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方向感的日俘们开始惊叫欢呼,挤到门缝前,打算看一看“日本海”,但车站外的车牌告诉了他们真相——贝加尔湖。
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谎言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一开始就告诉这些战俘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劳改营,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恐慌和混乱。负责押送的苏联士兵开的枪已经够多了,每一颗子弹都很珍贵,至少比这些战俘的生命更值钱。
这个谎言在苏军出兵东北时就已经初具雏形。苏联人有自己的理由,他们是这场世界大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超过2700万人死在战场上或是消失在苏联关押自己被遣返战俘的劳改营里,直到战后15年,苏联20到30岁的青年人口男女比率仍是6:10,满目荒夷的战后大地亟须输入新血来恢复活力,这些来自各国的战俘就成为最适合不过的劳动力。8月23日,也就是苏军与关东军签署正式投降协定的5天后,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第9898号《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安置、劳动使用》决议。
在这份出自一个计划经济已经高度成熟的政权之手的文件中,各人民委员部的战俘人员分配精确到了个位数,从人数最多的内务、建筑工业、林业、煤炭、冶金一直到人数最少的海军、河运和造船工业,近60万日军战俘被精致而科学地分配到不同的行业之中。“质量最好”的战俘会被送进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关怀”之下的直系收容所,享受和苏联正统的古拉格劳改犯一样的待遇;其他战俘则分别送进各企业管理的战俘营和武装力量部管理的战俘营,他们的“待遇”也许不如直系战俘营那样管理得“系统而有序”,纪律会比较松散,但工作环境可能会更加严苛。
穗苅甲子男所在的收容所建在伊赛图的一个空旷山谷里,四面全是莽莽无边的原始森林。这座收容所只是分布在苏联深林荒原中的267个收容所下2112个分营当中的一个。尽管日后逃出生天的日俘将自己称为“西伯利亚拘留者”,但实际上,西伯利亚的收容所只是数量上最大而已。在整个苏联的大地上,从阿尔泰山区到哈萨克,从赤塔到蒙古,从哈巴罗夫到伊尔库茨克,苏联的势力所及之处,到处都分布着日军收容所。一名叫江部忠夫的日俘就被分派到蒙古收容所,尽管在伪满洲国时代,“日满蒙一家共存共荣”是最响亮的宣传口号之一,但这并没有阻止蒙古兵“用刺刀抵着,将我们装上卡车”,送往“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在两年的时间中,13000名战俘有超过1600名死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相比来说,穗苅的收容所因为太过偏远,所以并没有遭受如此严苛的看守,斯大林在9898号决议中为关押这些日军战俘特批的800吨带刺铁丝网显然也没有用在这里,甚至连巡逻的岗哨也没有。但同样的,官僚体制下达的命令常常只是一纸空文,决议中优待战俘的条款也从未被遵守,大多数战俘抵达收容所时,身上还穿着关东军的夏装。穗苅不得不在没有手套、棉鞋、棉帽的情况下,冒着12月的寒风搬运粗大的原木。“手指、脚趾变得干燥,然后变成黑色,开始溃烂,一块块往下掉肉”,为了保住性命,很多人不得不截掉手脚。这种缺少御寒衣物的情况极为常见。在苏联人看来,这些日本战俘不过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微不足道、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西伯利亚的极寒荒原会慢慢咀嚼这些牺牲品,直到他们的身体成为滋养这片不毛之地的肥料。
1946年,溥仪(右)在苏军押解下自苏联伯力战俘营飞抵日本横滨厚木机场,以证人身份出庭东京审判
劳役的饿鬼
每当碰到自己的大腿,山本善丸就会想起伊尔库茨克漫长的、寒冷的、缺衣少被的冬天,还有脱得一丝不挂,冻得上牙打下牙地站着,被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检查身体的情景。这种检查名义上是记录每名战俘的健康状况,但实际上,只是“捏捏肚子和屁股的表皮,以胖瘦决定身体的状况。”根据肉的厚薄,这些战俘会被分为三等。
没人愿意分在第一等。那些“屁股上肉最多”的人,可能是最不幸的一群,因为这些“最健康”的人必须从事最重的体力劳动:伐木、采石、搬出枕木和模板、房屋建筑、铺设铁轨。早在1946年3月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下达了《最大限度利用德国人及日本战俘》的指令。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城不仅仅是那些风华正茂的年青共青团员辛勤汗水的杰作,更是39400名日本战俘苦役劳动的产品。如果在矿区的话,这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被当作是最合适的挖掘机器,他们会被派遣到最危险的狭窄矿洞里,在完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情况下安装炸药或是架设框架。即使他们逃过了频繁发生的矿难,粉尘和窒息也会时时刻刻要了他们的命。
但最不幸的是那些在“特殊机构”工作的日俘,在负责开发原子弹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场地中,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这些日本战俘的一举一动。1949年7月底,就在原子弹试爆之前的一个月,苏联政府下达指示,“参与了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重要特殊工程建设的各类战俘和犯人都应成为幽灵”。
如果被分在了二三等,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逃脱苦役的厄运。苏联人对日本战俘的顺从和卖力赞赏有加,“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但最具有黑色幽默的一点是,高强度的劳动,反而与刺骨寒冷下的缺衣少被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非常适合成为收容所的座右铭,到了户外,不运动血液就有可能冻住,甚至可能会冻死在这片被遗忘的冰雪荒原之中。
尽管高强度的劳动可以给身体带来暖和起来的假象,但身体真正的热量来源,却是食物。为了体现共产主义人道的优越性,1945年9月28日通过的《日本战俘粮食供给标准》无比精细地规定了每天的食物数量。即使这个标准距离《日内瓦公约》的标准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对这些饥寒交迫的战俘来说,也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前提是它真的被认真执行了。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名日军战俘体会过苏联政府的人道关怀,在穗苅甲子男的记忆里,从冬到夏,从春到秋,每一天的两顿饭都是黑面包和土豆泥,外加半桶红茶水或是略有咸味的菜汤。一块3公斤的黑面包,要分给16个人,即使分配得再平均,每人也只能大致分配到190克。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
在那些更加贫乏的收容所里,所有可以果腹的东西都成为人们搜求竞逐的目标:猫、狗,甚至是鼹鼠、野鼠、青蛙和蛇。在安吉连收容所,苏联士兵会用“恐惧轻蔑的眼神”盯着日本兵们“平静地吃着蛇和狗”,而且“因为第一年捕猎得太多了,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时,几乎见不到蛇了”。
1948年,日本舞鹤港,由西伯利亚集中营遣返的日俘向迎接他们的医护人员挥手致意
死亡并不平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日军战俘的日常生活,应该被称为日常死亡才对。因为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兽类的本能,而无时无刻袭来的死亡反而更具有生活的气息。
比起冻死和饿死,疾病和瘟疫的死亡都已经算得上是善终,这些病人有时会被送进苏联军医院或是可怕的遗忘收容所。但对大部分战俘来说,这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在很多地区,进入医院等同于死亡,因为一般的医院里甚至连阿司匹林和止泻药也没有。肺结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断呛出的血痰里。医生不懂得消毒,凭着一腔蛮劲儿,用普通的剪刀为战俘剪掉冻伤的手指,用矿场里切金子的锯为战俘截肢,术后三四十天的高烧和几乎百发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战俘命丧黄泉。
对战俘来说,恶劣的环境让死神满载而归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在面对死亡这方面,大家似乎取得了平等。但内部的魔鬼却也在向死亡进行残忍的献祭,就更为令人发指。
从表面上看,吉村是个相当平庸的人,“下巴方而宽”。但和他接触长了,便会发现他有一双“蛇蝎般冷酷的眼睛”。正是这个乌兰巴托西北部羊毛厂战俘收容所里的队长,发明了“祈祷天明”这种听起来很美的私刑惩罚。吉村规定他手下的战俘必须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早饭前每人必须从两公里外的山上运回两根木头,早饭后,则是连续八个小时的烧砖、纺羊毛和凿石头以及收木筏的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半才结束。如果有人完不成任务,吉村便会罚这个人脱光衣服,绑在树上,站在户外“祈祷天明”,而吉村和他的同伙却在屋里饮酒作乐。天寒地冻加上饥肠辘辘,到天明时,这个战俘往往只剩下低低的啜泣,然后便断了气。
吉村并不是唯一以虐待难友为乐的战俘队长,这种同胞之间的虐待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却真实发生,人性卑污的劣根似乎不能完全解答这一点。事实上,苏联人很愿意看到这一点,甚至还大力鼓励这种以上欺下的行径。很多收容所的情况就像是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杂交出来的魔种,原先的军官要求下级绝对地服从,否则暴力相向,而苏联士兵则在旁边冷眼旁观,或者饶有兴致地添油加火,观看这种“动物打架的行为”。
战俘营里的官兵待遇也各有等差,军官往往在分配食物时独霸最大的一份。死亡的平等就这样被轻易地破坏了。一名叫村山常雄的战俘,在离开西伯利亚后统计了46300名死亡战俘,结果将校死亡只占死亡总人数的1.5%,下级士官也只有8.3%,剩下的90.2%全是像他一样的普通士兵。至于死亡的总数则至今是个争论不休的数字,苏联官方从来没有通报过一个直接的数字和死亡名单,死亡数字总是两千、三千的一点一点从牙缝中挤出来,把悲伤的消息一点点地透露给日本国内的家属,日本自己的统计数字则是5.5万人左右。日本的民间却流传着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20万人的说法,在这个说法中,到西伯利亚的行进途中就有4万人死亡,而后来的奴隶劳动则造成16万人死亡。
尽管这些战俘一直在西伯利亚冰冷的荒原上被人遗忘地劳动,但日本国内却一直坚持不懈想方设法地接他们回国。在日本政府和国人看来,这些所谓的战俘是被苏联非法扣押的拘留者,日本与苏联交流最频繁的舞鹤港上,被战俘家属挂满了自己丈夫和儿子的照片,希望从港口下船的人能认出某个人的面孔,或者至少带来一点战俘们的消息。为了迎回自己的国民,日本政府答应了苏联政府提出的7760万美元的巨额遣送费,用必需的商品作为抵偿。
这些努力最终换回了51万名战俘的归来。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暗中向苏联当局提出要求,“俘虏的日本人不经过共产主义教育,不能让其回国”,苏联政府对这个想法相当赞赏,认为这样可以将日本战俘改造成埋在日本国内的一颗共产主义革命的定时炸弹。活着的人不得不“高声大嗓地唱《红旗歌》和《国际歌》,并且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同志和共产主义的无比热爱之情”,才被允许返回自己的祖国。
舞鹤港成了一个悲欣交集的地方,走下船的日本战俘会被久久等在码头的亲人拥在怀中,寒冷、饥饿、死亡、凌辱、劳累,都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但这记忆仍会时时触碰灵魂最痛的地方。
 爱华网
爱华网